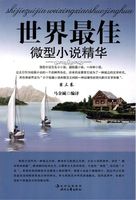天门移鱼解惑,石达开先想明白了其中的含意。
他刚要开口,天门递个眼色过去,然后埋头吃鱼,“这种江鲜,在北方是吃不到的。”
石达开把自己碟中的鱼夹给天门,天门会意地冲他一笑。
韦昌辉看着面前的鱼出神,半天才回过味来,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把女营解散?”
天门笑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好主意,女兵不用打仗,应该让她们有家的归家,无家的配婚,共享天伦之乐。”韦昌辉大开其窍,道:“天门,你最得天王信任,可在他跟前多念叨念叨,我在外头找些臣僚同时请奏,力争尽快解散女营。”
天门顾念着苏三娘尚被洪宣娇关押,道:“苏三娘是马上战将,不是寻常妇道人家,留她在城里做什么女营总管?她与罗大纲情投意合,何不将她发往罗大纲军中……”
“说的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苏三娘原本就不该入城的,明天我便去请天王下旨,令她出城。”
一顿饭,一团和气,既解了石达开和苏三娘的困,也了却韦昌辉的心愿。
这些都不是天门的主要目的,他知道杨秀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也看出杨秀清与洪韦之间已生隔阂,他在不动声色之间,为杨秀清埋下了一颗地雷。
是的,太平军惯用埋雷战术,杀伤力极强,官兵已屡屡败于地雷战中。
天门这颗雷,不用火药,也不用引线,而是埋进了猜忌和憎恨。只要洪秀全解散女营,杨秀清在城中失去十万兵士的依靠,必然对洪秀全产生猜疑;只要解除洪宣娇的兵权,洪宣娇必然对洪秀全心生憎恨。
这样一来,暗中角逐,狗咬狗便在所难免。
天门在席间再三阻止石达开多言,是因为他很快离开天京,无论他出什么主意,鼓动韦昌辉做什么事,都无关紧要。而石达开还要在太平军里混,若他搅和到韦杨的矛盾里,到头来只怕洪秀全要丢卒保帅,反成了牺牲品。
说到底,韦昌辉这个人是不会与石达开真正站到一起的。
天门的计划很完美,可是他没想到,曾国藩却无意间破坏了他的计划。此时,曾国藩的水师已经组建完成,团练队伍也已训练有素,正准备水陆两军齐发,由南到北一路收复失地。
天门不愿再入女营,不愿再去与洪宣娇周旋,但洪秀全命他出城的上谕未下,最后这件选美的差事仍要办好。
第二天,再开朝会,在韦昌辉等人的力主下,洪秀全冲破杨秀清的各种阻挠,任命石达开为天京守城主官。
没占据江宁前,在调动军帅方便,杨秀清从来说一不二。坐稳天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在洪秀全面前受挫,这件事对他的震动极大,他担心的是有一便会有二,渐渐地会失去太平军的控制权。
洪秀全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城外头,清妖在江南江北驻扎两处军营,随时有可能大举攻城,这个时候,洪秀全哪来的底气,敢做出有损他权威的举动?
杨秀清感觉哪儿不对,默默注视着天门,回想起永安城外那一幕。
永安城外,他袖里藏剑,悄悄向天门刺去,突然身后扑上来一人,将天门击落马下……
杨秀清知道没有刺中天门,可是那个吃他一剑的人是谁呢?是替天门挡剑,还是意欲生擒拿天门误撞到剑上?!
天门被清妖活捉,不仅毫发无损,竟然辗转重归太平军,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
散朝后,杨秀清拦住天门,假惺惺地客气一番,对在永安时没能保护好他表示歉意,接着话锋一转,突然问道:“那个清妖认得你?”
杨秀清自以为聪明,可以诈一诈天门,孰不知一开口,便已输了。
这种事怎么说得清楚,杨秀清裹挟在乱军中,急于逃回城去,突然蹿出一人,他只见黑影一晃,连男女都未分辨清楚,问出这种话,任由天门如何回答也无对证。
天门知道如今的杨秀清,喜欢别人称呼他九千岁,便说:“九千岁该感谢我,不是我阻挡住那清妖,落马被擒的就是你啦!”
杨秀清是太平军主将,清妖擒贼先擒王,合乎情理,既然他不敢承认谋杀天门,天门反手一击,不仅将他的嘴堵个严严实实,而且卖个大人情给他。
杨秀清顿时被噎住,呆了半晌,道:“如此说来,本王是该好好感谢你。”
“九千岁打算如何谢我?”天门步步紧逼道。
“这个,你想要什么?”
“九千岁如日中天,天门当然希望攀附,”天门庄重地躬身施礼道:“天门有意与九千岁的公主结为秦晋之好,不知九千岁意下如何?”
杨秀清有一女,年仅十一岁,天门知道此事绝不能成,才故意求亲。一来为麻痹杨秀清,不要在他出城时掣肘;二来为撇清石达开,以免将来他的身份暴露,连累到石达开。
听天门口出此言,杨秀清立即脸色大变。
莫说爱女尚且年幼,便是当嫁之年,凭他东王九千岁的尊荣,也应讲个门当户对,天门丧妻之人,岂能下嫁给他作填房。
杨秀清有心发作,但见天门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样子,并不像是作弄自己,而且是他有言在先,要天门提出请求。
杨秀清强忍不快,冷冷地说:“非是本王拂你的意,实是小女尚且年幼,懵懂无知,这时婚配,恐引人耻笑。”
“天门可以等,只愿先订下亲事,”天门仍是一脸真诚,“天门在天京无依无靠……”
“怎么叫无依无靠?你与翼王有亲,又与天王有结拜之谊,你正炙手可热呢!”
“石珞身故后,翼王对天门恨之入骨,我们二人早已貌合神离,更遑论亲情。”
“不是吧?据本王所知,你现正住在翼王府上,怎说没有亲情?”
天门上前一步,低声说:“实不相瞒,天门寄人篱下,去翼王府瞧石达开的眼色,实属无奈,而是天王的意思。”
“天王的意思?”杨秀清一想便知这句话内藏的深意,不禁大感意外。
天门的话有道理啊,在金田时洪秀全尚能为他建造官邸,而今他不顾艰难险阻,重回天国,更应该为他分发丞相府才是,怎么会平白无故让他住到翼王府去呢。
没看出来,洪秀全一面独断专行要石达开接管城防,一面却派天门去监视。杨秀清想到这里,不由悚然一惊,感到一阵后怕,原来洪秀全平日里沉湎宫闱,全是假象,暗中却防着为天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王。
石达开不过是仅领一军的三等王,而他杨秀清却节制诸王,掌控所有军队,洪秀全对他自是更加不放心!
天门何其聪明,他定是瞧出洪秀全心怀叵测,要学以前的皇帝,做卸磨杀驴的勾当,才急于寻求靠山盟友,以求自保。
天国中除了洪秀全,谁最有实力与洪秀全相抗衡,当然是他杨秀清,天门晓天机擅计谋,懂得审时度势。
杨秀清越想越觉天门突然亲自向他提亲,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杨秀清想,天门有心计,我有兵权,若我们二人联起手来,有朝一日要取天国,岂不是如探囊取物。
邵天门能审时度势,我就不能吗?想到这里,杨秀清道:“似丞相这般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你能相中小女,是小女的福气……至于定亲这件事,请容本王回家与夫人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可否?”
天门见杨秀清口风松动,忙道:“不急,不急,公主的终身大事,九千岁自当慎重,天门便候着就是。”
天门目送杨秀清向东王府的路上走去,追上韦昌辉,拉着他直奔女营。
洪宣娇让天门一吓,不仅脸上的伤口溃破难愈,而且发了高烧,卧床不起,不时胡言乱语。
洪宣娇的使女见到天门,哭丧着脸说:“丞相大人,您可来了,萧王娘她,她……您快进去看看她吧!”
韦昌辉觉得奇怪,问使女:“她怎么了?说话为何吞吞吐吐?”
“奴婢不敢说。”
天门心里有数,拉着韦昌辉进到洪宣娇房中。
洪宣娇满头乱发,脸上的烫伤渗着血水,面目可怖,韦昌辉瞧了一眼,惊得连连后退道:“这是她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
“贵哥,你来了?你的娇儿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打我吧……”
洪宣娇看见韦昌辉,猛然扑了过来。
韦昌辉吓得抱头鼠窜,几个使女赶忙抱住洪宣娇,将她拖到屋里,将门反锁上。
天门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萧王娘,竟如此不堪一击,被自己一吓便疯了。他仿佛看到多年前装疯的若兰,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请医士看过了吗?”天门问。
“看过了,也开了方子,只是不见效。”
“她这是疯了呀,她脸上的伤是自己抓挠的吗?真是报应!”韦昌辉说。
天门想起朱九涛教过他一个方子,便要来纸笔,写出来交给使女道:“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吧。”
韦昌辉看使女跑远了,道:“何必救这个荡妇,让她疯着就是!”
天门轻声说:“她已经受到惩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