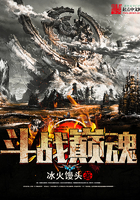且说陆熠写了那些书信,心中忐忑。一条路是走迂回,通过书院,若是那院里的先生不计较得失定会前来兴师问罪。另一条路则是走的直线,直接向皇帝进言,虽说成功几率较小,但影响大,事也彻底办了。
陆熠在牢中苦等一月,表面上他于往常无异。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第一条路算是夭折了。前去书院,快马日夜兼程十日便到,来回不过二十日。三十日过去了,这边还没有动静,想来是那书院的学究们明哲保身,没有风吹草动何苦惹祸上身,不会轻易来解救自己的。
只有看第二条路,陆熠心忖着,湖州到长安来回便要一月。若是真告了御状,使团被劫那皇帝碍于面子,定会借着春闱的名头,悄悄派人前来。春闱还不到时候,眼下就只有等了。
陆熠瞧了瞧墙角的黑暗角落,那伴随自己一月有余的老鼠似乎呼之欲出。看来是那午饭要来了。
果不其然,牢头端着碗筷一瘸一拐走来。递于陆熠,摇了摇头,便转身走了。
自从送出那书信后,陆熠天天盼着那来解救自己的仪仗,叫牢头一有消息便来通知。起先牢头还会安慰几句,几十天下来,牢头干脆只摇头,不说话了。
陆熠一阵落寞,有些心灰,难道天下的乌鸦竟是一般的黑?
薇达公主已和本大人分开关押。毕竟男女有别,吃喝拉撒皆在牢房之中,些许不便。若不是陆熠叫牢头送去一只马桶,那薇达估计早就羞愧难当,自尽了事了。
对那俩番子,张县令也想提审一次,碍于语言不通,只能作罢。心中奇怪的是那陆熠的亲戚一下自都不来劳烦自己,耳边倒是清净不少,可心里却不是滋味,隐隐觉着有大事发生。
时光如流水,转眼又是一月。
离陆熠限定的三月期限将至。后日便是清明佳节。在湖州有句话叫“清明大如年”。
湖州地处江南水乡,全年雨水较多,盛产稻米,遍植桑麻。一年中,又以春耕秋收最为繁忙。一年的劳作便从清明正式开始。因此,便有了清明祭祖的习俗,给坟茔周边开开沟、栽栽树。给坟添添土、整修整修,用些食品、香火祭奠祭奠,表示以后一段时间因农忙而无暇顾及,实在是想从祖先那里得到谅解。
张县令思忖着待到清明之日,花些钱好好修葺祖坟,以报祖先在天之灵。过得清明,便要好好准备那半月之后的春闱事宜。心忖着怎么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其实他自己心中惧怕,放不放人只在那一线之间。那陆熠十岁便是如此,若是待到羽翼丰满,定会找自己麻烦。暗下了决心,横竖结下了梁子,等诸事停当,定要做一个了结。至少也要来一个发配充军,叫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客死他乡,永世不得翻身。
有了主意,心情也随即好了起来,端起茶杯靠在太师椅里小唑一口,拈来一块精制糕点,细细品味起来。却看见张安跌跌撞撞从门外跑来,气喘吁吁道:“大……大人,有大大得人……来了!”
“说清楚?什么大人、大大人的?”张县令怒道,“急什么?慢慢说!”
“大人,小的……刚在城门口一辆四驾的……马车朝这里驶来!照理三品的大员是少不了的!”张安心道,幸亏跑得快。
“快,快,准备出迎!”张县令一把从太师椅上窜了起来,大吼道,“红袖、碧纱取官服来!”
一阵鸡飞狗跳,县衙上下忙了一个不可开交。等到诸事齐全,张县令迎出门外,那四驾的马车正好驶进那牌坊。车夫见到有官员出门相迎,便停了车,转身问道:“大人,前面就是了!”
里面的大人,便是轻装简从,自长安直奔湖州而来的魏征。魏征年过五旬,怎经得起如此折腾。老身子骨早就散了架。不敢对圣上有所埋怨,把一股怒气都撒到了那个未曾蒙面的湖州县令身上。正欲撩开车帘子,便听到扑通一声,有人唱道:“湖州县令张沼,拜见大人。不知大人驾到,未曾远迎,还请大人恕罪!”
魏征心道,终于见到这个挨千刀的县令了。不说话,从马车上缓步下来。笑道:“不必多礼,起来说话!”
张县令听不出那人的口气,站了起来。瞧见那半百的老者,气定神闲,眉宇间英气勃发。除了脸露倦意,哪有半丝年迈之气?那老者身着紫袍,腰间一条镶金嵌银的金鱼带。张县令只觉天旋地转,双腿发软。这不是朝廷一品的大员吗?结结巴巴道:“大人……里边请!”身子一恭到底,大有魏征不进去便一直弯下去的意思。
魏征旅途劳顿,深感太宗急切,只带了一名贴身的护卫,一路行来吃住都是在车上。早就厌倦,正要看看那湖州县衙的情况,便回答道:“张县令,前面带路!”
张县令这才站直了身子,站到魏征后面,道:“大人先请!”一只手乖巧得搀起了魏征,不紧不慢得往里走。
来到正堂,魏征坐在正中,那护卫站在其后。张县令此时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坐吧!”魏征道,“出门在外,没有京城那么多的规矩!此次春闱本官负责湖州县,所以套叨唠几日了!”
张县令一惊,以往春闱撑死了也就来了一个三品的侍郎。今年怎么会来一个一品的?想破了头还是想不明白。便顺口道:“大人一路辛苦,不知可用过午膳?”
“在路上吃过一个馒头了!”魏征有些开玩笑似的说道。
“这怎么行?大人快请!”张县令跟张安耳语几句,吩咐他去准备。
匆忙准备的饭菜当然不行。魏征心中有事,加之湖州的菜虽精致,但不对胃口,吃了几口便觉得饱了。
吃罢,到了偏厅吃茶。
张县令见那大人吃得少,心忖着到底是怎么回事?莫不是酒菜不和胃口?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小县的吃食怎能跟京城比?便道:“大人吃的还习惯么?”
“老了,咬不动啦!”魏征这才抬起头来,眼睛死死盯着张县令,似要把他看穿一般,道:“如今陛下圣明,国泰民安,作为县官是不是很清闲啊?半天都没有来告状的!”
张县令以为是嘉奖,道:“是啊。本县民风淳朴,极少有民事纠纷!”
“如此甚好!”魏征瞧那县令得意洋洋的样子,心中暗道不好。居安思危,偌大县城一案都没有的话,不说明治安好,而是说明县令大人审案不公,百姓都懒得来告状了。表面上却装了一番,又问道,“既然民风无以到开堂的地步,那大牢的款子也不要了吧!没有犯人要大牢何用?”
叮当……
张县令刚端着的杯子掉到了地上。这大人定是知道些什么?否则不会一到便开始问大牢的事!而大牢里只有俩番子和陆熠三人。莫非跟陆熠有关?想到这里手上再无气力,杯子徒然掉了下来,摔个粉碎。
魏征心道这县令胆子也忒小了,自己只是略微一吓,他便露出了马脚。虽不知那陆熠是否还在牢中,但可以肯定,牢里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拍桌子,叫道:“好你个湖州县令,要欺我到什么时候?”
张县令诚惶诚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人息怒,下官真不知何时骗过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