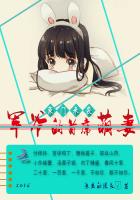七叶手持令牌,佩着能让人放松心房的洗尘香,随便扯了个为公主殿下寻几名乐师演奏新曲的名目在乐府一待就待了整整两日。期间,从现今的曾经的宫廷第一乐师到刚入乐府连乐谱都没能弄明白的新人乐师乃至乐府中的宫奴女婢,一应人等全都见了个遍也没见到文杰口中的那名乐谣乐师。
正当她开始猜想是不是文杰强行逗留得太久太过虚弱以至于记忆已经不牢靠的时候,在受到乐府气氛感染无意识地哼出了一首夙夙谱写的曲子时,却意外得到了一名已经显得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乐师的青睐,终于在一次和老乐师试探性地交谈了一番之后寻到了些眉目,老乐师有些怀念地提起了自己曾经一名名叫阿谣的得意弟子。七叶顺着话题往下问时,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细说,只又叹息着提起一本被称为《点降曲谱》的乐谱来。
据说此谱乃是千年前某位精通百乐的得道高人所著,一音一调无不精妙至极,是以当这本曲谱经外使交由皇帝,又由皇帝交由乐府处的时候,乐府里边的所有乐师都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复。
古谱和现今的谱子虽有极大不同,却也没有浇灭乐府乐师心中的火热,很快,第一首曲子就被译了出来,并交由到了包括阿谣在内的几位最能领会乐曲精髓的乐师手中。
那曲子名为《情狂》,写的是一名凡间女子对一位天神一见倾情,甘愿追随其后为其贡献终身,最后却因见到天神和其道侣琴瑟和鸣双宿双飞而妒火难消,最后落到因爱痴狂被逐离神域的故事。
那时阿谣还是个十五六岁情窦初开的小丫头,对****的全部体会全来自以往听过的戏曲和话本评书,对于情之一字虽能勉强体会一二,却始终无法深解,自然在凡女因爱生妒为爱痴狂的这一段旋律上有些表现不足。
小姑娘心高气傲,几番尝试无果后剑走偏锋想出了个法子——去真正爱上一位像那位天神一样的英雄,然后像那名凡女一样去嫉妒,去痴狂。
再后来……
“再后来,她离开了乐府,我便很少见到她了。”老乐师满脸唏嘘。
“阿谣姑娘她去了哪儿?又发生了何事?”七叶追问道。
“后来的事,便不能再往下说了。”老乐师沉默片刻,告诫七叶道,“要不是看小姑娘你为人沉稳,不像是个会在背后嚼人舌根的人,老夫我今日所说的这番话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与你听得。宫人妄议后宫乃是大忌,这故事,你听过,便忘了吧。”
英雄,妄议后宫……
这宫中除了皇帝和他的儿子们,谁又敢自认为是英雄,除了皇帝谁的宫里又敢自称为后宫?
听起来乐谣应该是在先前被自己忽略过去的那群宫妃中啊,而且看这老乐师面有戚戚的模样,莫不是她的日子过得很不好,相当不受宠?
“这几日,我已经将乐府中能听到的曲子都听了个遍,就连那些未曾在人前演奏过年轻乐师的拿手曲子我都统统听了一遍,可这铃铛的最后一声却总是不响,也不知是何故。”七叶有些忧愁地向公主汇报。
文昌公主显得也很忧愁,自打确认她所期待的贺礼真的需要这铃铛响够七声七叶才会开始动手为她准备之后,便一直对这铃铛很上心,若不是近日都要随着皇后娘娘她们一道劝慰开解德昌,她肯定要亲自前去的。
“我和父皇说一声,明日你再去各个宫里看看。”
“是。”
于是接下来两日,七叶便如愿将后宫里边大大小小的宫殿院落全逛了个遍,可那乐谣却仿佛蒸发了一般,半点踪迹不见。最后,整个皇宫里边,就只剩下最为偏远僻静的冷宫和皇帝所在的乾天宫和御书房这些平日里后宫妃子轻易进不得的场所了。
从先前在乐府里边闲聊时那老乐师面上的戚戚然之色上来看,在冷宫的可能性无疑要更大一些。
过了某位不受宠的嫔妃清净的小院,一路向西又行了一段挺远的距离,远远便见到了一处和宫内那些琉璃彩绘朱墙青瓦的建筑格格不入的冰冷灰色建筑群。
供人行走的小路上落满了不知打哪儿吹来的树叶,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打扫过了,一路踩着那些枯萎的杂草走过时,隐隐还能看到蛇鼠穿出来的孔洞。若没亲眼见过绝没法想象,富丽堂皇的皇宫之内,还有着这样一个地方。
忽然有凄厉恸哭合着器物摔落的声响一起传来,哭声中仿佛还夹杂着谁清冷刺骨的嘲笑声。闹了一阵,未等到七叶走至就已经渐渐低了下去。灰色院落忽然变得无比安静,仿佛其中根本就没有半个活物一般,既冰冷,又死寂。
七叶踏入院门中,哼着那首《情狂》朝着那一排一排看起来丝毫无异的屋子走了过去,一直走到了第十九间的时候,终于听到了些不一样的动静,简陋花窗窗纸上透出来了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人影似乎有些情绪激动,细瘦指尖极用力地抓着窗沿,将窗纸都抓破了一些。
七叶停下脚步,低声问道:“是阿谣姑娘吗?”
人影忽然剧烈地颤动了一下,有些恍惚地低声喃喃念了一句阿谣,半晌后才微弱着声音慢慢说道:“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叫过我阿谣了。”
“可介意请我进去一坐?”
“只怕屋内太过湿寒,姑娘呆不久。”
等了许久,门慢慢打开,现出一个身形单薄消瘦的人来。乐谣手扶门扉,面色苍白没有半点血色生气,羸弱得好似随时准备断气一般:“还劳烦姑娘帮我一把,扶我进去。”
七叶无言地点了点头,将乐谣搀扶着走至床榻边,只觉得压在臂上的重量又轻又沉(轻的是久病消瘦,沉的是生气不足以支撑身体),顿时觉得无比心酸。想着这个当年日夜抚琴不措却无丝毫疲态的小姑娘,怎么如今就落成这副模样了呢。
乐谣坚持不肯躺在床上,坐在床沿上上缓了一会儿,微弱着声音费劲地说道:“这冷宫里除了那些按时送来吃穿用度的宫人,平日里谁都不愿靠近,我已经很好多年没见过生人了,无论姑娘是为何事而来,我都很感激。”
是啊,没事谁愿意来冷宫里边呢?
七叶暗自叹息了一声,起身想给乐谣生个火取暖,四处扫视了一圈,别说炭火了,就连火盆都没找到一个。
“不介意的话点个烛火吧,至少看起来显得暖和一些。”乐谣拢了拢依旧湿寒的薄被,自嘲道。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七叶想了想,问道。
“若是往前些时候倒是还有……如今,却是不必了。”乐谣笑着微摇了摇头,在冷宫待了这么多年,再多的执念也早被磨尽了,如今将死,又哪里还能生得出来什么执念。
“姑娘找我是为何事?”
七叶从袖中将从文杰处得的玉佩取出,交至乐谣手中:“我来找你打探洛神花的下落。”
“洛神花……”乐谣盯着玉佩发愣了好长一段时间,却并没有直接说出来洛神花的下落,而是问道:“多年不见,文大哥还好吗?”
“他……”七叶迟疑了一下,道:“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是吗?”
乐谣闻言显得有些黯然,想着年少时还曾和他一起玩笑说要活得久一些,最好熬成千年老王八把世间流传的曲乐全学会,如今却是一个比一个的短命。
“他知道我在这里吗?”
“不知。”
“老师告诉你我在这里的?”
“没有,我找遍了宫里,最后来的这里。”
“是吗……”
“……”
“姑娘看起来不像是宫里人,是为此特地从外边来的吗?”乐谣沉默良久,冷不丁地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我还以为,我装得很像了。”七叶吓了一跳,几乎要惊出一身汗来。
“是挺像了,可你不该哼那首曲子,这后宫里边已经很久没人敢提起过这曲子了。”乐谣微敛着眼眸,目光扫过不远处桌案上一张琴弦尽断的古旧桐木琴,她终于能够完美地演奏出来那首曲子,然而琴弦已断,她的命也终将要断了。
“不敢提起,不代表就忘了。”七叶扫了一眼那把桐木琴一眼,问道:“要再弹奏一次吗?”
乐谣微言眼睛一亮,骤然又暗下来:“等不到了。”说罢,兀自闭上双目,又沉默了良久,才缓缓说道:“你要找的东西,在我族本家,凉国极北的天弃山脉深处。我还没回去过不知道具体位置,不过,你可先去琅州神音府设法取得一份信物再去,会省事很多……”见七叶没反应,又继续道:“若无事,便早些离开吧,眼睁睁看着有人在自己面前死去不是件有趣的事。”
七叶将头发割下来几寸长的几小束,和断开的琴弦撵在一起接上,又从身上摸出来一个装血的竹管,将琴弦放进去盖好,刻上符文等了片刻,取出,重又装回了桐木琴上。当乐谣正一句久过一句幽幽地将劝慰七叶离去的话说完的时候,七叶正好按着琴弦,发出了试音的第一声响。
乐谣闻声骤然睁开双眼,浅赤色的双眸似有火焰燃起,明亮得仿佛回到了十余年之前,她还在乐府中的时候。她只觉得已经枯竭的身体里复又生出了无穷力气,心火燃烧,身体中冰凉许久的血液像是沸腾了一般,难得在苍白的肌肤上映出来了些许血色。
这一刻,仿佛连再严寒的风雪,都动摇不了她单薄的身体一分了。
她忽然掀开被子,赤足向着琴案奔了过去,指下有清悦琴声从容响起,开篇的喜悦一如多年前,未曾改变……
曲罢,琴弦复断,一声似凡女魂断神域外的决然突兀响起,桐木琴上忽然飞出来成千上万只蝴蝶,它们穿过破损的窗纸,飞过长满杂草落满枯叶的小道,飞过檐下悬挂声音清脆的檐马,飞过鲜花盛放如春的御花园,飞过乾天宫前盘龙飞凤的汉白玉,飞过那所古韵深远的乐府,应着冷宫第十九间屋子燃起的火光,将最后的绝响,燃在了寒风之中。
皇宫里再没有乐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