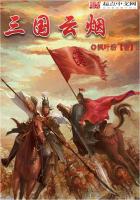曹谦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找到冯老神医,不想他就这么将曹谦和冯老混撂在当场,曹谦先是一愣,然后看看冯老混。
“哥哥,都是小弟我不成器,连累哥哥。”冯老混一咧嘴,挤出来一个要多难看有多难的笑容。
“你别动,我去请他老人家。”曹谦说着要抬腿迈步准备进屋。
曹谦刚走到茅草屋的檐下,冯天出来了,俩人差点撞了个满怀。
冯天的身上多了一个竹编的箱子,挂在肩头上,曹谦在近前闻到一股轻微的药香。
“哼,跟初九这厮混在一起,断不是什么善类,看在你帮我一次的份上,就让我跟你去一趟吧。”冯老神医不躲也不避,他比曹谦矮半头,用鼻尖对着曹谦的下巴说道。
“哦,老神医,您怎么知道我是来找您的?”曹谦一见这老头儿的眼力还挺毒,觉得挺惊讶。
“我是老了,可眼睛不花,你断不可能来找单保夫妇,除了我,你还能找谁?你身后还跟着初九那个不孝子,定是他带你找到这里的。”
“老神医精明。”曹谦对冯天一拱手。
“行了,别恁麽说,找我做什么?”
一直没说话的冯老混在一旁插嘴道:“这位是汝阳县的曹三郎,他家父被人打伤,求叔叔救命则个。”
冯天看了一眼冯老混,没说话,单是“哼”了一声,冯老混灰溜溜退到曹谦身后,曹谦看出来,冯天尽管只是冯老混的远房叔叔,但这冯老混挺怕他,赔笑道:“您的侄儿在我这里还算规矩,希望您别太苛求了。”
冯天仍是“哼”了一声,说道:“算了,待我给令尊治一下伤,两下不欠,你我之间就是路人,至于这个初九,俺是一眼也不愿意看到他。”
说到这里,冯老混早就羞愧难当,一言不发。
几个人这就要抬腿动身,单保在一旁忙不迭拱手道:“几位留步,救我们全家则个!”
冯天迈出去的腿又收了回来,看了看单保和他的浑家,叹道:“这如何是好?”
曹谦明白,刚才尽管他出手将那三个恶棍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但连最笨的人都明白,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回头再找几个人回来报复,非但他们的女儿单翠娘要被恶霸抢了去,怕是全家人一无幸免地遭殃,想了想,说道:“几位,咱们这样,神医您跟着我先走,给我父亲治伤,让冯老混带着这一家人回汝阳安顿一下,先避一下风头再做打算。”
冯天略微想了一下,点头道:“也好,初九,这回看你总算有点用处,好做!”
冯老混对叔叔做了一个揖,算是领命。
曹谦将檐下的马拉了过来,先让冯天上马,他随后认蹬上马。
作为一个现代人,怎么会骑马?
曹谦在穿越前,曾带着几个贴心的马仔给一个夜总会老板看场子,一连几个月,没有混混前来捣乱,平安得到保证,夜总会营业额翻番上升,夜总会老板非常高兴,就掏钱请客,到一处跑马场散心,曹谦于是就有机会接触到骑马运动并为之着迷,他觉得驾驭这个活物跑来跑去的,比开车兜风要有意思多了,从那以后,只要有时间和闲钱,曹谦总要去跑马场消遣一番,想不到,用来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在穿越到宋朝以后,居然派上了用场。
虽然曹谦的骑术并不精,但驾着马一路小跑还是可以的。此时太阳西斜,如果没有脚力相助,怕是天黑了,也断难到达汝阳县。
黄昏时分,曹谦驾着马载着冯天进了汝阳县,穿街过巷,到了他和老曹三的家;曹谦先下了马,站稳后将冯天扶下马。这间临街木楼的大门紧闭,曹谦着急知道老曹三怎么样了,并不叫门,上前一把将门推开,迈步往里进,屋里没电灯,漆黑一片,曹谦的身子刚一探进来,“砰”、“啪”,两个不知名的东西一个打在曹谦的头顶上,一个打在曹谦的左肩,曹谦眼前一黑,左肩也是传来一阵剧痛,好在曹谦反应很快,向后一跳退出门外,冯天在门外也惊得“哎哟”了一声,绕到马的另一侧躲了起来。
曹谦遭到偷袭,被打得头昏脑胀,立即火冒三丈,回头将挂在马鞍上的入鞘长刀拔了出来,对屋里喝道:“什么人,出来。”
“哦,是曹三郎啊,对不住。”有人说着话,立即从屋里走出三个人来,其中有两个人一人一根折断的木棍,曹谦一见都是平时关系比较好的街坊,怒火平息下来,揉了揉头顶,活动一下左肩头,走到这三个街坊的近前,说道:“几位也不是小孩子,开这样的玩笑。”
这三个街坊一个劲地赔礼,其中一个街坊解释道:“三郎有所不知,在你为令尊找大夫的时候,来了几个人,说要限定天亮前把老曹三安顿到别处去,这里他们要占了,刚才三郎你也不招呼一声,推门就进,我们只道是那几个人又来寻晦气,自然要打将出去,不想误伤了三郎。”
曹谦听完街坊的话,虽然表面上平静,实则心里动了真怒,天杀的尹师绮,一直在背后操纵着汝阳县的各路黑道势力,非要将他父子逼至绝境,早晚有一天,他曹谦要将尹师绮踩在脚下!
“辛苦各位了,都回家休息去吧,改日我曹谦定要重谢各位。”曹谦下完了逐客令,三个街坊也毕恭毕敬向曹谦还了礼,都各自回去了。
“老神医,往里请。”曹谦知道既然对手苦苦想逼,他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将老曹三的伤处理好。
冯天进了屋,曹谦点起了灯,虽然屋里的家什全都打碎,但经过街坊们一番收拾,整洁了一些,老曹三躺在屋当中,身下是从楼上搬下来的木床,在街坊们的照顾下,情况略微好转,有些昏昏沉沉地睡了,因为曹谦回来,他听到有动静,睁开眼睛,正看到曹谦焦急的目光,挤出来一个笑容,说道:“我儿回来了。”
“父亲,都是孩儿不好,连累了父亲。”
父子这头交流感情,冯天那开始为老曹三处理骨伤。
“还不错,这骨正得不错。”冯天看到老曹三腿骨上绑着一根木棍,早将折断的腿骨正了过来,不由得连连称赞。
“不才,是我。”曹谦对冯天一拱手。
“这么说你学过?”
曹谦当然不能说起他穿越前亡命黑道,总要学一些处理各类外伤的手段,只得说:“家父的腿断得不成样子,我只好自己瞎琢磨想办法帮家父治伤。”
“看起来你这厮有点资质,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弟。”冯天说完,不待曹谦回话,独自打开药箱,为老曹三进一步正骨,敷药,包扎。在冯天为老曹三处理骨伤的时候,老曹三看着冯天,说道:“我认识你。”
冯天也点点头说道:“我也记得你,我还吃过你的炊饼呢。”
等都处理完了,夜渐深了,曹谦留冯天歇息,冯天看看外头的天色,只得同意。
曹谦到楼上从一堆破烂中拽出几条絮被,拿到楼下,平铺在地,带着歉意对冯天说道:“老神医,实在抱歉,委屈您在我这里将就一晚,明天我定要重谢。”
“呵呵,俺在乡野间行医,比这里要苦的地方不知去了有多少,连风餐露宿都使得。”在冯天说话的时候,曹谦突然觉得肚子饿,从赶走邹耳开始,接着就是一场恶战,然后就去找大夫,为此又跟人打了一架,直到现在,一直水米未沾,怕是连铁人都捱不住。
曹谦站起身来,从被砸烂的东西当中找出老曹三做炊饼用的面粉,本来已经散落,曹谦小心翼翼地用手将干净的部分(kuai)起来,放在一片被砸烂的铁锅余下的铁片上,接着看到门口那匹马的马鞍上还有一个牛皮水袋,将之取来,淋在铁片上的面粉上和匀,分成几个剂子,挨个摁成饼子,然后到灶台旁升起炉火,待炉火将尽时,将铁片放在红炭火上,然后将挨个将面饼贴在铁片上烙熟,等所有的饼剂子都熟了之后,先是伺候老曹三吃下一个,然后再请冯天用面饼。
“看不出,你倒还有些手艺。”冯天嚼着焦香的面饼说道。
“没办法,人总得吃饭嘛。”曹谦讪笑道。
吃过了饭,冯天因为和老曹三算是老主顾,加上是一个年龄段的人,共同语言总要多一些,就谈了一会儿,在老曹三的眼里,曹谦绝对算得上一个孝子,一个扎实肯干的好孩子。
经过老曹三的一番谈论,冯天对曹谦的态度也改善了许多。
冯天还跟曹谦谈起冯老混。
原来冯老混原名冯延庆,字福,和冯天算是一个族内的亲属,到了冯老混爹妈这一辈,虽然家道有些中落,也小有一些房屋田产,冯老混的爹妈只有冯老混这么一个儿子,因为出生时恰逢当月初九,就作为小名,唤作初九;夫妻二人拿冯初九端的当作掌上明珠,俗语说,惯子如杀子,这句话从古到今应报不爽,这冯老混在爹妈的娇惯下,凡是安身立命的本事,一样不会,倒是吃喝嫖赌,无一不精,冯老混的爹妈,冯天也可以称做他们为同族的堂哥和党嫂,都是没有福荫的人,早早过世,因为家族衰微,族内有人找到冯天,托他照顾冯老混,那时冯天刚刚入门医道,中年气盛,开始欣然接受了委托,然而,没过多久,他看到这冯老混整天介出入瓦子赌坊、眠花宿柳,急得真个是五内俱焚,但毕竟冯老混已经长大成人,连亲生爹妈都尚且管束不住,何况他这个远房的族叔!冯天眼睁睁看着冯老混将爹妈留给他的祖产吃光败净,生活无着,只能和冯二、三卓子等人混迹在一起,一气之下,干脆眼不见为净,冯老混也自觉理亏,再也不敢面见冯天。
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到夜深人静时,曹谦再也撑不住,蹲在墙根处,眼皮一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曹谦梦到一阵马蹄声,紧接着一阵肃杀之气渗透入骨,好像数九寒冬的风,让人从骨髓处感受到寒冷。
“嗯?”
曹谦猛地惊醒,虽然周围仍是漆黑,但是他分明听到门外有声音,尤其那声音,曹谦听上去就像是用一盆水泼在门上,曹谦尽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直觉驱使他悄悄站起身,伸手将缴获的那柄长刀抄在手中,因为门有缝隙,曹谦将长刀对准缝隙,用力一插,一声令人感到骨缝发麻的惨叫声,隔着门传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