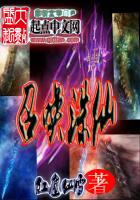入监后的第十三天上午,刚到工地半个小时,“苏生,接见。”
“终于来了,家里终于来人啦。”以前在看守所,那是知道根本见不了,现在不一样了,这几天身边的同犯一个个接见,快急死了。
教育监区十几个会见的排成两路纵队,干部领着去接见室。“谁会来呢?父亲?哥哥?还是姐姐?”我揣测着。
十来分钟的路程,到了接见室,里面人很多,玻璃墙很厚,把家属和服刑学员隔开,靠电话沟通。我急切地找望向家属入口,却没看见人。
“教育监区学员苏生,到15号窗口会见。”接见室广播里传来声音,我赶紧跑到15号窗口,父亲已经在等着啦。仅仅两年多没见,老苏老得厉害,头发几乎白完了,腰也佝偻着。
拿起电话,老苏没有责怪我:“一接到监狱的信马上就赶过来了,在里面咋样?吃能饱饭不能?有没有人欺负你?”
我去,邮政这速度也没谁了,不到两百公里,邮了十三天。
老苏的问话像面对一个刚被送到幼儿园的孩子,我没有机会也不想告诉他们这里面真实的生活,苦辣酸甜都是我咎由自取。我努力笑着:“里面挺好,不用担心,馒头管饱,没人欺负我。况且我都26了,有事会自己想办法处理的。”
老苏压低声音:“那就好,那就好。对了,来见你之前,我专门去你大姑家了,你记一下电话,以后有啥事跟她联系,她家住在塔北路,离监狱这儿不远。”
看来,老苏是想让我大姑帮忙找关系啦。
我一眼不眨地盯着老苏已经有些浑浊的眼睛,这两年,您过得……还好吧?我很没有底气地问。这个问题愚蠢极了!这些年,我的案子走到那里,他便跑到那里,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去求了多少人啊?看守所给自己送药的宋干部、给自己拿棉鞋的马干部、公安分局的“豪哥”、法院的“林姐”……
老苏没回应我,而是喃喃地交待:“你有胃病,不管好哩赖哩都要吃饱。少吸点烟,对身体没一点好处……”
我听着老苏女人似的唠唠叨叨,眼泪突然就冒出来了。
老苏没享过福,一生都在操劳。他用辛苦赚来的那点可怜的钞票,养活全家五口人,却从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胃病犯了,我娘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却总说喝点热水,休息一会就好了。他期望自己的儿子能靠知识改变命运,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上大二那年,娘因病去世,老苏精神一下垮了。本就话少的他以后更加沉默,也不再外出打工了,整日侍弄着几亩田地,只有在我放假回家时才难得一露笑颜。而现在,他孤零零一个人在家又是怎样度过?他生病了怎么办?他心情不好又该找谁诉说?
我强忍住情绪,转了一下头,快速把泪擦掉,扬起头笑笑说:“监狱里伙食比看守所强多了,每个星期都有肉片大米饭呢!活儿也不累,况且早习惯了。对了,我的事情你不要再奔波了,已经这个样子了,你年龄大了,顾好自己就行了。对了,我哥和我姐怎么样?”
老苏:“你哥人在山西,开车开了这么些年,工资倒也一直涨,可市里房价涨得更快,一直买不起,那边战友有点关系,去包点活儿干干,打算搏一下。你姐在家带孩子呢,两个孩子离不开。”
“嗯,没事,就是挺想他们的。”嘴上说没事,心里还是有点淡淡的失望。
回来车间已经收工了,白背心跑到我的监舍:“家里来人了?我烟吸完了,先给我拿条烟。”我说就一条,拆开给他拿了几包,白背心很不高兴地走了。白背心没满足,以后肯定会故意找碴儿。晚上,我给眼镜监舍长也扔了两包,监舍长明显露出不屑,可还是接住了。
监狱里抽烟真是太方便了,从超市里就可以买到香烟和火机,而看守所都是黑市交易,还经常没火机,就得搓火,从被子里撕点棉絮卷点********,用鞋底子在水泥地上猛搓,不一会儿就着了。但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搞到********,就只能用洗衣粉替代了,洗衣粉不太好搓,费劲。
老蒲有哥哥的关系,已经去了生活监区,最起码这几年吃喝有保障了。我呢?也许只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了。
第二天到工地后,我试探着问白背心,“组长,你认识江风吗?”
白背心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压低声音说:“你认识他?他可是教育监区的牛B人物,姐夫是监狱里的领导。”
巧了,江风居然真的在这儿,还真的留在了教育监区。“嗯!在外边就认识,朋友。”我说谎了,我担心如果说是两人在看守所认识的,白背心会不说实话。其实,江风和我只是在看守所一个号里呆过几个月。
“他是文教上的,平时出工去教务中心,星期天会来工地。”白背心显然对江风很熟。
教育监区罪犯构成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占绝大多数,就是刚从看守所送来的新人,第二部分是留教的,前面说过;第三部分就是文教的,一共有三十来个人。
本来想多了解一点江风的情况,突然车间里又打起来了,这次是戳鞋底台子上的,还是老套路,新人不服气,还手,留教的一拥而上,新人被痛打一顿,然后去反省。谁知这新人挺志气,咽不下这口气,瞅着机会,跑到鞋底台子上,抄起一个戳刀对着刚才打他最狠的那个组长就捅。平时耀武扬威的组长碰见横的也怂了,转身就跑,两个人围着台子转了好几圈。
眼看就要见血,不管不行了。值班干部提了副手铐出来,指挥组长们一拥而上,把那个新人按翻在地,带上手铐,拖回监区挂在监舍走廊的铁窗户上。为了杀鸡儆猴,这一挂就是三天。
每天收工回到监舍,都可以看到奄奄一息的新人,这将是监狱给他也是给我们这些新人上的重要的一课。
这次白背心没有说谎,星期天的时候,文教的人来了。一进大棚,他们便迅速分散开来,隐藏到车间的各个角落,找把司(关系好的罪犯)喷空,反正他们没有生产任务。
白背心把话捎到了,江风来找我了。“啥情况?怎么来这么晚?我第一次减刑监狱都公示了。”江风说。
“我倒是想早点来找你,可也没办法啊!”我简单把同案上诉法院驳回重审区检察院撤诉市检察院重新公诉中院审理后全部加刑只好又上诉又被驳回维持原判的情况简要说了一遍。
江风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后皱着眉感叹,六年好好的,上什么诉,现在十一年爽了吧?我只能苦笑。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生活监区卖小伙儿的推着车进车间了。“想吃什么?我去买。”江风问我。我说不饿。江风执意去买了苹果和包子,回来让我吃,我给白背心扔了两个小笼包。江风凑到我耳朵边小声说:“你不要管他,自己吃饱就行了,他们留教的都是杂碎。”
虽然都是教育监区的,但江风住在一楼,我们新人住二楼,在监舍是见不着面的,江风交待我缺什么东西让人给他捎信。第二天,一个负责新人训练的组长找到我,扔了五盒烟,“江风给的,先吸着,拿多了白背心该给你下了。”江风心还挺细,我笑笑接过烟。
江风从小家庭条件优越,有姐有哥,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对其娇惯的不得了,所以也养成了任性的性格。江风从小就聪明,读书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全班乃至全校第一名。高考时这家伙更绝,一门功课因为打游戏错过了时间没能进去考场,就这分数居然达到了二本线,可怕不?毕业后,他顺利留在省计生委工作,后来因为厌烦了那种无聊的生活,出来开过网吧,在自家厂里当过业务员,钱没少赚,可也染上了一个坏习惯——赌博。
开始他还是和熟悉的朋友一起玩,也不是太大,一场下来输赢几万块。时间长了,赌瘾越来越大,他开始玩“推饼”,两张牌,一翻一瞪眼,速度超快,一晚上下来输赢至少几十万。这个时候,不管江风愿不愿意承认,他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了。
几个经常与江风在一起玩牌的知道他家底厚,便三个人合伙前前后后赢了他二百多万。所谓当局者迷,江风当时光想着翻本,从来没想过他们出老千。直到一个圈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点醒他。江风知道真相后,越想越气,便去找他们要钱。可到人家手里的钱那能那么容易要回来,三人当然不愿意。江风一气之下,把其中一个赌徒的儿子绑了。
后来的事情不用细说了,2005年底,江风被刑拘,被关到新乡市看守所。家人多方打点之后,江风因为绑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没办法,绑架罪起步价就是十年。
江风进去三个月后,我也进了看守所。不过当时我在A9,江风在A10。我在A9呆了半年多后,调到了A10。
江风喜欢拉着号里人斗地主。这个豫北小城,斗地主就像成都的打麻将,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从小就会打麻将,但对纸牌一窍不通,斗地主还是刚进看守所在A9的时候半推半就学会的。刚进A9的时候,号头说咱们斗地主吧,我说不会。“不会可以学啊,我们教你.”学了一夜之后,号头说咱们赌方便面吧,一次一包八毛钱的天方小面。我想了想,说:“中!”此后的一段时间,我每天基本上都要输个二三十包面。
其他人都偷偷说我是个傻B,号头坑你呢!我笑笑也不反驳。
我一个外地人,一米七三的个头,体重125斤,脸上架了副七百度的啤酒瓶底儿,想不受欺负,你教教我应该咋办?还有,我帐上的钱不是家里送的,是老板的。我们进来后,老析让人每个月固定几次来送钱,不算多,但是很勤很准时。
几天过后,效果就出来了。号头时不时地给我扔支烟,穿灯泡一天穿个三四千就行了,刚来时一天六七千个。
调到A10后,江风让我报了报家门,然后问会不会斗地主。我开始还以为A10的斗地主把戏和A9的一样,玩了几次之后才知道江风家庭富裕,才看不上那点东西,纯粹是消磨时间。
相处了几个月,江风很喜欢找我聊天,问一些我上学的情况,给我讲一些自己的经历。2007初的一天,江风要投牢了。临别时他说:“我姐夫在中河监狱,如果你也投牢到哪里就找我吧。”我说我的户口是本地的,按照异地羁押的原则很有可能也被扔到中河去,有缘在监狱里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