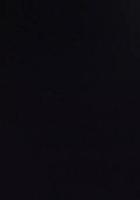斑驳树影的山道上,远远地,迎面走来一个人。
这人背着一担小山一样的柴禾,低着头一步一晃地向他们走来。身形交错的刹那,这人猛地抬起头来,眼光犀利地落在我身上。
一望之下,我感觉浑身像被透视般地不舒服,我下意识地别转了头。
大约走出去五米左右,从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太阳要落了,别往上走了。”
我们四人几乎同时转身,视线全都诧异地投射到那个背柴的樵夫身上。只见他六十出头的年纪,沟壑纵横的老脸,饱经沧桑的眼睛,此刻,他正面向我们站着,脸上隐隐透着不安之色。
胡东疑惑地问道:“大爷,您是和我们说话吗?”
老樵夫皱着眉道:“除了你们这附近还有别人吗?”
胡东面露惊讶之色:“您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山?这山上……”
“这山上倒没什么,只是山顶上那所房子去不得。”老樵夫闷哼一声道。
阿杰眼光一闪,几步奔到老人身前,指着“鬼屋”的方向急切地问道:“大爷,您说的是那里的那座‘蘑菇房’吗?”
老樵夫吃惊地望着阿杰,点头说道:“没错,从这往上除了那所房子就没别的了。怎么?你去过那里?”
阿杰不理会老人的问话,继续追问:“大爷,您为什么说那房子去
不得呢?”
老樵夫抬起布满血丝的老眼,下意识地朝着“鬼屋”方向望了一眼,脸上瞬间积聚起一团阴寒之气,他叹了口气,闷声说道:“那屋里原来住着一个老妇人和她女儿,他们不是本乡本土上的,是从外地迁过来的,听说那老妇的女儿长得很标致,而且是即将要结婚的女人,幸福过着每一天的生活,但就在试婚纱回来的路上被人强奸了。她妈妈知道后却骂她说要不是你愿意怎么会被强奸,并且给了她一片药让她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最后那个女孩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躺在自己的新房的床上割腕自杀了,她的鲜血把那洁白的婚纱染的通红。
说到这,老人顿了一顿,神秘兮兮地说:“告诉你们说呀,有人晚上经过那儿的时候,听到屋里边有女人哭呢,阴惨惨的,可吓人了。”
我听得头皮一阵阵发麻,一颗心“呯呯”乱跳不止,我胆战心惊地问道:“大爷,那女孩的妈妈呢,后来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问到了大家的心坎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了老樵夫脸上。
老人眼中再次掠过一丝忐忑,声音喑哑地说道:“她妈妈最后自杀了,但那女孩的尸体却不见了。听说后来警察,找遍了整栋房子,就是找不到尸体,也许,是被她未婚夫带走了吧。真是怪呀。”
听着听着,我眉心拧成了结,心情沉重地问道:“那女孩的妈妈尸体怎么处理了?”
“埋了。”老人叹息着说道。
“埋在哪里了?”阿杰紧张地问道。
“还能埋哪?我们这儿不兴看风水,就用滚鸡蛋的办法选坟地,在蛋摔破的地方挖个坑埋人,埋完后再用土填平,不建坟堆的。那可怜的老妇就是这么埋在她们家房子边上了,也就十多米远吧,不过,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可记不得了。所以啊,我每回从那儿路过都绕着走,生怕踩着她的坟地啊。”
一席话说得我脸色煞白,因为,自己上一次很可能踩到了那老妇人的坟。
“差不多就回吧,天黑了会迷路的。”老人丢下这句语重心长的话,便背着硕大的柴堆艰难地向坡下走去。
望着那座行走着的“柴垛山”,我只觉后背一阵阵发冷,我的眼前反复上演着那个鬼屋之夜的某个片断,那诡异的背影像毒蛇一样缠上了我的心,我的脑,以至我的全身。
“上山还是下山?大家想好了吗?”
“当然是上山。”阿杰和胡东几乎同声回答。
而邱国则试探性地问道:“或者我们先回去,明天白天再来?”
“不!”阿杰语气很重:“反正要去,白天晚上又有什么分别?也许在夜里,我们可以得到更多关于怨灵的信息。”
胡东更是苦笑着加了一句:“鬼真要杀我们的话,随时随地都会下手,之所以现在还让我们活着,很可能是在给我们机会,最后的机会。”
当那栋丛林掩映的“蘑菇房”再次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不知不觉间,起风了,一切都和一个多月前一模一样……一个月前那个诅咒之夜再一次浮现在我脑海之中。
“真是谢天谢地,这下不用淋雨了。”李刚边说边打了个喷嚏,第一个跑上去敲起了虚掩的院门。许久,里面也无人应答。
细心的阿杰突然皱着眉头说道:“这门上怎么这么多蜘蛛网啊?好像很久都没人住的样子。”
“是吗?”急性子的韩建一下子挤到门前,下意识地用手一推。
门开了,院内的一切也随之袒露出来。
荒草遍地,几只受惊的麻雀扑打着翅膀从草丛中飞起。
“满院子蒿草!都没人打理的?看来真没人住啊!”韩建好奇地说道。
“不是吧?咱们不会这么倒霉吧?好不容易找到一栋房子还进不去!”李刚最初的喜悦已被强烈的沮丧代替,转身便要离开。
“唉,别急着走啊!反正来都来了,好歹进去看看,兴许屋里有人也说不定啊。”阿杰叫住李刚,和我撑着伞从韩建身边走过,径直走向正房前的石阶。
“要命啊,这么多蜘蛛网!”阿杰一边抱怨,一边用伞尖打落门上的蛛网。
“门虚掩着,好像没锁。”我取出纸巾,小心地垫在门把手上,用力往外一拉。
伴随着房门的开启,一股夹杂着霉味的灰尘扑面而来,直呛得我忍不住捂着嘴打了个喷嚏。
阿杰捏着鼻子倒退几步,整个人再次暴露在大雨中。他向院门边的同学招了招手,高声喊道:“门开了!快进去躲雨!”
六个人陆续进入厅堂,由于阴雨天的关系,厅内的光线相当昏暗,不过,我们还是在最短时间将厅内陈设打量一番。木板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靠东墙的角落里散乱地堆着桌椅等杂物。厅堂中心有一个火塘。
“啊——”韩建突然发出一声夸张的惨叫,大家顿时吓了一跳,转眼间汇集在他的身边。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那……那里!”韩建左手却哆哆嗦嗦地抬起,指向自己头顶的斜上方。
不约而同地,大家沿着他的手指方向紧张看去。
“啊——”不知是谁再次发出一声尖叫,尖叫声中,所有人的视线都被眼前那张硕大的蜘蛛网牢牢粘住,呼吸几乎在刹那间骤停。
那张从顶棚铺张下来的大网上,爬满了至少近百只蜘蛛,最近的几只就在韩建头顶不足一尺的地方,悠闲而自在地蠕动。
这个数量已经足以令人吃惊,而这些蜘蛛的身形却更令人望而生畏。它们每一只都足有乒乓球大小,就那么八爪鱼般张着脚伏在灰网上,而那张大网则随着蜘蛛们的蹬踏而微微晃动。
“真是少见多怪,我以前在山里经常见到这样的蛛网,甚至还有比这更大的蜘蛛!比如一种虎纹捕鸟蛛,只只都有碗口大!有的还带剧毒呢!”李刚不以为然率先打破平静。
“那这些蜘蛛有没有毒啊?”韩建胆子最小,此刻吓得声音都变了。
李刚大大咧咧地说道:“放心好了,它们没毒的!顶多是看着恶心罢了。”说着,他便向中心的火塘走去。
刚到近前,火塘内突然“蹭”地一下跳出一道黑影,重重落在地上,还没等大家看得清楚,这个一尺多长的动物已经从人群中穿梭而过,夺门而出。
“吓我一跳!是野猫吗?”胡东拍着胸口说道。
李刚笑笑:“是只老鼠。”
“那么大的老鼠?”我们同声惊呼。
李刚眼睛一翻,戏谑道:“云南十八怪——三个老鼠一麻袋嘛,亏你们还是大学生呢!怎么好像外星人一样,啥都大惊小怪的!”
阿杰嘴巴一撅,上去就向李刚背上捶了一拳:“别啰里啰嗦的,快把火塘升起来烤火啊,浑身都湿透了,难受死了。”
“yes,小的这就去准备,请各位老爷稍候。”李刚做了个鬼脸,转身几步就窜上楼梯。
阿杰突然顿了一顿,眉头微皱地望着我:“阿航,你不觉得奇怪吗?这么大一栋房子,竟然长时间荒废着没人住,而且连门都不上锁。”
“也许……屋主搬到别地方去了吧。”我话音刚落,就听一阵“啪啪啪”沉重的脚步声响,李刚已经从楼上跑了下来,怀里抱着一抱木柴,嘴里大声喊着:“大家伙儿动动手,帮忙找点儿废纸破布什么的!”
阿杰和我答应着往厅堂右边那个房间走去,胡东也紧跟着过来。当三个男孩踏进那扇敞开的房门时,立即感觉到一阵扑面而来的冷风,这风来得异常突然,而且也异常阴冷,令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激灵。
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我的眼睛飞速地在室内逡巡。很快,我便注意到那扇少了两块玻璃的窗户,以及窗子上摇来荡去的一个布娃娃。不知何故,在我的视线碰触布娃娃的一刹那,我的胃就像被什么东西搅动了一下,一阵痉挛。
这是个极其特殊的布娃娃,绝对不是在商店里买来的,而是经过粗糙手工缝制的,因为那娃娃身体的比例极度的不协调,短小的四肢,大大的头颅,身上没有套任何衣服,从头到脚都是雪白雪白的,那个大大的脑袋上竟然没有缝上五官,只在头顶钉着两根红绳编制的粗粗的长辫子。而两个辫梢又都被栓在窗框上,所以,这个怪异的白布娃娃才会在窗子上随风摇摆,跳着诡异的舞蹈。
我径直走向那个白布娃娃,并且用手抓住了它的一只脚,于是,娃娃像钟摆停摆般静止不动了。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娃娃,心里总觉得怪怪的,可是又说不出怪在哪里。这时,身后传来阿杰的声音:“你们看,墙上挂着照片呢。”
我应声回头,只见阿杰正指着墙上的一个奖状大的玻璃相框向我招手,随后,他又抽出一张随身携带的纸巾,麻利地拭去玻璃表面的灰尘。
三个男好奇地聚在相框前,玻璃板背后的几张照片很快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很显然,照片上的是一个三口之家,老奶奶、年轻夫妇除了一张三人站立的合影,其余大部分都是年轻母亲和孩子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很高,身材也很魁梧,一张脸十分俊秀,而他的女人则显得娇小玲珑,样子也清秀端庄。
但这个家庭里的人们,又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