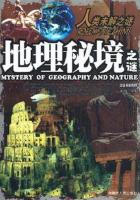陈景佑瞥一眼妘璃,问他:“那你想怎么罚呢?”
古梭想了想:“就换她给本王捡猎物。”说罢,向身边的侍从使了个眼色,侍从马上将背上放着死畜的竹篓取下递给妘璃。
竹篓里的猎物大多是一箭毙命,奄奄一息的也流了不少血,不多时也会死了。妘璃紧皱眉头接过竹篓,眼睛一闭将它背在身上,闻着血腥味直想作呕。见她这副难受的样子,古梭露出满意笑容,骑着马向一片林子去。
妘璃跟上他的狩猎队伍,经过陈景佑时向他请求:“公主在南面,还望南郡王替奴婢向公主殿下知会一声,奴婢晚些跟她请罪。”
古梭虽有为难之意,但其到底是西凉皇子,想来也不会鲁莽,但是陈毓馆行事冲动,这会儿等不到妘璃将猎物送去,也不知急成什么模样,可万不能在西凉人前丢了脸面。想到这儿,陈景佑赶紧往南找去。
而另一厢,古梭狩猎最喜速战速决,他带在身边的侍卫又都是最能跑动之人,他的速度要比陈毓馆快了不知多少。妘璃才捡了一只猎物,古梭的队伍就已经跑开了数十米,照这样妘璃根本追不上他们的脚步,无奈之下只好自寻近路,赶抄上去。可恰恰好的,也不知妘璃近日是冲撞了什么,事事不顺。眼看赶在与古梭同行的树林边上,古梭突然将箭一转,急速而发。
妘璃只觉小腿钻心一疼,一记踉跄摔在地上。有人跑来,拨开草丛,是西凉侍卫。他见射到是个人,大声向古梭禀报。正要赶往别处的古梭一听骑马过来,见是妘璃,双眉一皱,镶玉长弓掷在地上,大怒道:“不是让你跟在本王后面,谁让你出来的!”
妘璃忍着痛,牙齿不停地打颤:“奴婢捡回猎物时,皇子已向别处出发。奴婢的双腿不如皇子马儿的快,便想抄近路……”
古梭不耐烦地来回瞪了她两眼,下令道:“时间也差不多了,回罢!”
随身侍卫颤颤提醒:“可是皇子,我们今日猎的这些,恐怕不足以取胜。”
古梭指着地上面色苍白的人振愤道:“自这个丫头冒出来就扫了本王的兴,现在完全没了兴致,给我回!”
“古皇子息怒。”妘璃双膝跪好,咬咬牙握住那根光滑的箭柄,闭着眼往外一拔,险些疼得叫出来。她死死咬着下唇,待到稍能喘息,双手将长箭呈上,“还请古皇子息怒,奴婢自当再领罚。”
对于又见惯打斗血腥场面的古梭来说,自己的箭上即使沾上再多猎物的鲜血他都不以为然,可以说压根不曾注意这面上的血是多是少,是什么颜色。可独独面对这只箭时,鲜红的血色夺目刺眼,顺着箭身顺着她那双发抖的芊芊玉手缓缓淌下,一时间他竟然语塞,甚至惊讶。他总以为中原女子都是柔弱无能,尤其是那公主更是不入他目,却不想眼前这个女子竟能有这般勇气,着实让他出乎意料。
他沉着脸拉紧缰绳,一夹马腹,向营地奔去。
皇帝正和大臣在营帐中喝茶聊天,来报古梭归来,心下不由一惊。出门一看,果见古梭站在马儿前,脚边放着两只装着猎物的竹篓。
皇帝大笑道:“古皇子第一个回来,想必打了很多猎物吧。”
古梭低声一笑,叹口气:“惭愧,中途不小心伤到了陈国宫里的人,所以便先赶回来跟您请罪。”
说着,妘璃被两个西凉侍卫拉着左右胳膊丢在地上,腿上的箭伤因为被带着强行奔跑而撕裂得更大,一路上流血不止。此时的妘璃疼得只剩一丝力气,撑着双臂在地上跪着,吃力说:“奴婢光华殿宫女妘璃,奴婢知罪。”
那边古梭又叹:“既然是公主殿下的人,我便更要受罚了,恐怕公主也要怪罪我了。”
皇帝笑道:“皇子哪里话,是她鲁莽了!”说着,向边上的太监使了个眼色。
太监搀起妘璃,将她带到陈毓馆的马车边上,不闻一声便走了。
腿上的伤口还在冒血,妘璃用手帕暂时将伤口捂住,幸而本次狩猎时间已到,不一会儿陈景佑便带着陈毓馆回来了。陈毓馆原本很是生气,得知妘璃受伤,又跑来看见地上染了许多血滴,心肠软了下来,让浮香去请太医。
妘璃愧疚不已,一个劲地向陈毓馆请罪,陈毓馆远远盯着正在喂马的古梭气愤道:“若不是那个人有意刁难,我又何必生气,你又何必受苦。宫女做错了什么找主子便是,难道还轮得到他教训我的人?!”
妘璃低着头,也不知说什么才好,今日狩猎这一桩桩的事儿,如若当初能够细心一些,也不会落得现下这般。古梭是来和亲的,可见他的意思似乎并不喜欢陈毓馆,这已然是件糟糕的事,现在陈毓馆又因为她对古梭视如恶敌,她实在是罪该万死!
回到离宫,浮香服侍陈毓馆去了,妘璃按照太医给的方子煎好药,打算早些休息。屋外忽然有人敲门,妘璃扶着墙打开,外面站着一位年约二十的将军,虽身穿黑甲手中提剑,但盔帽已经卸下,应该是刚刚巡查完毕。而妘璃一眼就认出了他,有些受宠若惊,也不由紧张起来。他递出一瓶红盖小瓷瓶,说:“上好的金疮药,对伤口很有效。”
妘璃温婉而笑,低眉顺首:“奴婢谢过虞将军,太医已为奴婢开了方子,这药将军还是拿回去,在战场上它对你更有用。”
虞舜夫道:“现在又不是战场,我也没有受伤,它对于我来说根本无用。你还是收下,这西山之行恐怕还需几天,我有责护好每一个人周全,也不想因为任何一个人耽误此程。”
妘璃眨眨眼,双手收下:“是。”
屋顶传来碎玉落珠的声响,灰蒙的天空突降大雨。正准备离去的虞舜夫望着这突如其来的阵雨皱紧的眉头,而耳边传来一声轻语:“下雨了,如若将军不嫌弃奴婢屋里的茶,不如避一避再走吧。”
虞舜夫本无意多留,可这雨实在太大,晚上还需值夜,身上这衣服还不能更换。思来想去,便步入屋中,坐在向门的位置。妘璃小心为他沏上一杯茶,微笑说:“说来还没来得及谢谢将军的救命之恩,当日若不是将军,奴婢恐怕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我?”虞舜夫奇怪抬起头,全然将那日之事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