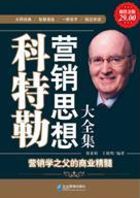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对于状况的判断常失去客观性。当情况需要我们找出一个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便依赖我们记忆中过去所发生的事,或者依赖过去一度成功过的解决方法,这是解决问题最常见的方法。把解决过去事件的办法搬来解决当前事件,这种问题解决方式怎么能够行得通呢?结果花在擦屁股上的时间远比解决问题本身要长得多,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弄清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虽然会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功”嘛。
杀鸡用不着牛刀
管理者日常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是真正的普通情况,而其中的个别事件只不过是一种症状。像对存货处理的决策实际上不能称“决策”,只能说是一种类似于杀鸡的“处置”。这类问题是普遍的。与其说是决策,不如说是生产中的事件。
工厂中的生产管制和工程单位,每月要处理的这类问题成百上千。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类问题都只不过是一种症状,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重要的情况。
生产部门的程序工程师或生产工程师,都只在工厂中的某一部分工作,所以他们通常都看不出这种情况。他可能每个月都碰到蒸汽管或热水管接头故障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但是只有经过几个月对这类问题的大量分析之后,才会发现作为普遍问题的性质。于是他们就会发现,由于温度或者压力太大,超过了设备的负荷,需要重新设计接头。而事情往往是,在他们得出这一结论之前,生产部门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修理接头。
第二类是实质上仍属普通的问题,但却以特殊的形式偶然出现。
例如某公司接受了另一家公司的合并建议,之后便不会再接到同样的建议了。就个别的公司以及它的董事会和经理而言,这是一件不会再重复的情况。但它当然是普通的情况,它在各处不停地进行着。在思考接受或不接受合并的建议时,要考虑一般的规则。为此,他必须参考别人的经验。
第三类是例外的真正特殊的事件。
在1965年11月间,美国的整个东北部地区从圣罗伦斯到华盛顿州,发生一次全面停电的事故。按照初步了解,这是一次真正的特殊事件。又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孕妇服用“太利多迈”而导致产出畸形婴儿的悲剧,也属于这类性质。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说,这类事件的发生率只是千万分之一或者亿万分之一,发生过一次之后,恐怕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例如,我们所坐的椅子分解成原子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复原。真正特殊的事件是极为稀少的,但无论什么时候,当这类事件出现时,我们必须问一问:这是真正的特殊事件,还是另一种普通事件的首次出现?
第四类是新的普通问题的第一次出现。这是决策过程中要处理的最后一类事件。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像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停电和“太利多迈”药物的导致婴儿畸形这类事件,在现代的电力技术和医药学条件下,只不过是频繁出现的不幸事件的第一次出现,我们可以寻求到普通的办法来解决,这类事件是不会再发生了。
除了真正的特殊事件外,所有的事件都需要用普通的办法去解决。就是说,需要制订一种法则、一种政策和一种原则。一旦我们制定出一种正确的原则,类似问题的处理就易如反掌。换句话说就是,类似问题再度发生时,就可根据原则去处理了。但是,如遇到真正的特殊事件,就必须个别对待。特殊事件是不能用一条普通的规则去处理的。
有成效的决策人常常要花费时间来确定问题的属性。他明白,如果他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那他就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显然,我们最易犯的错误就是将普通情况当作一连串的特殊事件来处理。换句话说,当其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而缺乏一条处理原则时,就会实用主义地来对待每一事件。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挫折和无效。
我认为,肯尼迪政府许多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失败,正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错误。肯尼迪总统手下自然有许多杰出的政府官员,但却只做成功了一件事,那就是处理古巴导弹危机。除此以外,这个行政当局没有做成功任何事情。其主要原因就是其内阁成员也已承认的实用主义。
换句话说,他们拒绝建立原则,而坚持“就事论事”。然而人人都看得清楚,甚至他们自己也都清楚,他们所赖以制订政策的基本假定,他们关于战后形势的基本假定,无论是在外交事务或者内部事务中都已经变得不现实了。
另外一种常犯的错误是,误将真正的新问题当作旧问题来处理,因而仍然应用旧的原则。
正是由于这种错误,使当时纽约及加拿大安大略一带的局部停电像滚雪球似的扩展,导致整个美国东北部的停电。开始时,地方的电力工程师,特别是纽约市的电力工程师,应用处理正常超负荷的原则来对付当时的局部停电。但是,他们的仪表已经给出信号,表示有某种特别的故障要求用特别的而不是惯常的方法去处理。
与这种错误的做法相反,肯尼迪总统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时获得巨大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接受了这次挑战,把它看作是特别的非常事件而认真加以思考。当肯尼迪总统做出决策之后,他的智慧和勇气就发挥了作用。
第三种常见的错误,就是对基本问题的似是而非的确定。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军方因未能使高素质的医官继续服役而烦恼。曾经有过无数的研究和建议。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说——薪酬不够作为出发点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军队医药制度的传统结构。美国的军医制度一向重视普通医师,这和今天重视专科医师的潮流相违背。美国军医系统的晋升制度,是专业医生晋升到军医行政方面去,这就使医务人员脱离了高深医学的研究和专科实践。因此,受过很好训练的年青医生觉得,在军队中服务只能做普通医生或晋升做行政主管,这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才干。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发展他们的医学才干和成为一位专科医生的机会。
直到现在,美国军方还没有大胆面对这个基本决策。美国军方是不是甘心让他们的军医院成为第二流的军医院,让那些不能成为一流人才的医生充斥他们的军医院呢?他们是不是愿意将军医院改组成与过去的陈旧结构不同的新机构?在军方接受这个观念而认为这是真正的决策之前,只要有可能,年轻有为的医生将会继续希望离去。或者,是只看到了问题的部分,而没有看清全貌。
这就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汽车工业突然遭到尖锐的攻击,认为美国的汽车不安全,为什么美国的汽车业界在遭到攻击时那样惊惶失措。事实上,美国的汽车业界不仅重视车辆本身的安全,而且还曾经努力使公路更安全和致力于训练驾驶员。社会上说车祸的原因,一在于道路不良,二在于驾驶不慎,这种说法仍然是似是而非的。确实,所有与汽车安全有关的机构,从公路警察到训练学校,都以安全作为他们活动的目标。而这些活动也收到了效果。重视行车安全的公路减少了许多事故,而经过安全训练的驾驶员也比较重视安全。虽然按每千公里每千辆汽车计算的事故比率在下降,但事故的总次数及事故的严重程度却在继续上升。
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清楚,由于少数驾驶员酒醉驾驶和有“肇事倾向”的驾驶者发生的车祸,往往占了车祸次数的四分之三。这些人远非训练所能奏效,即使是在最安全的公路上,他们也会发生事故。很久以前人们也已经清楚,我们必须针对比例虽小但却显著的事故做一些事情,即使已经有了安全法和安全训练,这些事故照样发生。这就是说,我们除了必须对安全公路和安全训练作一些补充,以便在正确驾驶时保证行车安全外,我们还要在工程方面想办法,做到即使在驾驶错误时也能保证行车安全。但是美国汽车业界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上述例子显示,为什么“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更危险。与交通安全有关的每一个单位,包括汽车业界、公路委员会、驾驶员协会以及保险公司等,都不敢承认车祸发生的不可避免,认为凡有车祸即是忽略了安全,就像老祖母一看见专治性病的医生就认为是鼓励不道德的性行为一样。正是人类的这种将“道德”和“是非”混淆在一起的倾向,使不周全的假定变得很危险,而且很难改正。
所以,有成效的决策人总是在一开始时,先把问题假定为普通性质的。他总是将那些复杂而令人注目的问题,先假设为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症状,然后努力寻找问题的真正本质。
如果这是真正的特殊事件,有经验的决策人仍然会先怀疑这是不是一宗第一次出现的新的普通情况。他会用发行债券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财政问题,即使这些债券在最近几年能以最好的价钱卖出也罢。如果他期望在最近的将来得到资金市场的帮助,他就会创造出新类型的投资人和为现在尚未存在的公众资金市场设计一种适当的证券。如果他必须要和一批能干但缺乏纪律的部门主管合作,他不会马上想到杀鸡儆猴,而会从根本的立场上去促进一种大规模机构的观念。如果他认为他的公司需要成为独占性企业,他就不会以猛烈抨击社会主义来使自己满足。他会谋求在不负责任的、竞争而且不受检查的私人企业和同样不负责任、基本仍然不受控制的政府垄断这两者之间,就如同在腹背受敌之际创出一条公共管制的第三道路。
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最明显的事实之一,是暂时性事物所具有的耐久性。举例来说,英国旅馆的特许卖酒处,法国的房租管制,华盛顿的“临时”政府建筑物,这些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仓促决定的,当时是准备应付几个月之后便取消的临时措施,但是过了五十年,这些临时措施还是屹然未动。有成效的管理者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当然,有成效的管理者也会采取临时措施。但是每次采取临时措施时,他都会问自己:“如果我必须长期执行这种临时措施,我会愿意吗?”如果他不愿意,他就会继续寻找更通用、更高水平,也更全面的解决办法。这也就是一种正确的原则结果,有成效的管理者不用作很多的决策。但这并不是由于管理者在作一项原则性决策时要花很长的时间,实际上作一项原则性的决策,不会比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决策所需的时间长。有成效的管理者不需要作太多的决策。既然他已制定了一套规则和政策来解决普通的问题,那么,种种问题都可以在这些规则和政策的指导下加以处理了。西方有一句格言说:“法律愈多的国家,就是愈没有好律师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个案件都是独特的案件,而不是在通用法律下能够解决的案件。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管理者要天天做决策,这只不过是懒惰和无效的表现。
决策人还常常要留意是否有出现非常事件的信号;他要经常问自己:“这一解释能说明某些事件吗?能说明所有同类的事件吗?”他要将这一解决方法所预期的结果记下来,然后进行检查,看看是否与预期的结果相符合,比如看看是否能够消灭车祸。最后,如果出现了别的非常事件,如果出现了他的解释所不能说明的事件时,如果结果与他预期的情况有出入时,他就要回过头来,重新考虑问题。
事实上,这些规则是希腊医学家在两千多年前提出来的。也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科学方法,还是三百多年前的科学家伽利略所应用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规则是古老、著名而又经过时间考验的,是人人都能学会、人人都能应用的规则。
非黑未必即白
“两全其美”看起来很好,因为一把手抓住了两个想要的东西。可是,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容易形成欲望的陷阱,结果两手空空。企业能不能在有两个决策方案的情况下都试一把呢?事实证明,惟有“非此即彼”才是理想选择。
所谓非此即彼的陷阱,形象地说就是“两者择其一”。为每个问题多考虑几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这应该是一条不变的规则。否则,我们就会陷入“两者择其一”非此即彼的错误陷阱之中。假如有人说“世界上的事物非红即绿”,那么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反对。然而,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每天都在接受并按此而行的一些说法往往就是这么荒谬。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涉及一对真实的矛盾,比如说绿色与非绿色,它包含了各种可能性;另一个只是一种对照,比如说绿色与红色,那只是在许多种可能性中举出了两种。然而,没有再比把这两种概念混为一谈更常见的了。由于人们常常喜欢走极端,这就更增加了危险程度。在“黑与白”之间的确存在着各种可能的颜色,但这些颜色并不包含在黑白两种颜色之内。然而,当我们说“非黑即白”时,我们往往会认为我们已提到了黑白之间的各种颜色,因为我们提到的是颜色的两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