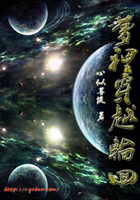彭府大门被拍得山响时,已是十日之后。这时,方晗刚从午间小憩中醒来,躺成“大”字型,揉着惺忪睡眼望外面明晃晃的日头。回忆这十日,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作死”。
她途遇同门师妹,牟足一腔热血替她出头,不料打错了人,更不料的是凌沫雪这个小贱人一见势头不对,马上逃之夭夭,再不提半句同门情谊。
错手伤人,不得不赔。她好容易唬住彭古意,入彭府做婢女打短工来还债,原以为一月就能还清,谁知十天药浴伺候下来,她的赔偿单已经埋到膝盖。
曾以为她五年未回家,家里的老爷子会念及父女之情前来赎她,孰知十天过去,老爷子连个影儿都没有。亲爹,这真是亲爹啊。
想她从小兵蛋子做起,出生入死,几番起伏,终于升到一品大员,统领千军万马,原以为走上了人生巅峰,可以傲视新旧玩伴,孰知现实如此残酷,她竟因为赔不起银钱而沦落到给人当婢女,还要被各种嫌弃。
心好累,感觉不能再爱了。
“砰砰砰”,拍门声猛地响起,一声急过一声,半点空隙不留,惊得院中鸟笼中的雀儿直扑棱翅膀,镀金的笼子当当作响。
方晗亦被惊到,翻身下床,蹬上靴子出去开门。她心情不爽,语气中多了三分不耐:“人来了,别拍啦。病再急也要让大夫喘口气。”
她想着,恐怕是有人来求医。
“砰砰砰”,又是三声山响。
方晗“哗”地打开门,没好声气道:“急什么急,急着去投……”“胎”字哽在喉中,滚了几滚,又重重地落回肚中。
面前是一位年逾半百的老人,身着锦缎华服,眉目严肃。他似乎跛了左脚,双手拄着一根碧绿的镶珠手杖,此刻正怒气冲冲地立在彭府门外,目光几乎能吃人。
方晗见此人,大喜过望,欢呼着迎了出去:“你终于来了。”
老人怒气不减,提起手杖点在她额头,格住她扑来的动作。接着,杖头一转敲在了她脑门上:“翅膀硬了啊,见面连声‘爹’都不叫,你你你,你你娘的腿。”
方晗忙不迭往旁边跳开,摸着被敲疼的脑门,辩道:“爹,我娘不正是你媳妇吗?”
老人跛着脚,气得吹胡子瞪眼,手中拐杖如雨点般落下去:“还敢跟我顶嘴?真是气死我了。你这个不孝子,当年一声不吭跑去从军,五年了,在外整整五年。我求着皇上好容易允了你一月的假,谁知你不老实回家,在外面净惹是生非。还想让我拿出家底赎你?你想得美,你这个不孝子——”
方晗抱头逃窜,左躲右闪。老爷子腕力不错,真被敲中这么多下,那可有她受的。
老爷子满院子追打,却因跛着左脚行路不便,屡打不中。他追着追着,忽然“哎唷”一声,似脚下不稳要仰面跌倒。
方晗一下窜过去,忙将他接住:“爹,你悠着点。”
不料,老爷子蓦地反手扣住她的手腕,抬眼,阴森森一笑:“上当了吧,看你还往哪里跑。”说着,举起拐杖“噼里啪啦”一统狠揍。
她几乎吐血:“……这么好的演技,你怎么不去碰瓷?”
老爷子揍完自家闺女,顺了气,心满意足地放下拐杖,伸出一只手:“一拐一两,共二十两。挨打给钱,不许赖账。”
她疼得呲牙咧嘴:“明明只打中十九拐,怎么算出的二十两?”
“啪”的一下,老爷子又给了一拐:“二十两了。”
她:“……”
这么一通闹腾,搅得院中尘烟四起,鸟飞狗跳。许多花花草草也跟着遭了殃。
彭古意听得外面喧哗,行出房门,却见到如此一幕,不觉握紧了手中的折扇。
那畔老爷子将拐点在地上,正愤然质问方晗:“为什么伤人?为什么要赔那么多钱?你是不是又手痒调戏人家姑娘了?今天不闹个说法出来,我就打断你狗腿。”
方晗被这一连串问题搞得头晕,正纠结着如何回答以及先回答哪一个,这时转眼看到彭古意出来,立刻伸了食指向他,将这些问题踢了过去。
老爷子这才注意到有外人出现,转身,沉目打量对方。
彭古意扫视一遍院子中缺枝少叶的花草树木,盘算定下一张赔偿清单,这才稳了稳心神向前行来。从吵嚷声中他已猜出十之八九,向老爷子拱拱手,道:“这位老丈,你女儿在我这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