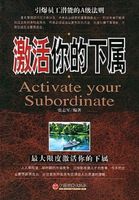忙碌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日子居然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叶远臻不再十分忙碌,他会时不时地约沈初见出去坐坐,或隔三四天,或是一两个星期,不多不少,不远,也不近,他会在车辆穿行的街道上让她走在靠里的一侧,会在天气变冷的时候准备一双精致的羊毛手套。她在他吸烟的时候皱过一次眉头,他就再也没有在她面前抽过第二次烟,他家里总是备着上好的碧螺春,哪怕她只去过寥寥几次,他会带她去徐徐那里吃饭,每次都点她最爱吃的菜肴,却再也没有像临江楼那里的温柔相拥。他们像是突然打开了经脉,总是有许多话题可以聊,不再相顾尴尬,她却觉得,没有了最初那种相互不敢触碰,却无比朦胧的奇妙感觉。
他们像是极其矛盾的双面体,一面亲近无二,一面客气有加,叶远臻不说,沈初见心里像是揣了一只红眼睛的小兔子,七上八下的蹦跳,忐忑而难安。
她想不顾一切地去找他说个清楚,划分清楚界限,好过这般受烦扰,却又始终无法张开口,生怕这一开口,就会毁掉了所有。
沈初见觉得,自己长到十八岁,人生的前十八年都没有现在的疯狂,叶远臻的出现在她平静的心里投下了一颗石子,却激起了万丈波澜。他不是易阳,他从不温柔体贴,他表面是是一个翩翩公子、谦谦绅士,背地里又阴暗腹黑、手段多端,他和她认识不过一年,易阳和她却早已相识数年,可是他却能轻而易举地把易阳的影响淡化减弱,他强势、他独断、他心里藏着无数秘密,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未知体,易阳是她心里的白月光,叶远臻却是霸道独具的罂粟花。
她不敢扪心自问,她怕心底里的答案会让她心惊肉跳,可是她却无法忽视那种感觉,从未有过的感觉,新鲜、冒险、悸动,宛如金戈铁马,在她心上纷沓而至。
过了十一月份,马上就临近沈初韶和易阳的婚礼了,易阳越发少的露面,沈初韶也安安分分地不再惹事,倒是易笛,来的只勤不少,他总是能收集到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然后送来给她,沈初韶也没了劲头和他吵嘴,她正在忙着置办自己的新装。
沈初韶和易阳的婚礼定在腊月十六,最后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沈柏雄的病反反复复,大半时间都在静养,沈初见打理着生意,也逐渐上手,她理事有条、赏罚严明,借着陈立周的事彻底整顿了一遍上下,简化了繁琐无用的手续,处理了一批走人情关系占着位子不干实事的一干人等,明确强化工厂的生产质量,强调着重务实,手段干脆利落,竖起了很好的威信,颇有一些叶远臻的风范,李掌柜对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开始真心实意地服她了,秦常誉还是老样子,持中而立,态度永远不温不火、不紧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