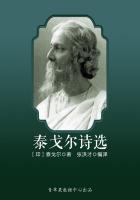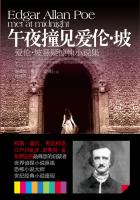就在永井清雄和他的官佐们进入松山本道阵地的地堡中时,中国滇西远征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率领他的师以上指挥官出现在怒山的老鲁田山峰之上。在美国强大机群的掩护下,将领们沿山峰一字儿排开。他们神情严肃而又心潮澎湃地欣赏着松山上的浓烟烈火,同时,为怒江西岸直插霄汉的巍峨雄峰面暗暗纳罕。
两年来,据守怒山的十一集团军与侵占我高黎贡山的日寇隔江对垒,势均力敌而又势不两立,都在积蓄力量意欲吞掉对方。日寇妄图扫平滇西远征军,直下昆明重庆,一举结束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圣战,以达到使中华亡国灭种的目的;远征军则在积蓄力量和仇恨,等待时机,歼灭入境之敌,光复河山,一洗国耻。现在,时机到了,愤怒的中国兵将要怒吼着,越过怒山山脉,跨过怒江,怒不可遏地杀向万恶的日寇了。
汹涌澎湃的怒江,气势磅礴的怒山,乃是中国人民的怒气凝成,今天要怒吼了。
站在怒山老鲁田山峰上的宋希濂右边的是美军顾问窦尔恩,集团军参谋长车藩如、副参谋长陶晋初,七十一军军长钟彬、副军长陈明仁,接替成岗新上任的“中国战神”——新编三十九师师长洪行,八十七师师长张绍勋,八十八师师长胡家骥,二十八师师长刘又军;站在宋希濂左边的是: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黄杰,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第二军军长王凌云,荣誉第一师师长汪波,七十六师师长夏德贵;紧挨着宋希濂身后站着的是集团军参谋处长欧阳春圃、作战科长蒋国忠、兵站分监李国源、炮兵司令邵伯昌以及二十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刘建忠(他是来十一集团军组织协同的)。
宋希濂环视四周,老鲁田群峰上哨兵林立,数十门榴弹炮、野炮、山炮组成的炮群,分布在各山头的东坡,都昂起漆黑的炮口,炮筒在烈日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炮手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只待一声令下,我们的炮弹就会在电闪雷鸣中飞过怒江大峡谷,倾泻在松山之上。
宋希濂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抗日将领,对炮兵有一种热烈的追求和渴望。“自一八四〇年以来,受尽世界列强欺凌和屠杀的中国人,还没有用这样强大的炮群满腔愤怒、痛快淋漓地轰击过万恶的侵略者!”他想。同时,在抗日战场上,有不少场合,宋希濂因手头没有炮兵而留下终生遗恨。如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宋希濂率领他的三十六师(当时宋为七十一军军长)在河南富金山与日寇十三师团激战,虽打得连日寇报纸都不得不承认:“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但宋希濂还是十分惋惜地说:“我们站在山头上,对敌军的活动,他们的炮兵阵地、运输车队,以及一些搭有帐篷的伤兵救护所等,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惜我们没有炮兵,如果我们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有一个炮兵营,就可以给它以毁灭性的打击。”(宋希濂《鹰犬将军》)
且说宋希濂对他的集团军的各种炮群深情而自豪地注视良久,再转过身来举起望远镜,认真察看这座被日寇自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东方的马其诺防线”、“支那第一要塞”的阵地——松山。奔腾激荡的怒江穿山破峡由北向南蜿蜒而来,在大坪子和惠通崖之间闪动着黄绿色的水光。惠通崖旁,滇缅公路向西、向松山盘旋而上,隐人松林和硝烟烈火笼罩的大垭口。天上,无数的飞机在盘旋、俯冲、轰炸,一阵阵灰黑的硝烟越过怒江峡谷,飞到老鲁田山峰上来。此时,闻惯了硝烟味的将领们顿时精神大振,不禁指手画脚,为美国盟邦的飞机叫起好来。
“邵司令,向松山打一个基数,严惩日寇,壮我军威!”宋希濂突然下令。
邵伯昌受令后,立即转身对待命的陈镜清、王恩培等几位炮团团长下令:“猛、准、狠地向松山打一个基数,看我的信号,齐射!”
一分钟后,一颗红色信号弹从邵伯昌手中升起,顿时,天地震动,日色无光。
此时,中国将领们群情激愤,那报仇雪恨的狂奋心情随着炮筒的伸缩而振奋,随着怒火的喷射而激荡,随着炮弹的轰鸣而爆发!一百年来,中国人被外国的洋枪洋炮打死了数千万人,如今半壁大好河山又被日寇踩在铁蹄之下,亿万炎黄子孙正在枪刀和皮鞭之下当牛做马,沦为奴隶。站在怒山老鲁田山峰上的将领们都是从上海,从黄河,从长江和衡阳、汉口败退下来的指挥官,败军之耻,失城失地之痛,长期以来使他们咬牙切齿,誓报与日寇不共戴天的国家仇、民族恨。如今,经过两年的艰苦经营,在美国盟邦的装备训练下,在大西南人民,尤其是云南人民的养育下,遍体鳞伤的滇西远征军终于。恢复元气,拉开了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序幕。“我中华民族也有扬眉吐气的这一天!”新编三十九师少将师长洪行脚一跺,激动地吼出声来。
宋希濂则板着冷峻肃然的面孔,但他的双眼仍闪射出异样的光芒,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永远不会忘记七年前的奇耻大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旬,南京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曾对日本天皇裕仁夸下海口“一个月之内打垮中国”的日寇陆军上将杉山元飞到上海亲自督战;南京战地指挥官朝香官(天皇的叔辈皇族)带着十二万日寇决心以最残忍、最野蛮、最凶恶的方式夺取南京。十二月十二日,当时身任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经过浴血拼搏,一兵不带地逃离南京,在一艘机帆船上几乎坠入长江。要不是中央宪兵团的张国维救了他,哪还会导演出今天这种气壮山河、扬我国威军威的场面!
宋希濂永远不会忘记两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的坦克撞开国门畹町,碾着滇西大地柔嫩的芳草,轧着满地缤纷的残花,在短短一个星期内,闪电般地直下芒市、陷龙陵、取腾冲,其先头部队一举突破怒江天险。于是便出现了一场千钧一发、力挽危局的血战。这是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成败的历史性的一战。不管政治家们为了政治目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出于偏见不顾事实,很少披露这一真相,当时的当事人宋希濂、李志鹏和日寇十五军团长饭田祥二郎中将以及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都是见证人。陈纳德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就说,日军“照此速度前进,十天内可以到达昆明,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重庆抗战局面就不能维持’美国反攻日本的战略设想就将成为泡影。滇西、缅甸一失‘印度不保。连丘吉尔都惊呼:“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饭田祥二郎中将在从龙陵赶往惠通桥的路上说:“照此速度前进,至迟五月十日可占领下关,中旬可拿下昆明,月底可直逼重庆。六月初,天皇陛下就可向全世界宣布:大东亚圣战已胜利结束。与德国元首希特勒会师中东的伟大时刻就指日可待。到那时,即使蒋介石迁都新德里,也只是一个成不了多大气候的流亡政府,不足挂齿了。”
真是十万火急,一发千钧。这么关键的一仗,不能不归功于宋希濂的决断和李志鹏的神速与果敢。
这是一场恶战。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下晚,李志鹏奉宋希濂之命率三十六师先遣团一〇六团乘车赶到保山时,保山城正乱成一锅粥,城里大火熊熊,浓烟冲天,这是白天日寇狂轰滥炸的罪恶现场。万千难民在城郊公路两边用手从炸弹坑边扒土寻找亲人的尸体,呼儿唤女,寻爹觅娘,那号啕之声连绵几里,哭声震野。顿足捶胸、呼天抢地之状,惨不忍睹。李志鹏不敢停留,催动一〇六团直向西扑去。由于公路上尽是横七竖八的车辆,他们走走停停,心急如火,但又不得不排除一路车辆组成的路障。到夜里十二点,才到达七〇七公里处。在这里,李志鹏询问几个仓皇逃来的难民,知道惠通桥正在激战,而且一部分日军已爬上怒江东岸。十万火急,刻不容缓!他命令部队枪上膛,刀出鞘,随时准备和迎面撞来的日寇决一死战。
但迎面开来的还是商车、难民车和运送物资的军车以及蜂拥而来的难民。他们堵塞于途,使前往迎战的一〇六团寸步难行。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李志鹏只好下令:先头车将机枪架在驾驶篷顶上,开亮车灯,有不让路的,对空开枪警吓。这样,前进的速度才快了一点。
对付这种混乱,三十六师是有经验的。在南京大撤退中,他们奉命掩护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渡江逃命时,就很叫争相狂逃的俞齐时的七十四军和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在挹江门吃了不少苦头。
如果说当年奉唐生智的命令,掩护他的卫戍司令部逃跑是天大的耻辱,那么,现在是奉了蒋委员长和宋总司令的命令,扫开一切路障去迎敌则是无上的光荣。所以,李志鹏的车队过了七〇七后,在混乱、拥挤的公路上就机枪与喇叭齐鸣。民族危亡在此一举,一切都顾不得了!
尽管如此,一〇六团先头部队乘车来到老鲁田顶峰时,已是五日早上了。此时怒江东岸,惠通桥头的宪兵、工兵还有化学兵、息烽部队的各一排已打得所剩无几,三百多日军正越过中国兵的尸体,从笔直的小道直破弯弯拐拐的盘山公路向老鲁田峰顶冲来。一〇六团团长熊正诗眼尖,见一个负了伤的中国兵正抱住一个日寇的脚,不让他前进,日本兵调转刺刀从伤兵的胸口直扎进去。
日军先头部队距山顶只有三十米了。如果他们冲上山头,滇西路上再无险可守,日军就能长驱直入!到那时,人类历史就要按日本人的意志来写。
“打!”熊正诗对从车上飞身而下,迅即散开成冲锋队形的战士一声怒吼。
轰轰轰,随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一〇六团一营的四百多名官兵冲入敌群,一时间刀枪飞舞,杀声震天。
此时,躲藏在盘山公路九弯十八拐的草丛、荆棘中的华侨和难民一见中国的救兵来到,都手拿石块或扁担、拄棍跳出来齐声呐喊助威。不少难民就地取材,翻起满山坡的三尖石、囫囵石就往山下滚。一石滚动,沿路上又撞起不少石头,都翻滚着、蹦跳着、呼啸着,从半空向爬上山来的日寇劈头盖脸地砸下去。江边,过了江的日寇正往上爬,不过江的日寇正跳上橡皮舟。松山上公路拐弯处,日军正架设山炮,惠通岩下日寇正在集结,后续部队滚滚而来。在龙陵镇安所东进的路上’饭田祥二郎中将正挥动指挥刀,命他的机械化部队全速开进,今日势必东渡怒江,拿下保山。怒江西岸,一〇七、一〇八团飞驰而来;已逃到戥子铺、七〇七、莽林寨、太平村等地的几千难民和华侨,丢下自己的贵重包袱,回转身来,奔至老鲁田和中国兵一齐投入战斗。永平路上,总司令宋希濂、七十一军副军长陈明仁,驱动他们的滚滚铁流,掀掉在滇西路上一切要钱不要国的发国难财的车辆,风驰电掣般地向怒江扑来。窄路相逢勇者胜,敌我双方都在拼命争夺怒江这一线天堑,争夺滇缅路这一丝命脉,争夺惠通桥这一生死存亡的咽喉!
只剩两条铁索的惠通桥两岸,雄伟险峻的怒山和高黎贡山之间,弹雨在横飞,空气在燃烧,吼杀声盖过怒江咆哮的狂涛声。怒水为之变色,滚滚翻动的已不是蓝色的漩涡,而是血水红波。在这血水红波中,扭打着的是双方伤员,漂流着的是死尸,它们被红色的漩涡卷进江底,又从深邃的江底皮开肉烂、面目全非地浮出江面,滚动着、沉浮着三三五五地漂向下游,漂向大海。
战斗在惨烈地进行。
所幸的是,团长熊正诗率着十几个弟兄杀到江边,占领了由宪兵、工兵们挖掘的一段战壕,并借此向正在抢渡怒江的日寇狠狠射击。同时,在半坡上负伤的中国兵也不断连滚带爬地下到大坪子,用绑腿布草草包扎一下伤口就立即投入战斗。
正在渡江的日寇的不少橡皮舟被子弹打通,顿时泄气,连同日军一起葬身江底。只有少数爬到江边的日寇,下半身泡在水里,倚着光溜溜的岸石向岸上射击。
老鲁田山头上,李志鹏见打退了敌人,就给部队下令构筑工事。由于与后方联络的电话线尚未架通,李志鹏已派出第三批骑兵通讯员去催赶后续部队。并派出两名中校副官去沿途传令:不论什么车,车上乘坐什么人,见了三十六师部队而不靠边停下,部队有权射击!不如此,就不能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
李志鹏的师指挥所设在老鲁田山峰上的一条坎儿下,连个坑都没有,更莫说掩蔽部了。恰巧一颗日寇山炮弹打过来,落在他左前方十几米处,轰然一声,掀起漫天土石块和灰尘,将他扣得严严实实,他从灰堆里滚出来,抖抖身子,眨了眨眼,风趣地说:“也好,省得老子伪装!”
天慢慢黑下来。
李志鹏严令:除江边前哨阵地严密监视敌人行动外,怒江西岸半坡和老鲁田主峰上所有部队必须彻夜构筑工事,迟缓怠工者就地正法。
天黑定后,戥子铺、莽林寨、太平村、由旺乡几千民众抬着担架,挑着饭菜,扛着木板、楼楞和锄头赶到老鲁田来和部队一齐抢修工事。妇女们替伤员包扎伤口,重伤员很快被抬走,轻伤员仍坚守阵地。
一夜之间,老鲁田山上战壕交通壕密如蛛网。
天亮前,李志鹏命民众全部后撤。
拂晓,日寇在松山上的山炮、钢炮一齐向惠通桥东岸打过来,硝烟和浓雾搅在一起,暗无天日,只有炮弹爆炸的火光一闪一闪地似乎要把江雾烧红。
惠通崖下,日寇在十几挺机枪掩护下在江面上架设浮桥。
太阳冒山时,渡过江的日军展开冲击。
到中午,一〇六团虽打退了日军十几次冲锋,但江边阵地已全部丢失。
日军已冲到半山腰的战壕里。
三营七、八、九连的勤务兵、司号员、伙夫都全部投入战斗,和日本鬼子厮打在一块。
半坡上的阵地也丢失了。
松山上隔江相望的日军狂呼乱叫,在为快冲上老鲁田的日寇呐喊助威。
日寇正向山头冲来。
李志鹏提起一挺机枪,眼中喷火,口中狂呼:“弟兄们杀出战壕!一〇六团不准有一个活人离开阵地,杀!”
战士们跳出战壕,挺起刺刀,居高临下向敌扑去。
敌我杀得难解难分。
杀——!一〇七团卷地而来。
冲——!一〇八团直向江边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