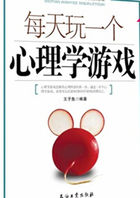他不说,我不说,一切都变得好安静。
耳边响起的唯有从窗外飘进的虫鸣!
不管多晚,他都不会留宿,倒是一夜深,就命春秀伺候我上床就寝,他即使不离去,也不会让我继续陪坐着。
乾陵和硕并为变,他仍是我所认识的乾陵和硕,只是收敛了他的暴戾。
这份变数,谁说得清楚,兴许是暴风雨来前的片刻宁静。
今夜,他一如往常,一夜深,就命春秀伺候我上床,而他只是端坐在椅子上,安静不发一语。
我则轻合上双眼,神经敏感,可疲乏的身子,没一会就进入了浅眠。
他坐了一会,便静静地离去,换做是以前我定然不会转醒,可现在......小小的动静我便转醒。
我知,他走了。
侧转脸,我凝望着从窗口投射进入的微弱月光,心里久久无法平静,一份纠结,泪珠儿又止不住的落下。
无法入睡,我缓缓地起身,右手习惯性的抚摸上已除去绑带的左手腕。
福俞宁说是腕骨已经愈合,可挫骨伤筋至深,这左手废了也不无可能,当然现在话不能说绝,这左手日后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每每右手触摸上左手腕时,我的心自能平定,它宛如成了一剂镇定我心魂的良药。
我抚摸着左手腕,怔怔出神,陪伴我的还是那阵阵虫鸣。
猛然......我眼底像是有什么一闪而过,敏感的神经使我瑟瑟发抖,眼泪又开始往下落。
我不及擦拭去眼泪,匆忙下床,赤脚走到窗口,推开了窗,探头出去。
没有任何动静,我缩回身子,转身,难道是我的错觉?
思忖了一番,我便关上了窗,踱步走回到床前,坐下,摇了摇头,不想再做无谓的思索,缓缓地躺下了身,我虽易醒,可也易睡。
疲倦一上,合上眼,就进入了梦乡......
清早,春秀推门声将我惊醒,惺忪的眸子中视线仍有许模糊。
春秀走入内房,来到我的床前,见我醒着,问:“婕妤您怎的没睡好?”
我摇头,说:“没,听你推门,才醒。”
春秀心疼,问:“您今个觉得身子可有好些?这手腕可是有知觉?”
我莞尔一笑,说:“没差没好,就那样。”
春秀叹气,迈步上前,蹲下身子,握住我放在薄被外的手腕,细细地揉着腕骨处,说:“婕妤这左手一定能好。”
“是!会好。”好与不好,我不在意,只是为了安抚春秀,我只道会好。
“婕妤,早上您可有什么想吃?”
“不了,一会就喝药,吃不了。”想起一早就要喝下一碗苦药,我这胃就已抽紧。
“奴婢给您熬点粥,您总是为了喝药不吃,这身子能好?”
“春秀,吃了,喝不下,这取舍......”我将选择的权利交给春秀。
“这药要喝,这粥也要喝,婕妤,一半一半可好?”春秀思了半天,给出了选择。
“好。”我点头应允,换我选,我会选粥,这样或许是最好的,只是福俞宁......
他,我想到的就是药,就是诊断,每每喝药都是由他看着,说是陛下旨意,药要喝去三分之二,我忍着,憋着,将药喝去,可为了那三分之二的药,我也只能不做任何进食,几天下来,胃自然有了反抗。
......T^T............T^T............T^T............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