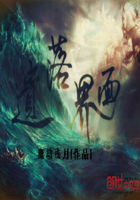第十章
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他们告诉我说:有人下午要来看我。那天天热,房间里有好多苍蝇。我的护理员把纸裁成纸条,绑在棍子上做成掸子,来驱赶苍蝇。我看着那些苍蝇叮在天花板上。护理员一停止挥赶,再一打瞌睡,苍蝇便飞下来,我就吹着气把它们赶走,最后用双手捂住脸,也睡着了。天太热了,我一觉醒来,腿上发痒。我叫醒护理员,他往绷带上倒了些矿泉水。这样一来,床给弄得又湿又凉。睡醒的人就在病房里聊天。医院的下午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每天早晨,三名男护士和一名医生,挨个巡视病床,把病人一个个抬下床,送到包扎室去换药,趁换药的机会,给病人整理床铺。去包扎室换药可不是好玩的,我后来才知道,床上有病人,也照样可以铺床。护理员泼完了水,床上又凉快又舒服,我正吩咐他给我脚底什么地方挠痒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带来了里纳尔迪。他脚步匆匆地来到床前,弯下腰来亲了亲我。我见他戴着手套。
“你好吗,宝贝?感觉如何?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是一瓶科涅克白兰地。护理员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了。“还有个好消息。要给你授勋。他们想给你弄块银质奖章,但是也许只能搞到铜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受了重伤。他们说,只要你能证明你有什么英雄事迹,你就能得到银质奖章。否则就只能是铜的了。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什么英雄事迹吗?”
“没有,”我说。“大家在吃干酪的时候,我被炸了。”
“别开玩笑。受伤前后,你肯定有过什么英雄事迹。仔细想想看。”
“我真没有。”
“你没背过什么人吗?戈尔迪尼说你背过好几个人,但急救站的少校军医说,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得到奖励,得让他在提议书上签字。”
“我没背过什么人。我动都动不了。”
“那没关系,”里纳尔迪说。
他摘下手套。
“我想我们能替你弄到银质奖章。你不是拒绝比别人先接受治疗吗?”
“也不是很坚决。”
“那没关系。看看你伤得多么严重。看看你的勇敢行为,总是要求上一线。再说,这次行动又很成功。”
“他们顺利过河了吗?”
“顺利极啦。俘获了近千名俘虏。公报上写着呢。你没看公报吗?”
“没有。”
“等我带一份给你看看。这次奇袭非常成功。”
“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棒极了。大家都棒极了。人人都替你感到骄傲。跟我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吧,我敢肯定你能拿到银质奖章。跟我说说吧。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停了停,想了想。“说不定你还能弄枚英国勋章呢。那儿有个英国人。我去找找他,看他愿不愿意推荐你。他总会有点办法的。你遭了很多罪吧?喝一杯吧。护理员,去拿个瓶塞起子来。噢,你真该看看我是怎样给人切除三米小肠的,我的医术现在是今非昔比了。这可是给《柳叶刀》杂志投稿的好素材。你替我翻译出来,我把它投到《柳叶刀》。我的医术日益精湛。可怜的好宝贝,你感觉怎么样啦?怎么还不见那个该死的瓶塞起子?你这么勇敢沉着,我都忘了你在受罪。”他拿手套拍拍床沿。
“瓶塞起子拿来了,中尉长官,”护理员说。
“打开酒瓶。拿个杯子来。喝了这个,宝贝。你那可怜的脑袋怎么样了?我看过你的病历。压根儿没有骨折。急救站的少校是个杀猪的。我要是给你动手术,决不会让你吃苦。我从不让任何人吃苦。我掌握了这里面的诀窍。我天天学习,手术越做越顺当,技术越来越精湛。原谅我话这么多,宝贝。看到你受这么重的伤,我真心痛。好了,喝了这个。不错的。花了十五里拉呢。一定不错。五星的。我一离开这儿,就去找那个英国人,让他给你弄一枚英国勋章。”
“他们的勋章可不是随便给的。”
“你太谦虚了。我打发联络官去,他能对付那个英国人。”
“你见过巴克利小姐没有?”
“我把她带来。我现在就去把她带来。”
“别去,”我说。“给我讲讲戈里察的情况。姑娘们怎么样啦?”
“还有什么姑娘们。两个星期以来就没有调换过。我再也不去那儿了。太丢人了。她们哪儿是姑娘,简直就是老战友了。”
“你压根儿不去啦?”
“就是去,也只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来的。顺路去看看。大家都问起你。她们居然会待这么久,彼此都成朋友了,真是太丢人啦。”
“也许姑娘们不愿意再上前线来了。”
“她们当然愿意来。他们有的是姑娘。只是管理不善。他们把姑娘们都留在后方,供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尽情享乐。”
“可怜的里纳尔迪,”我说。“一个人孤零零地作战,没有新来的姑娘。”
里纳尔迪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我想你喝点酒没害处,宝贝。你喝吧。”
我喝了那杯科涅克白兰地,觉得浑身热乎乎的。里纳尔迪又倒了一杯。他现在安静了。他端起酒杯:“为你英勇的伤口。为了银质奖章。告诉我,宝贝,这大热天里,你总是躺在这儿,不感到冲动吗?”
“有时会的。”
“我无法想象怎么能这样躺着。我会发疯的。”
“你是发疯了。”
“我希望你回来。现在没人半夜三更带着浪漫故事回来了。没人可以开玩笑。没人可以借钞票。没有把兄弟和室友。你为什么要受伤呢?”
“你可以拿牧师开玩笑啊。”
“那个牧师。开他玩笑的不是我,而是上尉。我是喜欢他的。要是非得有个牧师,就用这个牧师也就行了。他要来看你,正大做准备呢。”
“我喜欢他。”
“噢,我早就知道啦。有时我觉得你和他有点那个劲儿。你知道的。”
“不,你不会吧。”
“是的。我有时是那样想的。你们就像安科纳旅第一团的番号,有点那个劲儿。”
“嗐,见鬼去吧。”
他站起身,戴上手套。
“哈,我喜欢逗你玩,宝贝。尽管你有牧师,有英国姑娘,你骨子里还真跟我一模一样。”
“不,我跟你不一样。”
“是的,我们是一样的。你其实是个意大利人。肚子里除了火和烟以外,什么也没有。你只是假装是个美国人。我们是兄弟,彼此相爱。”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要规矩点,”我说。
“我会叫巴克利小姐来的。没有我,你跟她在一起会更好。你会纯洁一点,甜蜜一点。”
“嗐,见鬼去吧。”
“我会找她来的。你那冷冰冰的美丽女神,英国女神。我的天哪,碰上这样的女人,男人除了崇拜还能做什么呢?英国女人还能有别的用处吗?”
“你这愚昧无知、嘴巴龌龊的意大利佬。”
“一个什么?”
“一个愚昧无知的意大利佬。”
“意大利佬。你才是个冷面的……意大利佬呢。”
“你愚昧无知。笨头笨脑。”我知道那个字眼刺伤了他,便乘胜追击。“没见识,没经验,因为没经验而变得笨头笨脑。”
“真的吗?让我跟你说说你们那些好女人的事吧。你们的女神。找个一向清白的姑娘和找个女人,只有一点不同。姑娘会痛。我只知道这一点。”他用手套拍打着床。“而你永远不知道姑娘是否真喜欢干那事。”
“别生气嘛。”
“我没有生气。我跟你讲这些话,宝贝,只是为你好。让你少些麻烦。”
“就这唯一的不同?”
“是的。但是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傻瓜却不明白。”
“谢谢你好心告诉我。”
“咱们别拌嘴啦,宝贝。我太爱你了。不过,可别当傻瓜。”
“不会。我要像你一样聪明。”
“别生气,宝贝。笑一笑。喝一杯。我真得走了。”
“你真是个贴心的哥儿们。”
“现在你看到了,我俩骨子里是一样的。我俩是战友。跟我吻别吧。”
“你还挺伤感的。”
“不。我只是比你感情更深一些。”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在向我逼近。“再见。我很快会再来看你的。”他的气息远去了。“你不乐意,我就不吻你啦。我会把你的英国姑娘送来的。再见,宝贝。科涅克白兰地就放在床底下。早点康复。”
他走了。
第十一章
牧师来的时候,已是傍晚。在这之前,他们给我送来了饭,后来又收走了碗盘,我便躺在那里望着一排排的病床,望着窗外在晚风中微微摇晃的树梢。微风从窗口吹进来,到了夜晚,天凉快了一点。这时,苍蝇落在天花板上,落在电线吊着的电灯泡上。电灯只是夜间有人给送进来,或者有什么事要做时才开。黄昏后病房里一片黑暗,而且要一直黑暗下去,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好像小时候早早吃了晚饭就给弄上床睡觉一样。护理员从病床间走来,到我跟前停住脚。有人跟着他来。原来是牧师。他站在那儿,小小的个子,棕色的脸,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你好吗?”他问。他把几包东西放在床旁边的地板上。
“挺好,神父。”
他在先前给里纳尔迪端来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局促不安地望着窗外。我注意到他的脸显得很疲惫。
“我只能待一会儿,”他说。“时候不早了。”
“还不晚。食堂怎么样?”
他微微一笑。“我还是人家的一大笑料,”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很疲惫。“感谢上帝,大家都平安无事。”
“看你挺好,我很高兴,”他说。“希望你不感到疼痛。”他好像很疲惫,我很少见他这样疲惫。
“已经不疼了。”
“食堂里缺了你,挺想念的。”
“我也盼望回去。一起谈谈总是很有意思。”
“我给你带了些小东西,”他说。他从地上捡起包裹。“这是蚊帐。这是一瓶味美思。你喜欢味美思吗?这是些英文报纸。”
“请把报纸打开给我看看。”
他一听很高兴,马上打开了报纸。我双手捧着蚊帐。他端起味美思给我看了看,然后放回床边地板上。我拿起那捆英文报纸中的一张。我把报纸转了转,正好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这样就可以看清标题了。原来是《世界新闻报》。
“其他的报纸是有插图的,”他说。
“看这些报纸一定很有趣。你从哪儿搞来的?”
“我是托人到梅斯特雷买来的。以后还会有的。”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神父。喝一杯味美思吧?”
“谢谢。你留着自己喝吧。是特地带给你的。”
“别这样,喝一杯吧。”
“好吧。以后再给你带点来。”
护理员拿来杯子,打开酒瓶。他把瓶塞搞折了,只好把剩下的那截戳进瓶里去。我看出牧师有些失望,但他还是说:“没关系。不要紧。”
“祝你健康,神父。”
“祝你早日康复。”
随后他还端着酒杯,我们彼此对望着。有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像好朋友一样,可是今晚却有些拘束。
“怎么啦,神父?你好像很疲倦。”
“我是疲倦,可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天气太热吧。”
“不是。还只是春天呢。我觉得打不起精神。”
“你有战争厌倦症吧。”
“倒不是。不过我是讨厌战争。”
“我也不喜欢战争,”我说。他摇摇头,望望窗外。
“你不在乎战争,你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你要原谅我。我知道你受了伤。”
“那不过是意外受的伤。”
“就算你受了伤,你还是不懂得什么是战争。我敢说。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点。”
“我受伤的时候,大伙正在谈论这个话题。帕西尼说得正起劲。”
牧师放下杯子。他在想别的事。
“我了解他们,因为我就像他们一样,”他说。
“不过,你和他们不一样。”
“可我确实跟他们是一样的。”
“军官们什么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