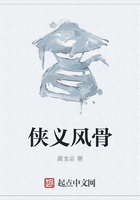侯爵老爷不屑再去搭理那帮人,往座位上一靠,准备继续上路,那神气就像是一个偶尔失手打破一件寻常物件的绅士,他已赔了钱,而且他是不在乎花钱的;车轮刚开始转动,一个金币突然飞进了他的马车,当啷一声滚落在车内的地板上,扰乱了他的安宁。
“停下!”侯爵老爷喝道,“勒住马!是谁扔的?”
他朝刚才卖酒的德发日站的地方望去,只见那个不幸的父亲脸朝下趴在石铺路面上,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黝黑粗壮的女人,正在编织。
“你们这帮狗东西!”侯爵语调平静地说,而且除了鼻子上那两个肉窝之外,脸色一点也没有变,“我真乐意把你们一个个都轧死,把你们从世界上消灭干净。要是我知道是哪个混蛋往我车里扔东西,要是离我的车子又不远,我一定要让他在我的车轮下碾得粉碎。”
这些平民百姓就是在这样的淫威下过日子的。多年来的惨苦经历告诉他们,这种人能够凭借法律手段,乃至超出法律的手段,对他们做出怎样的事来。因而,他们一言不发,手一动不动,连眼睛也没有抬起来。男人中,一个也没有。可是女人中,那个站着编织的女人,却坚定地抬起头,直盯着侯爵的脸。为这种事和她计较,有失他的尊严,侯爵只是用轻蔑的目光扫了她和所有那帮老鼠一眼,便又靠回他的座位,下令道:“走!”
他继续驱车走了,别的马车也一辆接一辆飞驰过去了。内阁大臣、国家谋士、税收承包人、医生、律师、教士、歌剧演员、喜剧演员,整个化装舞会五彩缤纷的行列,都接连不断地疾驰过去了。老鼠从它们的洞里爬出来看热闹,一连几小时站在那儿观望着。士兵和警察组成一道屏障,把他们和驰过的车队隔开,而他们则在这道屏障的后面钻动,伸头窥看。那位父亲早就抱起那捆东西,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曾在喷泉边照看过那捆东西的女人们,这时都坐在那儿呆呆望着淙淙的水流和化装舞会的滚滚车流——只有刚才站在那儿编织的那个女人,仍以命运女神坚持不懈的精神一直在编织着。泉水潺潺流动,河水湍急奔流,白天流入黄昏,城市里有这么许多生命按照规律进入死亡,时间不等人,那些老鼠又在他们那黑暗的洞穴里挤得紧紧地睡着了,化装舞会在晚餐时分欢天喜地地开场,一切事物都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着。
第八章 侯爵老爷在乡下
这儿有着一片怡人的景色,各种庄稼点缀其间,但并不茂盛。在本该播种小麦的地里,长着可怜巴巴的黑麦,还有几片疏疏落落的豌豆、大豆和几块长势不良的菜地。在这毫无生气的土地上,也像在它上面耕作的男男女女一样,全都有一种不愿生长繁茂的模样——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枯瘦干瘪。
侯爵老爷坐在他的旅行马车里(车子本该是比较轻快的),由两名车夫赶着驾车的四匹驿马,正艰难地走在一段陡峭的山道上。侯爵老爷的脸上一片红晕,这倒不是由于他体内的血色,不是他的高贵血统有什么问题,而是他无法控制的外因——那西沉的落日——所造成的。
旅行马车登上山岗,落日的余晖把马车里照得通亮,把车里的乘客染得满身猩红。“会褪掉的,”侯爵老爷看着自己的双手说,“很快就会褪掉的。”
实在,夕阳已经沉得很低,说话间就隐到山背后去了。待车轮上安上沉重的车闸,马车带着焦土味儿,在一溜烟尘中滑下山坡时,那鲜红的晚霞也在迅速地消退。夕阳和侯爵老爷一起下了山,待到卸去车闸时,天边已经不剩一丝霞光了。
不过,那一片山野的景象仍然依稀可辨。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后是一抹绵亘起伏的丘陵,一座钟楼高耸的教堂,一处风磨磨坊,一片狩猎的森林,还有一堵陡峭的崖壁,悬崖上屹立着一所用作监狱的城堡。在苍茫的暮色中,侯爵带着一种临近家门的神色,打量着四周这些逐渐模糊的景物。
小村子里有一条破败的街道,一间破败的酒坊,一个破败的硝皮作坊,一家破败的酒店,一处破败的驿站,一眼破败的水泉。一切的一切,全都那么破烂寒酸,这儿的人也一样,一个个都寒酸潦倒。不少人坐在家门口,正在剥着干瘪的洋葱之类,算是在准备晚饭,还有许多人在水泉边洗着树叶、野菜以及地上长的其他可以果腹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穷,原因并不难找。村里明文规定,这儿的人必须缴纳各种各样的税金:国家税、教会税、领主税、地主税、综合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哪个村子能够保住,不被吞掉呢?
村里看不见什么小孩,也没有狗。至于那些成年男女,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住在磨坊下这个小村子里,以最低的生活水平苟延残喘,要么就被关进悬崖上的那座监狱,在那儿了却残生。
暮色中,一个仆役飞奔在前开道,车夫的鞭声噼啪作响,鞭梢儿像蛇似的在暮色中扭动,那架势仿佛复仇女神也随之驾到,旅行马车来到了驿站的门前,侯爵大人坐直了身子。驿站大门紧挨着水泉,农民们都停下手头的活儿朝他望着,他也把目光投向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他们那日益憔悴的脸色和瘦弱的身体,这使得英国人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误以为法国人都是瘦弱的。
侯爵老爷朝村民们扫了一眼,见他们一个个都恭顺地低着脑袋,就像他自己在宫廷大臣面前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低头只是逆来顺受,并不是为了讨好逢迎。正在这时,一个满头尘土的修路工走进了人群。
“把那家伙给我带过来!”侯爵老爷朝那开道的仆役吼道。
那人给带了过来,帽子拿在手中。其他人也都围拢上来看着,听着,那神情就像是巴黎喷泉边观光的游客。
“我在路上碰见过你?”
“是的,老爷,一点没错。我有幸见到您过去。”
“在上山时和在山顶上,是两次?”
“是的,老爷。”
“你当时在看什么,那么死死盯着?”
“老爷,我在看那个人。”
他稍稍弯下腰,用那顶蓝色的破帽子指着马车下面。在旁的村民也都弯腰朝马车底下望去。
“什么人,臭猪?为什么要朝车底下看?”
“对不起,老爷,他挂在车闸的链子上。”
“谁?”侯爵问。
“老爷,就是那个人。”
“见鬼去吧,这班白痴,那人叫什么?这一带的人你们全认识。他是谁?”
“求老爷开恩!他不是这一带的人,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他。”
“挂在链子上?想找死吗?”
“求老爷恕我实说,这事儿是有点蹊跷。他的脑袋倒挂着——就像这样。”
他侧身对着马车,脑袋朝后仰去,脸孔朝天,过后才挺直身子,揉着手中的帽子,朝侯爵老爷鞠了一个躬。
“他什么模样?”
“老爷,他比磨面的还白。浑身全是灰,又白又高,像鬼一样!”他的这番描述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侯爵老爷,也许是想看看,他的心里是否有鬼。
“哼,你倒不错,”乖巧的侯爵说,觉得不值得和这种小人物多费口舌,“看到一个贼挂上我的马车,也不肯张一张你那张大嘴。呸!叫他滚一边去,加贝尔先生!”
加贝尔先生是驿站的站长,还兼管收税的差事,他早就站出来非常巴结地为这场盘诘帮腔,而且一直以办公事的神气,抓住受盘问人的袖子。
“呸!滚一边去!”加贝尔先生喝道。
“加贝尔,要是那个陌生人今晚到你们村子里来过夜,你一定得把他抓起来,查明他是不是干坏事的。”
“是,老爷,能为您效劳,不胜荣幸。”
“喂,那家伙跑了?——那个该死的哪儿去了?”
那个该死的已经和五六个伙伴一起钻到马车底下,正用他那顶蓝帽子朝链子指点着。这时,那五六个伙伴急忙把他拖了出来,把气喘吁吁的他推到侯爵老爷的面前。
“那个人是不是在我们停下来安车闸时跑掉的,傻瓜?”
“老爷,他一头就朝山下栽下去了,脑袋朝下,像跳水似的。”
“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加贝尔。走!”
那五六个察看链子的人,还像羊群似的挤在车轮中间。车轮突然启动,他们侥幸保住了自己的皮和骨头;除一张皮和一副骨头,他们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保全的了,亏得如此,要不恐怕就没这么幸运了。
马车一溜烟冲出村子,驶上了村后的山岗,山岗很陡,车子的速度马上就慢了下来。渐渐地,慢到了像步行一样,在夏夜的芬芳气息中摇摇晃晃地往上爬着。围绕着车夫打转的不再是复仇女神,而是数不清的蚊蚋。两名车夫都默不作声,只是挥动鞭子催赶着马匹。跟班的随在马儿旁边走着,开道的仆役小跑上前,消失在暮色中,嘚嘚的马蹄声依稀可闻。
在山岗最陡峭处,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立着一只十字架,上面有一尊新雕的耶稣受难像。雕像是木雕的,很粗陋,显然是某个没有经验的乡下木匠的杰作,不过他倒是根据现实生活创作了这一形象——也许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吧——雕像极其瘦小。
在这象征苦难日益深重、永无尽头的雕像面前,跪着一个女人。当马车驶近身旁时,她回头一看,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到车门前。
“啊,是您,老爷!老爷,求您一件事。”
老爷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脸上毫无表情地朝外看了看。
“嗯,怎么啦!又有什么事?老是求这求那的!”
“老爷,看在仁慈的上帝分上吧!我男人,那个看林子的。”
“你男人,那个看林子的怎么啦?你们这班人总是这个样子。又有什么交不起了吧?”
“他全交清了,老爷。他死了。”
“好哇!那他就安宁了。我能让他给你活过来吗?”
“哎,不,老爷!可是他就躺在那儿,在一小堆野草下面。”
“唔?”
“老爷,这儿野草堆太多了。”
“那又怎么样,唔?”
她看上去像个老太婆,其实还很年轻。她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两只骨节突出、满是青筋的手,不断地使劲互相握捏着,随后又把一只手轻轻搁到车门上,抚摸着,仿佛那是人的胸膛,会对她的祈求有动于衷。
“老爷,听我说呀!老爷,我求求您!我的男人是饿死的,那么多人都是饿死的,还会有更多的人饿死。”
“那又怎么样,唔?我能养活他们?”
“老爷,这只有仁慈的上帝知道了;不过我求的并不是这个。我求的是允许我用一小块石头或木头,刻上我男人的名字,立在他的坟前,好有个标记。要不,这地方很快就会记不清的,等到我也一样饿死时,就更加找不到,我就会被埋在别的野草堆下了。老爷,长满野草的孤坟这么多,还增添得这么快,受穷挨饿的太多了。老爷!老爷!”
跟班把她从车门旁推开,马车突然轻快地朝前驶去,车夫挥鞭加速,一会儿就把那女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侯爵老爷又在复仇女神的伴随下,飞也似的朝一两里格外的府邸驶去。
四周弥漫着夏夜的芬芳,就像不偏不倚的雨水一样,这芬芳也一视同仁地弥漫在离此不远的水泉边那群穷人的周围,他们满身尘垢,衣衫褴褛,劳累不堪。那个修路工,手中拿着那顶必不可少的蓝帽子,指指点点,还在对他们大讲特讲那个鬼怪似的人,大家都耐着性子听着。渐渐地,他们不想再听下去了,一个个逐渐散去,于是一扇扇小窗子里亮起了微弱的灯光。灯光闪烁着,待到窗口变成黑洞时,更多的星星出来了,仿佛灯光并没有熄灭,而是飞升到天空了。
这时,侯爵老爷来到了一座高大的邸宅和许多低垂树木的阴影前;当他的马车停住时,那阴影转换成一片火炬的光亮。府邸敞开大门迎接他了。
“我等着见查尔斯少爷,他从英国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老爷。”
第九章 蛇发女怪的头
侯爵老爷的府邸是座庞大、坚固的建筑,前面有个大石块铺成的场院,两道石砌的阶梯在正门前的石头平台上汇合。四面八方,什么全是石头的:沉重的石栏杆、石瓮、石花、石刻人面、石雕狮首,仿佛早在两世纪前,这座建筑刚落成时,蛇发女怪就曾光顾过这儿。
侯爵老爷跨下马车,在火炬的引导下,走上了宽阔平坦的石级,这一来搅扰了黑夜,惹得远处树丛中马厩顶上的一只猫头鹰大声地抗议。此外,一切都寂静无声,连那沿阶而上和举在大门口的火炬,都像在一间紧闭的大厅中燃烧,而不是在夜间的露天里。除了猫头鹰的叫声和喷泉落入石池的叮咚声,万籁俱寂。黑夜仿佛一连几小时敛声屏气,然后轻轻地长叹一声,接着又停止了呼吸。
大门在侯爵老爷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他穿过一座大厅,里面陈列着一些古代的长矛、短剑和猎刀,阴森可怖;更可怕的是那些沉重的马棒和马鞭,许多已回到他们的恩人死神那里去的农民,在他们的老爷发怒时,曾体验过它们的分量。
侯爵老爷绕过那些漆黑的、夜晚锁上的大房间,在举着火炬的仆人引导下,走上楼梯,来到回廊的一扇门前。门打开了,他走进了自己三套间的内室——一间卧室,另外还有两间。房间有高高的拱顶,地上没铺地毯,十分凉爽,壁炉里安着冬天烧柴取暖用的大柴架。摆设应有尽有,穷奢极侈,完全符合一个奢侈时代的奢侈国里的侯爵身份。富丽堂皇的家具中,最显眼的是上一代路易王朝——那可是传之永世的帝业啊——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不过其间也还有着许多别的陈设,反映了法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时尚风格。
供两人食用的晚餐摆在第三间屋子里。这是一间圆形的房间,坐落在一座塔楼的熄烛筒形的楼顶。这府邸里共有四座这样的塔楼。这间居高临下的小房间,窗户大开,木板条百叶窗关闭着,因此只能看到一条条形成平行细线的夜色,还有那与黑线相间的宽宽的石青色窗叶。
“我侄儿,”侯爵看了看准备好的晚餐,说,“据说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