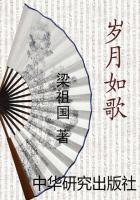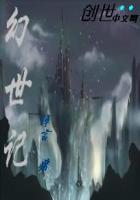庐山雾
“不识”皆因“只缘”,苏老夫子捋须在西林壁涂抹的那一雾,一飘千载,让庐山成为千古诠释的一个谜。
苏东坡的雾写在含鄱口,写在庐林湖,写在仙人洞、锦绣谷,写在都说是伟人头像的五老峰。
我伫立在含鄱亭,看白雾从谷底涌起,如惊涛,如雪浪,呼啸着,呐喊着,排山倒海,直扑山顶。顿时,众山皆成浮在雾海中的孤岛。于是庐山变得很文化,很禅意,你在雾气中沾濡灵气,引发绵绵遐思。
我仿佛听见雾的跫音,铿然作响,漫过我的脚面。我的衣袂飘起,灵魂脱窍而去,随雾升腾。此时,你真可以像朱自清所言:“什么都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我从缥渺中觅得自我,从虚无中获得真实,顿感对高山不必却步,临深渊毋须胆寒。
须臾间,雾填平了谷壑,充盈了天地,山飞走了,水不见了,树隐去了,眼前唯余白茫茫一片。俄顷,不知谁人拉开了遮天幂地的帷幔,云雾消散,山向你走来,水向你扑来,树向你迎来。庐山雾像雪白的棉纱,把山抹得更青,把水拭得更亮,把树擦得更绿,山河永恒,江山更加妖娆!
我看到雾走过庐林湖,如白衣大士乘莲座旋于湖面,拈花而行。雾像揉碎的花瓣,纷飞飘落,在湖面燃成火,燃成雪,燃成山野不变的春天。庐林湖恰似一个僧钵,钵底有龙在吟啸,潜龙在听经。庐山雾又如仙鹤,飞渡仙人洞,在锦绣谷栖留,于是满谷爆出花的笑声,泛起霞的流彩。
庐山雾春如乳夏似纱秋如烟冬为絮,变幻莫测,神秘幽奥。如果说庐山是一部书,雾则是她的封面,揭开它才能细味庐山。阖上它,依然挥之不去,回味无穷。雾中的庐山雾中的花,愈扑朔迷离,不识其真面目,就愈叫人心醉神往。
庐山啊,你是一位睿智的老者,那茫茫的白雾,是你飘飘的银须。
在波谲云诡的近代史中,你既置身其中,又不处于风暴中心,因而你才可以叱咤,才可以指点,才可以挥斥方道,如中流砥柱,拔地擎天!
井冈吟
跃上“天下第一山”,车抵井冈茨坪,放眼望,燃亮你双眸的是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吸一口浩瀚林海吐出的负离子,犹如喝下一杯竹叶青酒,叫你未抖旅尘心先醉了。
在下榻的酒店,煮沸了山泉,撮一把井冈雾、摘几朵井冈云,撒入壶中。茶杯里冲出窗外一片风景:欧陆式的现代华美建筑,与白墙黑瓦的“干打垒”农舍相映成趣。70年沧桑巨变竟浓缩在咫尺之间。
寻常农舍,却是亿万人心仪的革命中枢,恰如今日的中南海。我仿佛看见窗棂间透出如豆的灯光,映照出一个伟岸的身影,在伏案疾书;军械处的铁砧正在锻造长缨,炉火正红。屋后的竹林,方形的竹竿撑起一片绿云。啊,我轻轻地叩问,方竹啊,毛委员手中如椽的大笔,可是以你作杆?那缚住苍龙的长缨,可是以你为簇?方竹在向晚的风中摇曳,竹叶窸窣作响,似在低吟郑板桥的咏叹:“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
是日,“天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角滴水声”。梅雨初歇,天空放晴。
我站在黄洋界哨口,临风而立,凭栏远眺,但见莽莽苍苍的八百里罗宵井冈奔拥眼底,远去了,当年鏖战的枪炮声;人耳是,今日游人的笑语喧阗。我轻抚矗立哨口的炮筒,铁已冷,血犹热,炮腔里,浴血厮杀的呐喊声,还在铮铮轰鸣。一个巨大的声音,回荡在千山万壑:“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谁曾想到,在寂寂群山环抱的大井,那几间土房里,点燃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神州大地,从上房里传出的春雷,可以响彻寰宇。我看见,那几间白墙黑瓦的农舍,静立在雨后的苍穹下,屋前三两株缀满繁花的树,枝头春意正闹,眼前分明是一幅淡墨濡染的国画,宁谧而祥和。只有当你目睹屋后一堵残墙,墙上布满蜂窝似的弹孔,你才会想象出“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惨烈,不禁肃然兴叹。
井冈山,英雄山,共和国的伟大摇篮!
“小道”颂
这是一条寻常的小道,横卧在南昌近郊。
这是一条弯曲的小道,在荒芜的草丛中蜿蜒。
在那“文革”浩劫的日子,在那风狂雨骤的岁月,一个落难的长者,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用双脚,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了这条小道。
不论晨昏,不论寒暑,走过雨中的泥泞,走过雪中的湿滑。老人孤独地踽踽而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狂风暴雨曾使小道淹灭,霜刀雪箭曾令小草披靡,老人又用双脚走出一条新路。
这是怎样的一双脚啊!他曾戎马倥偬,驰骋疆场,踏遍太行,濯足长江。他曾无数次登上天安门,站在共和国大厦的高端。
而今,这双脚:叉重踏长征路,一步一个脚印,叩问这块神奇的红土地:新的长征路指向何方?
这条小道像琴弦,弹奏出新时期的交响乐章。
这条小道成为奔向现代化康庄大道的起始站。
老人在小道上默默地走着,他是在构思共和国未来的蓝图吗?
老人在小道上烙下坚实的脚印,他是在积蓄复出主政的巨大能量吗?
这条小道,当地工人把它命名为“小平小道”。
小道在一幢破旧的厂房后墙外面,静静地穿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荒郊,在艳阳下闪着黄色的亮光,向前伸延。
小道啊,你伸向何处?奔向哪里?
蓦然,心底涌起黄庭坚的吟唱:我欲穿花寻路,直人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
小道啊,你走进亿万人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