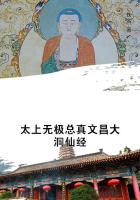警卫团的哨兵看到了战车扬起的灰尘,马上拿起武器。指挥官阿斯莫尔和他的军官们全身戎装迎接纳加领主。军团士兵们严阵以待,在他们身后列好阵势。
“阿斯莫尔领主!”纳加在战车上朝他喊道。“我有可怕的消息要带到底比斯的政务会。法老被一支喜克索斯人的箭射死了。”
“纳加领主,我随时准备执行您的命令。”
“埃及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纳加在羽毛装饰的、华丽夺目的战士队列前停下战车。为了他的声音能清晰地传到后排的队列,他提高了嗓门。“尼弗尔王子还是一个孩子,还不能马上统治国家。埃及此刻非常需要一位摄政王来领导他,以免喜克索斯人利用我们的混乱。”他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注视着阿斯莫尔。阿斯莫尔微微地抬起他的下巴,对纳加给予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他已经得到许诺,他的回报要比他曾梦想的要多得多。纳加将他的嗓音提高:“如果法老在战场上倒下,军队有权力在战场上经口头表决任命一位摄政王。”阿斯莫尔站在那里陷入了沉默,将一只握紧的拳头放在胸膛上,另一只手握着长矛。
阿斯莫尔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把脸转向全副武装的警卫团的队列。以做作的姿势,摘掉了他的头盔。他的脸色阴沉而严厉。一处被剑砍伤的淡色的疤痕使他的鼻子扭向一侧,他剃光的头顶覆盖着一层用马尾编织的假发。他将剑指向天空,然后,以一种运用于压过战场喧嚣的嗓音大叫道:“纳加领主!向埃及的摄政王致敬!向纳加领主致敬!”
在军团爆发出像觅食的狮群一样的吼叫声之前,士兵们惊愕得沉默了好一阵。“向纳加领主致敬!向埃及的摄政王致敬!”
欢呼声和喧嚣声一直持续着,直到纳加领主又一次举起他的拳头时才停下来。在一片静默之中,他清楚地讲道:“你们给了我极大的荣耀!我接受你们给予我的职责。”
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用剑和矛击打着盾牌,那回声像远方的悬崖上响起的沉雷。
在一片喧嚣声中,纳加招唤阿斯莫尔到他身边来:“在路上安排好岗哨,在我离开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消息不准到达底比斯。”
他们从加拉拉出发后经过了三天艰苦的骑行。马匹累得筋疲力尽了,就连纳加也感到疲惫不堪。然而他却只给自己一小时休息时间,洗掉旅途的尘土,换一下衣服。接着,刮刮胡子,梳洗头发并涂了点儿油,他登上了阿斯莫尔准备好的礼仪战车,阿斯莫尔此时正等在帐篷入口处。装饰着挡板的金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纳加穿了一件白色亚麻裙,一副镶嵌着黄金和宝石的胸甲覆盖着他肌肉发达的胸膛。在他的臀上佩戴着从法老的尸体上取下来的那柄传奇般著名的金鞘蓝剑。剑刃是由某种神奇的金属锻制的,比青铜更重、更硬,也更锋利。在全埃及独一无二。它曾一度属于哈莱布领主塔努斯,是他遗赠给泰摩斯法老的。
不过,在他所有装备中最有意义的是最不显眼的那件物品。在他的右臂肘部的上方——由一条普通的金带包着的是蓝色的鹰玺。像那把剑一样,纳加是从泰摩斯法老的尸体上取下来的。作为埃及的摄政王,现在的纳加有资格佩戴这种象征帝王权力的徽章。
他的警卫围着他排好,整个军团在他的后面列队。他身后一共有五千名士兵,纳加——埃及的新摄政王开始了向底比斯的进军。
阿斯莫尔作为他的持矛卫士前行。就指挥整个军团而言,他很年轻,但是在抗击喜克索斯人的战斗中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并且他也是纳加亲密的同伴。在他的血管里也有喜克索斯人的血。阿斯莫尔一度把指挥一个军团作为他追求的最高目标,现在他已经到达了山麓小丘上,在他的面前,突然矗立着不受约束的权力、加官进爵的广阔前景。为了加速他的恩主——纳加登上埃及王位,现在他没有什么不会去做的,再不道德的行为他都会欣然接受并乐此不疲。
“现在是什么挡在了我们的面前,我的老伙计?”纳加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这个问题提得太恰当了。
“黄花已经都清理好了,你成功路上的唯一障碍就是泰摩斯王室仅存的王子了,”阿斯莫尔回答道,然后用他的长矛顺着尼罗河那灰色淤沙的水域指向那远方的山峦。“其他人就躺在国王谷的坟墓里。”
三年前,黄花瘟疫普降埃及的两个王国。这个疾病如此命名是因为:在患者死于瘟疫的高烧之前,他们的身体和脸都被可怕的黄色损伤覆盖着。瘟疫对人可谓一视同仁,不分出身贵贱,不分平民王子,不分地位高低,不分性别男女,不分大人孩子,不分民族种姓,不论你是埃及人还是喜克索斯人,都难逃此劫。人们遇到它就如同田野里的高粱遇到了镰刀。
泰摩斯王室的八位公主和六位王子都死于黄花瘟疫。在法老所有的孩子中,只有两个女孩儿和王子尼弗尔·迈穆农活下来了。在阿斯莫尔看来,好像众神已经开始深思熟虑地为纳加领主扫除登上埃及王位之路的障碍。
有人说,如果不是足智多谋的泰塔施行魔法救了他们的话,尼弗尔和他的妹妹也会因此而死掉。三个孩子左臂的上方至今还有泰塔为他们切割的小伤疤,那是为了抵抗黄花病毒,他在他们的血液中植入了魔法保护而留下的标记。
纳加紧锁着双眉。即使在他胜利的此刻,仍然在忧虑那巫师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魔法。没有人会不承认他已经发现了生命的奥秘。他已经活得那么久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的年龄,有人说他已经活了100岁,而其他的人又说他活了200岁了。然而他走路、奔跑或驾驭战车,都和年富力强的男子汉毫无二致。在辩论的场合没有人会比他表现得更好,在知识的领域里他更是无出其右。想必是神惠顾于他并赋予他生命永恒的奥秘。
一旦纳加成为法老,那是他唯一缺少的东西。他能够从泰塔——男巫——那里强行得到他的奥秘吗?首先,必须得抓住他,连同王子一起捕获,可是不能使他受到伤害。他的价值宝贵无比,纳加派出到东部去侦察的战车会以王子尼弗尔的身份带回国王的宝座,在泰塔的外表下掩饰着生命永恒的奥秘。
阿斯莫尔打断了他的沉思:“我们的帕特警卫军团是艾布纳之南唯一的军队。其余的军队都被调到北部去抵御喜克索斯人了。保卫底比斯的就只有一少部分的老弱病残了。你的路上没有任何抵抗,摄政王。”
处于备战状态中的军团的恐惧都被进城时的情况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当守门的岗哨认出了蓝色的军旗时,大门就被推开了,里面的市民跑出来迎接他们。他们拿着棕榈叶和睡莲的花环,因为整个的城里都传说,纳加领主带来的是他们已经打败喜克索斯的阿佩庇获得了巨大胜利的消息。
但是当他们看到了第二辆战车的踏板上裹着的国王的尸体时,当他们听到了前列的驭手们那“法老驾崩,他被喜克索斯人残害。愿法老永生”的哭叫声时,欢迎的呼喊和笑声很快地被疯狂的悲鸣所取代。
号啕大哭的人群跟着装载国王尸体的战车向墓葬的圣殿走去,他们堵塞着街道。在混乱之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阿斯莫尔所属的士兵分队已经接管了主要街道的警卫们,而且迅速地在每一个广场和每一个角落安置了岗哨。
载着泰摩斯尸体的战车和人群徐徐地行进。通常熙来攘往的城市几乎一片沉寂,纳加的战车队穿过狭窄崎岖的街道向着尼罗河畔的宫殿行进。
他知道,每一个政务会的成员一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都会急匆匆地赶往会议厅。他们在花园的入口处下了车,阿斯莫尔和他的五十名贴身卫兵在纳加的周围列队。他们以密集的序列前行,穿过了里面的庭院,路过满是风信子和尼罗河河鱼的水中花园池塘,那些鱼儿像是水中的珠宝一样在清澈的池塘里熠熠生辉。
这样一伙武装人员的到来令政务会毫无防备。会议厅的门无人守卫,只有四位成员集合在此。纳加在门口停了一下,迅速地扫视了他们一眼。芒塞特和塔拉是年长的两位,已失去了昔日令人敬畏的权力;辛卡为人软弱且优柔寡断。在会议厅里只有一个纳加需要认真对待的、有影响的人物。
克拉塔斯比他们任何一位都年长,但那是一座年深日久的活火山方式的年长:岁月越久,爆发的能量越大。他衣冠不整——很明显他是从床上直接来的,但不是在睡觉。他们说他仍然能和两个年轻的妻子保持和谐的性生活并和他的五个情妇调情,对此纳加毫不怀疑,因为有关他的武功和风流韵事的传说很多。在他白色的亚麻男裙上有新的潮湿的污迹,身上散发出清新的女性肉体的天然香味儿,甚至很明显地可以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纳加理解他。他臂上的伤疤和裸露的胸膛是他多年来参加过上百次战役并获胜的证明。老人不打算戴那些他被授予的勇士金质奖章和嘉奖金牌,因为如此大量的宝贵金属会压垮一头牛。
“高贵的王臣们!”纳加向会议的成员们打着招呼。“我来带给你们不祥的消息。”他大步踏入会议厅,芒塞特和塔拉退缩着,像两只兔子望着弯弯曲曲的眼镜蛇临近似的盯着他。“法老去世了。当他带领我们攻占瓦顿山上的一个敌堡时,被一支喜克索斯人的箭射中身亡。”
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克拉塔斯全都呆头呆脑地、鸦雀无声地盯着他。克拉塔斯是第一个从震惊中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人。他的难过与他的愤怒不相上下。他沉思着站起身来,咄咄逼人地盯着纳加和他的卫士们,像一头在浅滩中的老雄水牛遭到了一群没有长大的幼狮的意外攻击。“你以什么厚颜无耻的叛国行为作借口,竟然胆敢在胳膊上戴上鹰玺?纳加,你这个喜克索斯的烂女人肚子里下出来的廷拉特家的龟孙子,你这个不配趴在他脚下的贱货,竟敢从他那里打劫那个护身符。你那娘们似的爪子也敢把那高贵得令你无地自容的人亲手挥舞过的剑放到自己的腰间!”克拉塔斯的秃顶因为愤怒而变得紫红,他那轮廓分明带皱纹的脸气得直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