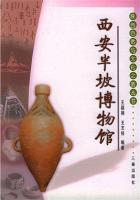“我的天,我是怎么啦?我犯了个错误,这不是我的房间。”萧纳说。
“先生,”柯林和鲁道尔夫同时,对开门的人说,“很抱歉我们的朋友打扰了您,他醉了。”
突然,萧纳迷醉的头脑里闪过一线光亮,他读着门上用粉笔写的文字——“我已经为我的新年礼物等待了三年——凡密。”
“没错,没错,真的是我家啊!”他呼叫道,“这是凡密给我的留言,我到家了。”
“天哪,先生,”鲁道尔夫说,“我真的被你搞糊涂了。”
“相信我,”柯林补充道,“我也同样被搞糊涂了。”
这个开门的年轻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妨你们到我的房间来坐一会儿,毫无疑问,只要你们的朋友进来看看,就会发现他犯了个错误。”
“那好。”
诗人和哲学家给萧纳让道,他走进了房间。显然读者已经明白,这里已经是马切洛的宫殿了。
萧纳用迷茫的目光打量着四周,不停地咕哝着,“真令人吃惊,我的房间怎么被装饰了一番?!”
“哦,现在你满意吗?”柯林问道。
萧纳注意到,钢琴还在,不过位置已经被挪动了。
“这儿,伙伴们,听听这个”,他敲打着音符,“这像什么?
动物总是能认出它的主人,唏,拉,嗦,发,咪,来。啊!可怜的‘来’,你总是这样。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乐器。”
“他坚持这样认为。”柯林对鲁道尔夫说。
“他坚持这样认为。”鲁道尔夫重复对马切洛说。
“还有,”萧纳指着椅子上闪烁之星装饰的衬裙,“难道那不是我的东西?啊!”
他直勾勾地盯着马切洛的脸。
“还有这个”,他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墙上贴着的通告上。
他开始读道:“‘鉴于萧纳先生已于4月8日午前口头承诺放弃这里的财产,并将它们留作租赁房屋的补偿,特此声明所有物品价值5法郎,立此为证。’哈!哈!如果我不是萧纳先生,那么‘特此声明’给谁呢?我的家当就值5法郎?再说还有这些,”他认出马切洛脚上的拖鞋就是他的,“那不是我的拖鞋么?一个心上人的礼物。轮到您了,先生,”他对马切洛说,“请解降一下,您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家用物品中间?”
“先生们,”马切洛对柯林和鲁道尔夫说道,“这位先生,”他指着萧纳说,“是在自己家里,我承认。”
“但是,”马切洛继续道,“我也是在自己家里。”
“没什么但是,先生,”鲁道尔夫打断他,“如果我的朋友认出这些是属于他的……”
“是的,”柯林说,“如果我的朋友……”
“而且,如果你能回忆起这些东西是怎样……”鲁道尔夫补充道。
“是的,”柯林随声附和道,“它们是怎样……”
“先生,请先让这位好心人坐下,”马切洛回答道,“让我为你们解开这个谜。”
“如果我们并不在意你的解释呢?”柯林壮着胆子说。
“说得对。”鲁道尔夫附和道。
四个年轻人围坐在桌旁,开始消灭酒馆招待奉送的一盘冷牛肉。
然后,马切洛开始解释上午他搬进来时发生的事情。
“那么,”鲁道尔夫说,“这位先生没错,我们是在他的地盘了?”
“你们是在家里。”马切洛有礼貌地更正道。
但是让萧纳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着实有些困难。同时,一件滑稽事的出现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当萧纳在餐具柜里东翻西找的时候,他发现了一沓钞票,那是马切洛早上递给伯纳德先生的那张500法郎的零头。
“哦!我就知道,”他惊呼道,“好运不会抛弃我。现在我记起来了,早上我就是为了追求好运而出门的。小半天过去了,在我离开的时间里,它一直都在这里期待着我。也就是说,我们在相互寻找的路途中失之交臂。我多么英明啊,将钥匙落在了我的抽屉里!”
“可爱的愚蠢行为!”鲁道尔夫看着萧纳低声说道。此时萧纳正在将这些钱按相同的正反面排放整齐。
“一场梦,一场虚幻的梦,这就是人生。”哲学家补充道。
马切洛大笑着。
一个小时后,四个人都倒头大睡。
第二天中午醒来,四个人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在一起。
萧纳、柯林和鲁道尔夫似乎互不相识,彼此以“先生”相称。马切洛不得不提醒他们是昨天晚上一起来的。
就在这时,门卫老杜兰德走进了房间。
“先生,”他对马切洛说,“今天是1840年4月9日,街上有泥浆。路易·菲利普仍旧是法兰西和纳瓦拉王国的国王。老天!”当门卫看到他先前的房客时,不禁失声惊叫起来。
“萧纳先生,您是怎么进来的?”
“通过电报,”萧纳说。
“啊!”门卫回答道,“您还是这么爱开玩笑。”
“杜兰德,”马切洛说,“我不喜欢下人插人我们的谈话。
去附近的餐馆弄四份早餐来,这是菜单。”他递给杜兰德一张刚写好的纸条,“去吧。”
“先生们,”马切洛继续对他的三个伙伴说,“你们昨天晚上请我吃了夜宵,请允许我今天为你们提供早餐,不是在我的房间,是在我们的房间里。”他把手伸向萧纳,补充道。
“哦!不,”萧纳激动地说,“让我们永远不分离。”
“对,我们在这里非常舒服。”柯林补充道。
“我得离开你们一会儿,”鲁道尔夫接着说,“明天《艾里斯的围巾》要在一份时尚报纸上发表,我是那里的编辑,必须过去把我的校样改好,我会在一小时之内回来。”
“糟糕!”柯林说,“我想起我还要给一个印度王子上课,他来巴黎学阿拉伯语。”
“明天再去吧,”马切洛说。
“不,不!”哲学家说,“那王子今天要付我报酬。我必须答谢你们。如果我不在书报摊闲逛,今天这个好日子就被我错过了。”
“但是你会回来的,是吗?”萧纳说。
“很快就会回来。”哲学家回答道,他喜欢这些行为古怪的人。
然后他就和鲁道尔夫一起离开了。
“照这么说,”当只剩下马切洛和萧纳的时候,萧纳说,“我也不能在纵情逸乐的枕边流连了,我得出去,想法寻找一些金币来平息那个贪婪无度的伯纳德先生。”
“那么,”马切洛担心地说,“你的意思是也要走?”
“是的,”萧纳答道,“我必须这样,因为我已经收到了正式的中止租赁通告,代价是5法郎。”
“但是,”马切洛说,“如果你离开,你会把你的家具一起带走吗?”
“我有这个打算。但是伯纳德先生说了,我不能带走一根汗毛。”
“糟糕!那会使我很尴尬,”马切洛说,“因为我已经租下了你房间里的家具。”
“伯纳德这个老吝啬鬼!”萧纳回答道。“啊!”他用一种忧郁的语气补充道,“我怎么说得准是今天,明天,还是以后能够找出那么多钱?”
“等一下,”马切洛突然喊道,“我有一个主意。”
“说说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法律上来讲,这个住所是我的,因为我已经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是的,住所是你的,但是这些家具呢?如果我还清了债,我就可以合法地拿走它们,但是现在我只能尊重法律。”
“是这样的,”马切洛继续道,“你有家具却没有住所,而我有住所却没有家具。”
“的确如此。”萧纳说。
“这间房子适合我。”马切洛说。
“对我来说,它也再适合不过了。”萧纳说。
“那好,我们做一笔交易,”马切洛继续道,“和我一起留下来,我来支付开支,你来提供家具。”
“那房租呢?”萧纳说。
“既然现在我有钱那么我就先付,下一次你来付。考虑考虑?”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最重要的是我得接受一个适合我的建议。完全赞同,原本绘画和音乐就是姐妹俩。”
“合法的姐妹。”马切洛说道。
不久柯林和鲁道尔夫一起回来了。马切洛和萧纳把他们的决定告诉了他们的朋友。
“先生们,”鲁道尔夫说着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心口袋,“我正打算请大伙一起出去吃饭呢。”
“刚好我也有这个打算,”柯林说着拿出一枚金币贴在眼睑上,看上去就像一只眼镜片。“我的王子给了我这枚金币让我为他买阿拉伯语入门课本,而那只花了我6个苏。”
“我,”鲁道尔夫说,“向出纳预支了《艾里斯的围巾》的稿费30法郎,我借口说需要钱去接种疫苗。”
“那么这是一个大家都有收入的日子了?”萧纳说,“就是我自己不能拿出任何东西,真感到耻辱。”
“同时,”鲁道尔夫说,“我坚持由我来提供正餐。”
“我也是。”柯林说。
“很好,”鲁道尔夫说,“我们投币来决定由谁付账。”
“不,”萧纳说,“我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说来听听。”
“鲁道尔夫付正餐的钱,柯林付晚餐的钱。”
“这就是我所说的所罗门式的裁决。”哲学家惊呼道。
为庆祝他们的相会,正餐定在位于王妃大街的普罗旺斯饭店。由于他们必须离开房间去吃晚饭,所以他们适度地喝了一些酒。从昨天晚上的柯林和萧纳开始,再到后来的马切洛,这几个人已经变得相当亲密,每一个年轻人都提出自己的艺术观点,都怀着同样的精神抱负和类似的希望。讨论和争辩使他们觉得意气相投,有同样的开玩笑的诀窍:既愉悦大家又不伤及感情。年轻使他们空白的心灵还没有被沾染上污点,很容易被高尚的事物所感染。他们开始于同样的起点并已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认为他们的相遇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的安排,上帝让他们互相牵起对方的手,并且向他们耳语传递福音,那就是人类博爱的惟一宪章——爱彼此。
晚宴的最后,他们都有些情绪消沉,鲁道尔夫站起来,提议为他们的将来干杯,柯林以一小段演讲回应他,那段演讲词既不引经据典,也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风格,仅仅用简洁朴实的大白话来表达,但发自肺腑、率性而出,又是那么易于理解。
“这个哲学家真笨!”萧纳嘟囔着,整个脸几乎扎在了酒杯里,“他竟然帮我在酒里兑水。”
饭后,他们去莫穆斯咖啡馆喝咖啡——就是他们昨晚去的那家小店。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由于受不了他们的激烈讨论,原先常来的熟客渐渐冷落了这个地方。
喝完咖啡和波希米亚利口酒后,波希米亚俱乐部已经宣告成立了。随后他们返回了马切洛的住所,也就是萧纳的安乐窝。与此同时,柯林出去预定了他许诺的晚餐,其他人买了爆竹、烟花和其他的焰火材料。围坐到桌边之前,他们从窗户放出了光彩夺目的焰火,把整个屋子弄得乱七八糟,四个朋友放开嗓门大声地叫喊着——
“让我们来庆祝这幸福的一天!”
第二天早晨,四个人发现他们依旧在一起,但是这次看起来并不惊讶。在他们去忙各自的事情之前,一起到莫穆斯咖啡店吃了顿节俭的早餐,约好了晚上会面。就在那儿,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问天天回来碰面。
他们就是本书中将要反复出现的主人公。本书写的既不是浪漫史,也没有其他的夸饰,从第一页开始,书中的英雄就属于直到今天仍然口碑不佳的阶层,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缺乏正常的状态,甚至他们以此作为托词:正常状态的缺乏正是生活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