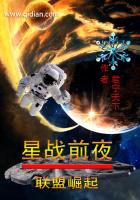此在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在于,“此在以生存为其规定性,它自身是‘存在论的’”。(SuZ,S.18)此在不仅能对生存展开理解,也能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给予理解。也正是基于此,此在体现了其在存在者———存在论(Ontisch-Ontologische)层次上的优先性。因为,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存在论层次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说,正是此在使一切存在论成为可能,一切存在论都必须依凭此在回到存在者———存在论状态。
此在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他把Existenz(生存)写成EK-Sistenz(生—存),义为“绽出”,二者在词源上有一种密切关联。由于此在先于一切存在者,它是存在论上必须首先问及的,之后才能问及存在者,并通达存在。由此可见,“对存在的追问,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对此在本身所包含的根本的存在倾向和先于存在论的存在理解的寻根问底”。(SuZ,S.20)并且,“形而上学奠基的问题在对人的此在的探讨中,即在对人的最内在的根据、对作为本性生存的有限性的存在理解的探讨中,找到了它的根”。(KuPM,S.230)基础存在论之于形而上学也是根本性的。
“因为存在论就是对有限性的一种指示。”基础存在论有别于一般的形而上学,“基础存在论是为了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而必然要求的、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KuPM,S.1)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与基础存在论的关系一直是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与基础存在论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其实,即使有差异,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无论是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还是基础存在论,其共同本性在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消解,或为形而上学作本源性的奠基。
此在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是理解与把握海德格尔早期美学思想乃至整个思想的重要问题。此在是人的基础和规定,而不是人,这正是他消解主体论的一种努力。不少研究海德格尔的著述,把这种关系作了不恰当的解释。有的著述把海德格尔思想导向了人学、人类学或人本主义;又有的著述把海德格尔思想与反人学、反人类学或反人本主义关联起来。这些处置都是对海德格尔思想自身的不理解、误读与臆测。因为,海德格尔思想与这些方面都没有意义的相关,不能这样“分门别类”地归入。在英加登那里,审美认识论与价值论有相当的地位,尽管基于艺术本体论,文艺作品仍然是纯意向性的客体,这与海德格尔早期美学的区分也是明显的。杜夫海纳也未走出审美的对象与主体相关联的模式。在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海德格尔更强调语言始源的与根本的地位,这一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存在论背景。
海德格尔也曾把此在说成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而此在又总以这样或那样去存在的方式是我的此在”。(SuZ,S.57)值得注意的是,此在往往用中性冠词,这表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存在者,又有别于有性别特征的人,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力图摆脱传统主体论美学和哲学的地方。同时,此在也不同于道德意识。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先于任何心理学、人类学,更不用说生物学了。”(SuZ,S.60)在此,其实已充分表明,此在的分析对于这诸多的学科来说,是根本性的。
“对于海德格尔,人类学的问题不是主要的。海德格尔并不太关心人类生存对其自身的意义。只是当存在涉及存在之史诗问题的时候,人类才在他的思考中出现。存在在人身上成为问题,人成为必要,都是因为存在成了问题。人是一种存在方式,此在就是存在成为问题这一现象本身。”梅洛—庞蒂把人的存在当做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础和本源,又把知觉而不是情绪体验作为人的存在的先验结构。当然,这里的“人”已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同时,海德格尔的不解的存在之谜,梅洛—庞蒂相信凭知觉可以把握。
海德格尔分析了笛卡儿的CogitoSum(我思故我在)这一近代哲学之基本起点,它是近代以来主体性美学和哲学的基础。在笛卡儿那里,“我在”与“我思”虽然是同样源始的,但问题在于,笛卡儿那里的“我在”是未经讨论的,而“只有规定了Sum(我在)的存在,才能搞清楚Cogitationes(思想)的存在方式”。(SuZ,S.61)海德格尔消解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中主体的思与在的逻辑关联与推理关系。此在通达存在,并思存在,而不是思物之物性与人之人性。海德格尔把笛卡儿的“我在”放回到存在论层面上去,而不再把“我在”作“我思”的逻辑结果。“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一切主体与对象、意识与存在、人类与自然的二元论,都是从存在与此在的源始统一中引申出来的第二位的和‘非本真’的东西。”二元论必须回归基础存在论。
理性主义及其对立面非理性主义,都不能关切基础存在论。同时,海德格尔批判了康德主体性思想,“这种批判间接表明通过主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无效的,而这种方法在胡塞尔的主体性现象学中却至关重要,这就使得胡塞尔对于康德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和敬意。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主体论现在已经失败,这是由于人在本质上的限定性,即人的直观依靠他自身以外的力量”。胡塞尔与康德一样,都属于这种主体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论关联于概念的运动,存在只是在质和量的范畴中得到把握。在物性本身的存在论渊源得到阐明之前,主体、灵魂、意识、精神、人格这类东西的存在,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领会。
海德格尔反对将此在与意识、心灵、精神等东西等同起来。在存在论阐明作出之前,这类东西既不可能获得规定,更不能通达存在。生命哲学的根本缺陷,也在于“生命”本身从未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成为问题。狄尔泰的研究由于基于追问“生命”得到的激励,暴露了他问题的提法和应用概念方式的限度,未能将生命理解为存在论上的存在方式。人格主义与哲学人类学也未能幸免受制于此限度,“而所有‘人格主义’流派和哲学人类学的倾向,都与狄尔泰和柏格森一道受制于这些限度”。(SuZ,S.63)显然,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与这些生命哲学、人格主义和哲学人类学是相区分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关于人格的阐释,也不能进入此在的存在问题这一维度,胡塞尔与舍勒虽然在许多方面大不一样,但在人格阐释方面却是一致的,“它们都不再提‘人格存在’本身的问题”。(SuZ,S.63)从而,不能为人格的阐释奠定一个生存论的基础,是生存论上未经讨论的。同时,“海德格尔是那样坚信胡塞尔的‘我思’是令人神迷的诱惑陷阱,以致全然避免在他的对此在的描述中求助于意识”。此在是思想回到事情本身的基础。萨特强调得更多的是人的自由之本性,不能理解与把握海德格尔由此在探问存在的意图与努力。同时,在萨特美学中,想象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他与海德格尔美学的重要区别。
传统人类学,一方面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另一方面认为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理性的存在方式,仍然不是存在论上的,是晦暗不明的。上帝的存在在存在论上凭借古代存在论得到解释,对人的解释也是如此。因此,基督教神学不能使人的存在在存在论上成为问题。对于心理学也一样,现代心理学已具有人类学倾向,即使把心理学与人类学合建为一种普遍的生物学,也仍然缺乏存在论的基础。作为“生命的科学”的生物学虽奠基于此在的存在论,但生命既不是纯粹现成存在,也非此在。生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但本性上只有在此在中才能通达。
这在于,“实证研究看不见这种基础,而把这种基础当做不言而喻的;但这却并不表明存在论之基础不是基本的东西,也不能表明存在论基础不比实证科学论题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成为问题”。(SuZ,S.67)因此,实证研究不能真正地奠定或代替存在论基础。新康德主义为了使哲学摆脱当时的实证科学对哲学的限制,把哲学规定为不再去关注存在者,而是去关注对存在者的认识。但海德格尔仍然看到了,在新康德主义的思想中,哲学依附于实证科学的发展。由此,他把哲学限定在存在者的存在的领域。
根本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它就是‘在者之在’,一种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谜一样的东西”。要追问存在和解答存在之谜,由于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必须通过存在者来通达,但一般的存在者却不行,惟有此在才能担当此重任。“萨特说过,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不同意这个命题,因为他相信,萨特是在古典的意义里使用‘存在’和‘本质’的;他尽管把传统的说法颠倒了,但仍然不出传统思想的窠臼。”此在没有现成的本性,其本性在此在的存在的追问中展开。在此在那里,存在不是被封闭的,而是以某种方式展开的,对此在进行分析的基础存在论为一切存在论奠定了基础,基础存在论不同于一般的存在论或本体论。此在切入存在者,使存在者敞开、显现。因此,此在是关联存在者与存在的桥梁,是通达存在的必由之路。西方美学史上,关于美究竟是什么的难题的回答,都难免陷入形而上学,其原因在于这些回答均把美的某一“要素”即存在者当做美(存在)的最终根据,而正是此在及其基础存在论克服了形而上学,由此才能通达存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