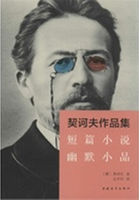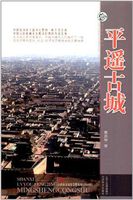“童珍同志,领导来了,这是佐厂长,你有什么事对他说吧。”童珍在医院里是常客了,医院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对症下药,在她面前不敢讲一句过头的话。
“报告佐厂长,”童珍忽地跳下床,啪的一个立正,“我没有完成任务,让盗窃犯跑了,请领导给我处分。”
“快躺下,快躺下。”值班大夫赶紧过来拉她。身上插着输液的管子,也怕她身体虚弱再一头栽倒在地。
“不要管我!”童珍再一次喊出了时代最强音:“我没有完成任务,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请组织上再考验我一次,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又是一个直挺挺的立正,只等领导发话了。
佐其人虽说听着糊涂,但心里已明白了大半:肯定是哪个坏小子拿她开心,冒充领导,让她去追什么盗窃犯,跑到土长城脚下冷饿交加,实在没气力了才昏倒在土长城下的。“童珍同志,由于你及时地追击,盗窃犯没有退路,已经在沟口被我公安人员截获,你任务完成得很好,立了大功,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佐其人也得对症下药,编瞎话还不能露出破绽。“是吗,太好了!”童珍乐得跳起来,值班大夫赶紧走过去把她扶到床上。“听领导的话,现在好好休息吧,啊。”
“是。”童珍应了一句,立刻躺在床上,许是疲劳过度的缘故,很快就睡觉了,脸上还洋溢着甜蜜的微笑。
“能不能再把她送到灵武精神病院?”佐其人问值班大夫。
“已经送过两次了,在医院里又待不住,总偷着往外跑,人家怕出事,不愿收了。”值班大夫解释道。
“嗯。”
其实,这些情况佐其人都十分清楚。童珍神经失常之后就被立即送到灵武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起码不再脱光衣服追打男人了,说话做事比正常人还正常,不细心的人看不出她有什么毛病;实际上她是从医院偷着跑出来的,并且是喊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口号一步一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从灵武走回厂里,身上又没有钱,一路上讨吃要饭,艰难可想而知。不料,回厂后一进她原来的宿舍,大概是触景生情,病情立刻又加重了,于是又送到灵武,稍有好转,又偷着跑了出来,好在这次发现得及时,却说什么也不肯住院,厂里只好把她拉了回来,重新给她换了一个单身宿舍;后来又与她家取得联系,家长的态度却是十分坚决,丫头进厂时是个好人,没病没灾的,既然病是在厂里犯的,我们家里不负责任,就留在厂里吧。狠心把她丢下就走了。好在童珍生活上尚能自理,只要不犯病倒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只是总有些坏小子出于开心,老在她身上搞个恶作剧什么的,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
实际上,童珍的爸爸并非那么绝情,忍心把一个神经失常的闺女扔在大水沟,他也是气急之下出于无奈才做出的决定。开始,他已经同意把闺女带回去治疗,条件是厂里要工资照付,按出差待遇,陪护的人就不要去了,厂里只付钱就行,另外再解决她弟弟的工作。厂里断然给予拒绝,只答应照付工资,其余一概不管。迫于无奈,他又退了一步,提出只要把童珍调回老家就行,按道理,这个要求比较客观,佐其人已经表示赞同,不料书记徐燮一口反对,理由是厂有厂规,原则上不能放一个人出厂,原则就是原则,不能随便变通,其二,今天放走一个,明天就会有一百个人来申请调动,你说童珍是疯子,特殊情况,他们会说他们的神经更失常,比童珍更厉害、更特殊,你照顾过来吗?要是全厂的职工都这么办,人不就走光了吗,厂子还办不办了?所以坚决不能放。童珍的爸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赌气把闺女扔在厂里,坐着火车回了老家,从此再未回来过。
佐其人一想到这件事就来气:人倒是留下来了,可实际问题怎么解决?昨晚上童珍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人家家长交代?气虽则是气,但毕竟徐燮是书记,自己仅仅是厂长,党委会的决议还是要执行的。
“唉。”他长叹了一声,嘱咐值班大夫一定要照顾好童珍,一会儿给他回一个电话,这才转身出了医院,赶紧向办公室走去,昨夜的一场大风总让他放心不下。
果然,办公室里的电话正在铃铃地响个不停,接过来一听,正是供生产用的高压电线被风刮断了,虽然已经派人去检修电路去了,但十几公里的线路不是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
“真他妈的越忙越添乱!”佐其人有气,本来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就紧,再一停电,就越发紧了。他只得一一安排各车间先做好准备工作,一来了电,立即开工,一分钟也不准耽搁,天捣乱,人大干,非得来个人定胜天不可。
临近中午快下班的时候,电送上了,佐其人松了一口气,电话铃却又响了起来。“喂,我是佐其人,哦,什么?!她自杀了!?躺在医院里怎么还能让她自杀?你们怎么搞的?!”电话是值班大夫打来的,赶忙解释:“不是童珍自杀,是四车间一个叫王爱花的女工自杀……”
怎么又一个自杀的?佐其人拿着电话愣怔起来,再没听清电话里讲的是什么。
佐其人匆忙赶到医院的时候,医院的里里外外全是人,和以往一样,人们以过节一样的兴奋谈论着、揣摩着王爱花的自杀。抢救室里更乱,大夫护士们往来穿梭,找东拿西,大呼小叫。佐其人找到值班大夫,简单地问了几句,知道又是喝敌敌畏所致,不禁长叹了一口气,“罗大夫呢?”他问。
罗大夫是抢救喝敌敌畏的专家,以往的十二例都是由她抢救的,有的救活了,有的连神仙也救不活。
“不是成立宣传队吗,她去宣传队了。”
“净扯鸡巴蛋,马上派人给我叫回来。”
“好。”值班大夫口里没说,心里发笑:这规矩还不都是你定的,你尽管骂好了。
佐其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自顾抽烟,一会儿,徐燮和党办主任高明也到了。
“怎么回事?”徐燮问。
“四车间的一个女工喝敌敌畏自杀了。”
“又是敌敌畏?”徐燮皱皱眉头。“什么原因?情况搞清楚没有?”
“我也是刚到。”佐其人冷冷地回答。他现在心烦,跟谁都不想多说一句话。
“小高,你去查一查,看看有什么背景没有。”徐燮知道他的熊脾气,倒也不计较,转向高明吩咐道。
“好。”高明立刻走了。
剩下二人一时无话,默默地坐着,看见罗大夫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便同时迎上前去。
“快去,一定给我救活!”徐燮严厉地下了命令。每死一个人,其家属总要来厂里折腾一顿不说,关键是全厂职工的情绪受到极大的影响,没有十天半月的总是恢复不过来。人心不稳,就像一个炸药库,说不定哪件事就会成为导火索,把炸药引爆。打倒“四人帮”是好事,就是不明白人们的胆子怎么逐渐也大起来了。“我尽力吧。”罗大夫顾不上多说什么,小跑着进了抢救室。
“走吧。”佐其人说。
“走吧。”徐燮道。
守在这里也没啥用,二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到了下午一点的时候,有了确切的消息:王爱花醒过来了,现在基本上脱离了危险期。敌敌畏她没少喝,足足灌了一瓶子,值得庆幸的是她到底经验不足,敌敌畏里没有兑水,也就是没有稀释,这样就减慢了人体的吸收,再加上抢救还算及时,总算救活了。
徐燮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高明也赶了回来,向徐燮汇报了王爱花喝敌敌畏自杀一事的大概情况。
据保卫科长迟人禄讲,第一个发现王爱花自杀并把她送到医院的是她同宿舍的一个姓苗的女工。小苗早起快上班时,才发现一夜未归的王爱花独自一人回到宿舍,精神不振,神情恍恍惚惚,进屋后就一头扎在床上哭起来。小苗问她昨晚干啥去了,她支支吾吾地说是加班,小苗来不及细问就赶着上班去了。在班上她总觉得不太对劲,加班的事固然常有,她不至于回来就哭啊,于是干完了手头的活就提前溜了回来,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敌敌畏的味道,她意识到出事了,一看王爱花,果然是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上,她立刻在走廊里大喊起来,叫来几个人把王爱花送到医院。保卫科顺藤摸瓜,找到王爱花的车间主任,证实王爱花昨晚并没加班,又询问了同车间平时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她的师傅说昨晚她去了二车间的老乐家,老乐说要给她介绍一个对象,他们又找到老乐,老乐说:“是呀,昨晚上我安排她和我徒弟小猪头见的面,就在我们家吃的饭,还喝了点酒,她可能多喝了点酒,就在我家睡的,这丫头,怎么回去就自杀了呢?”
“徐书记,您看这事……”高明汇报完了,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唉——”徐燮长叹一声,未作回答,这事不用调查,他心里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