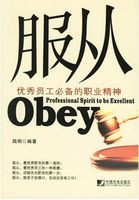那年,我学完算术课程,复习了拉丁语语法,又读了三章恺撒的《高卢战记》。我还读了不少德文著作,其中有些是盲文的,有些是沙利文老师翻译的,比如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弗雷德里希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诗与真》。我很喜欢阅读德语文学作品,特别是席勒的诗句,他对腓特烈大帝取得的光辉历史成就充满了溢美之词,他对歌德人生的描述也非常迷人。读完《哈尔茨山游记》后我意犹未尽,书中的语言诙谐,妙语连珠。满山遍野的葡萄,阳光下波纹点点的小溪,荒野之地的各种神奇传统和传说,幻想时代消失已久的“灰姐妹”都跃然纸上。只有那些对大自然怀有“细致感悟、真挚感情和独特品位”的人,才能够写出如此生动的句子。
吉尔曼先生教授了我一段时间的英国文学。我们一同阅读《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他对历史和文学有着广博的知识,他的精妙讲解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这比我机械地阅读笔记,或是上课时听简短的解释都要轻松愉快得多。
伯克的演讲比我读过的任何一本政论书籍对我都更有帮助。我的心潮随着那个动荡的时代起伏,两个相互敌对国家的各种人物似乎就在我的眼前,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的思绪越飘越远,伯克用流畅出色的文笔,气势磅礴的论证,做出了美国会独立、英国会惨败的预言。英王乔治和他的大臣们怎么会充耳不闻?后来我又读到这位伟大政治家维护他的政党和人们代表的详细资料,不禁觉得奇怪:
这些宝贵的真理和智慧的种子怎么会堕落到无知和腐败的稗子中间去了呢?
麦考雷写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与伯克演讲的风格不同,但同样吸引人。我的心跟随着孤独的主人公在克鲁伯街吞下苦果,在遭受身体和心灵双重折磨的情况下,他仍然言语和善,伸手帮助穷苦的贱民。我为他的每一次成功欢喜;我不忍直视他的错误。令我惊讶的不是他有过那些错,而是它们没有将他打垮,没有让他的形象渺小一分。尽管麦考雷文笔精湛,尽管他有把平凡的情景描绘得鲜活生动的能力,但他过于积极的态度有时让我审美疲劳。此外,为了达到文学效果,他常常不惜篡改史实的做法也让我对他的描述将信将疑。因此,阅读他的文章时,我不像听“大不列颠的德摩斯梯尼2”的雄辩演说时那样心怀敬意。
在剑桥女子学校,我这一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与同龄正常女生做伴的快乐。我与几位同学住在学校附近一所舒适的房子里。这里是豪威尔先生的故居,所以我们生活得像个大家庭。我与她们一起玩游戏,一同打雪仗,一同散步,一同讨论学业,一起大声朗诵感兴趣的文章。有些女生还学会了手语,这样沙利文老师就不用为我翻译了。
圣诞节,母亲和妹妹过来与我共度假日。吉尔曼先生还好心地邀请妹妹也来剑桥女子学校。于是,缪德莉也留下来了。接下来的六个月,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在那些快乐时光里,我们在学习上相互帮助,课余一同玩耍。
1897年6月29号至7月3号,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初试。考试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历史,总共要考九门。我全部通过,其中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
为了避免误会,我还是解释一下考试答题的方法吧。一般要求学生在十六个小时里做完,十二个小时做初级,四个小时做高级,至少要五个小时才能交卷。试卷早上九点从哈佛大学送出,专人送到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每个考生都不报名字,只报编号,我是233号,不过因为我用打字机答题,所以我的身份没法隐藏。
我被安排到一个单间中考试,因为打字机的声音会干扰他人。吉尔曼先生把试卷内容用手语读给我听,还有一位先生守在门口以防打扰。
第一天考德语,吉尔曼先生先把卷子通读一遍,然后逐字逐句念给我。我大声复述一遍,确定没有搞错,然后答题。试题挺难的,我打字很紧张。吉尔曼先生又把我的答案念给我听,我根据需要修改,然后他替我写上。我还想说明的是,以后的考试我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没有人为我念题,我也没有时间检查答案,除非提前做完。这样的话,我能纠正的错误只限于我还有印象的内容,然后把修改的内容附在试卷末尾。如果说我的初级考试成绩比高级考试成绩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高级考试时无人为我念我的答案,以便让我有机会修改;其次,初级考试的很多内容我在入剑桥学院之前已经熟悉,而且这个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吉尔曼先生拿了头年的哈佛试题给我练习,其中的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我都通过了。
吉尔曼先生将我的答卷和一份证明交给考务人员。证明上写着:“试卷是由海伦·凯勒:233号完成的。”
所有其他初级考试都这样进行,都没有第一门德语这么难。我还记得拉丁文试卷发给我时,史其林教授进来告诉我,我的德语考得很好。这个消息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怀着轻松的心情,用平稳的双手,稳步完成了这场马拉松考试。
准备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复试
在吉尔曼先生的学校的第二年伊始,我跃跃欲试,对成功充满信心。然而最初的几周里,我就遭遇到意外的困难。吉尔曼先生为我这一学年制订的学习计划以数学为主。我的课程有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希腊语和拉丁语。麻烦的是,这些教材很多都没有我急需的盲文版,学习器具也有缺失。班上同学很多,老师不可能给我特殊指导。沙利文老师必须把所有的教材都读给我,还要翻译讲课的内容,她那灵巧的手十一年来似乎第一次力不从心了。
课堂上习作代数、几何以及物理题目,是必须亲自动手的,于是我们购买了一部盲文打字机,否则我无法练习。由于我不能看到黑板上的几何图案,我只有在一个垫子上摸索:垫子上有由弯的和直的铁丝组成的几何图案。就像后来凯斯先生的报告里提到的那样,我必须在脑子里面重建和处理这些图表、假设、结论、演算和证明的过程。总之,每门课都有某种困难。有些时候,我感觉勇气全失,情绪失控,还可耻地把焦虑发泄在沙利文老师身上。而她是我各方面都要依赖的朋友,只有她可以让我面前的曲折崎岖道路变得笔直平坦。
但是,我一点一点地克服困难。盲文书籍和各种学习用具也逐渐齐全。我带着更强的自信投身到学习中。我努力学习代数和几何,然而仍然无法理解。我之前也提到过,我没有数学天赋。各种知识点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不言自明。最让我恼火的是几何图表,即使在垫子上摸索半天,我还是搞不懂各个部分之间有什么联系。直到凯斯先生开始给我上课后,我才对数学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正当我步入正轨,逐步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一起事件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的盲文书送到前夕,吉尔曼先生和沙利文老师起了争执。他觉得我学习过于劳累,虽然我竭力反对,他还是减少了我的朗诵课的次数。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如果有必要,我将花五年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然而第一学年结束时,我优异的成绩让沙利文老师和哈勃小姐1,以及其他人都觉得我可以不必花太多力气在两年内完成这些预科课程。起初,吉尔曼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不过,当我的学习任务开始变得不那么轻松的时候,他坚持认为我已经过劳,应该继续在他的学校学习三年。我可不喜欢这个计划,我希望能与同班同学一起上大学。
11月17日,我感觉不舒服,没去学校。沙利文老师知道我的不适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吉尔曼先生听说后,认为我累倒了,修改了我的课程计划,让我可能无法与同班同学一起完成毕业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和沙利文老师的分歧,我母亲最终让我和妹妹一同从剑桥女子学校退学。
经历了一些波折后,一位剑桥的家庭教师莫顿·S. 凯斯先生被安排来指导我继续学习。这个冬季余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沙利文老师是在朋友钱伯林家度过的。他的家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远的伦瑟姆。
从1898年的2月到7月,凯斯先生每周来伦瑟姆两次,教授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沙利文老师给我做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随后八个月里,凯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一次大约一小时。每次他都会向我解释我还不懂的知识点,布置新作业,并把我用打字机写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家,仔细批改,然后送还给我。
就这样,我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准备高考。我发现比起在课堂上听课,这样一对一的教学让我学起来更加轻松愉快。我不用赶进度,有疑惑就立刻提出来,导师有充足的时间为我解答。因此比起在学校,我进步更快,学业更好。数学仍然是我的老大难,要是代数和几何能有外语和文学一半容易就好了。尽管如此,1吉尔曼先生手下的首席教师。
凯斯先生还是能让数学也变得有趣,他能把问题分解得足够小,让我能够理解。
他让我保持警醒与热情,训练我的逻辑思维,使之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清晰顺畅,冷静地推导出结论。不管我有多驽钝,他总是温和耐心。要知道,我的死脑筋有时候可以让最有耐心的人抓狂。
1899年的6月29至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入学复试。第一天考基础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院的教务人员不许沙利文老师给我念试题内容,于是我们雇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一位教师尤金·C. 维宁先生,请他把试题用盲文抄给我。维宁先生与我互不相识,除了写盲文,不得与我交谈;监考人我也不认识,他也没有与我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盲文能充分地表述各种文学语言的内容,但是用来表达几何和代数,困难就出来了。我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特别是代数,这让我非常焦虑和气馁。我熟悉美国常用的所有类型的盲文:英式、美式以及纽约浮点式,然而这三种盲文里面的几何代数符号差别非常大,在考代数时我只用了英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寄给我一份哈佛代数往年真题的盲文版。当我发现试卷用的是美式盲文时,我沮丧透顶。我当即写信要他给我解释这些符号的意思。
他随信寄来一张符号图表,我立刻着手学习它们。代数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在拼命地学习那些异常复杂的标注,但如果一道题中包含大括号、圆括号和根号,我仍旧无法区分出来。我和凯斯先生都很紧张,对明天的考试都有不好的预感。不过我们来到学院,考试开始之前,维宁先生更全面地向我解释了美式盲文数学符号的意义。
考几何的时候,我的主要麻烦是我习惯于按照行列印刷的方式读题,或是让人把问题写在我的手上。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尽管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却发现盲文描述的内容令人迷惑,没法在脑中建立起空间想象。不过还是代数更伤脑筋,刚刚才学会的美式符号让我感觉似是而非。此外,我没法看到我用打字机做的答题。平时我总是靠盲文做题,或是直接在脑子里想。凯斯先生教导我主要依靠大脑去处理问题,并没有特别训练我如何书写答卷。因此我的答题速度非常缓慢,过程痛苦。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读例题,才能搞懂问题的要求。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能正确理解所有那些符号。我发现我当时能保持清晰的思维实属不易。
不过我并不怪罪任何人。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董事会无法知道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也无法理解我需要克服的特殊困难。如果说他们无意之间给我制造了这么多障碍,我还是很欣慰地看到我把它们都一一克服了。
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学习
考大学的奋斗终于结束了。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入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不过入学前,我继续跟凯斯先生学习了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秋季,我的大学梦才得以实现。
我还记得我在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第一天。那天,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我盼望这一天已经多年。内心深处的巨大力量,强过朋友们的劝告,强过内心的理智和犹豫,促使我以正常人的标准来考验我自己。我清楚道路的艰难,但我决心把困难都踩在脚下。我坚信罗马智者的名言:“被驱逐出罗马不过是住在罗马外面而已。”在通往知识的道路上,我没有捷径,不得不在困难中跋涉,这也难不倒我。我清楚,进入大学后,我可以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女士们携起手,一同去思考,一同去爱,一同去奋斗。
我急切地开始了学习。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光明美丽的新世界,让我觉得我有能力学到任何知识。在这思维的圣地里,我和任何人一样自由。这里的人物、景致、习俗、快乐与悲伤,都是用来诠释这个鲜活真实的世界的。讲堂里回荡着伟人和智者的思想,教授们就是智慧的化身。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大学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浪漫学习殿堂。许多让幼稚的我雀跃的幻想都退去虚幻,变得平白无奇。大学的缺陷也渐渐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