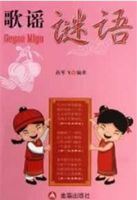虽然我们从一个爱情传奇讲起,但我们懂得,读诗要着眼于文学价值,而不是着眼于作者的故事。正是在这点上,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解读可说是普遍陷入了一个误区,大多数评论是把《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当作爱情传奇而不是当作文学作品来看重的,这就弄得本末倒置了。好比是把《红楼梦》当作曹家与清宫的秘史而不是当作文学作品来看重一样。
为什么会陷入这种误区呢?其原因盖出自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
勃朗宁夫人是个女性主义的先行者,她闯入“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在诗中揭露强暴、卖淫等丑恶现象,她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奥萝拉·李》塑造一个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女作者形象,尽管结尾也变成了幸福的家庭主妇,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期待给予了满足,还是遭到保守的评论界的酷评。《奥萝拉·李》受到许多读者欢迎,但评论界抱着“女性必须从属于男性”的顽固观念,攻击这部作品“违反女性规范,人物塑造糟糕,情节难以置信,冗长乏味,令人反感”,要求家长禁止自己的女儿读这本书。勃朗宁夫人去世时,爱德华·费茨杰拉德代表着男性的偏见,在私人通信里写道:“勃朗宁夫人的死真叫我感到轻松,因为不会有更多的《奥萝拉·李》了!感谢上帝!我知道她是个真正的才女,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她和她的性别最好去关心厨房和孩子,也许还有穷人。”
附带提一笔:勃朗宁晚年在书店里偶然翻到费氏书信集里这封信,引起他唯一的一次狂怒:“我妻子死了他感谢上帝!”这事使他的心脏受了损伤。
男性中心主义的审美观点要求女性成为“房中天使”,若不符合这一规范,则把她“妖魔化”为悍妇和女巫形象。对勃朗宁夫人的作品包括《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的解读,不能不受这种偏见的影响和扭曲。在很长时间里,她的女性主义倾向作品遭到贬斥和抹煞,这位女诗人及其文学成就被压缩到仅剩一个爱情传奇和一部爱情诗集(诗集也只被用于为传奇作注脚),而这个传奇又被描述成“小鸟依人”型的对丈夫的感恩和对家庭的依恋。——按照传统观念,这就是妇女的全部天职和使命。
20世纪初年的评论还曾试图做出如此的定论:“伊·巴·勃朗宁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女人被人们记得的。”
不错,勃朗宁夫人在《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中表现了绝处逢生的衷心感激和恩爱之情,但这并非传统观念所要求的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在身体状况上她的确是弱者,但在精神上她是强者,不是供男性中心主义消费的文学玩偶。在排除偏见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她的诗。
在遭长期冷遇后,20世纪末期女性主义兴起,伊·巴·勃朗宁因塑造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而重新引起关注和重视,2010年出版了伊·巴·勃朗宁的五卷本作品集。
解读他的诗
解读他的诗难度可能要更大些。勃朗宁被认为是英语诗歌中最难懂的诗人,评论家罗斯金就把读勃朗宁的诗比作爬冰川。由于难懂,译介也较迟,所以不少中国读者知道勃朗宁夫人是诗人,却还不知道勃朗宁先生也是诗人而且是大诗人。
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诗歌在19世纪30年代耗竭了能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退潮。浪漫主义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读者对主观抒情、自我膨胀的调子产生了审美疲劳。这时,正是勃朗宁率先改弦易辙,转向了“客观化”的方向,为现代诗开启了新的道路,同时他的主题也从浪漫主义的单纯化转向了复杂化。在许多方面,开创一代诗风的勃朗宁是现代诗的先行者。他作为戏剧独白诗大师,对现代诗尤其是对20世纪重要诗人叶芝、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等都有重要影响。
评论者认为,勃朗宁似乎“跳跃了几大步”,从浪漫主义直接跳到了心理分析。先拉斐尔派诗人斯温本说:“他思想的速度和别人比,就像火车比马车,或者电报比火车。”人们尽力追也跟不上。因此勃朗宁得到承认较慢,在他赴意大利后,诗名才稳步持续上升。
客观化、复杂化和心理分析,构成了解读勃朗宁的难点。读者必须了解:勃朗宁极少作主观抒情,他诗中以第一人称说话的都是客观化的戏剧人物,而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又十分复杂,诗中的矛盾冲突都是从独白者的情感活动中透露出来的。其次,他的诗主题思想复杂化,不像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那么鲜明单纯一目了然。勃朗宁的思想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例如完美理想与不完美哲学,就是突出的一对“对立统一”。他喜欢复杂化并非刁难读者,其实倒是尊重读者,因为以前的诗人都爱“定调子”,把自己的主张灌输给读者,而勃朗宁却把思考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要求读者保持分辨能力。勃朗宁面向的是爱思考的读者群。
解读勃朗宁爱情主题诗,还要加上一个难点,就是诗与诗人真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固然勃朗宁的独白诗是戏剧性的,但也不排除含有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尤其在他的爱情主题诗中,读者和评论者很容易强调勃朗宁的个人成分。有些评论者就从他的“沟通疑难系列”“争吵系列”等诗中,作出了“勃朗宁夫妇爱情神话破灭”的推断;与此同时,舆论也从热炒浪漫的“私奔”,转向纷传他俩的争吵和裂痕。其实这是带夸张的误读,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加以分析。
浪漫理想与现代哲学
众所周知,爱情的浪漫理想与现实生活间有差距,甚至有天壤之别。世间不知几许人已掉进了浪漫与现实间(或神话与神话破灭间)的深渊。所以,推导出“勃朗宁夫妇爱情神话破灭”并不奇怪。
作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他们在意大利的生活传出来的除喜讯外,也夹杂一些不和谐音。他们的意见分歧为大家所知的有:对儿子的教育发生分歧,伊丽莎白把儿子男扮女装,而勃朗宁觉得这对孩子的教育有害;伊丽莎白崇拜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而勃朗宁严厉批判这个政治投机家;伊丽莎白迷上了招魂术,而勃朗宁认为这纯属迷信。人们据此推断:他们俩的爱情神话已经破灭,勃朗宁夫妇的婚姻被说成“根本的不幸和不和谐”与“一场悲剧”。论者认为,读《一个女人的最后的话》等“争吵系列”的诗“应与勃朗宁夫妇的生活相参照,其中反映了勃朗宁夫妇生活中严重而持续的不和”,尤其是勃朗宁的名诗《荒郊情侣》被说成是勃朗宁夫妇裂痕扩大的明证,是“勃朗宁婚姻生活失败的痛苦的自白”。
那么,让我们分析一下作为根据的这两首诗吧。
戏剧独白诗《一个女人的最后的话》反映的是爱人间的争吵。但作者的倾向性其实异常明显,是对大男子霸权的批判也是对勃朗宁夫人女性主义倾向的支持。这不但不能证明他们“严重不和”,而恰好证明了他们在重要观点上协同一致。
爱人间夫妻间有点争吵是难免的,毕竟,浪漫是一阵子,而生活是一辈子。浪漫派诗人心醉神迷地歌唱爱情,从不写这种“毫无诗意”的琐事,而勃朗宁却反浪漫主义之道而行之,开始描写爱情生活的“全息”和“两面”,这正是他的创新和开拓。
《荒郊情侣》是评论界历来争议的焦点,起因则是过分强调了这首诗的个人传记性质。尽管此诗作于勃朗宁夫妇游历罗马郊野之后,也确实包含作者的感受,但绝非简单的纪实之作。此诗寓意深广,探讨的是异化和孤立等现代哲学问题。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那并不是勃朗宁夫妇的“裂痕扩大”,而是在宏观历史背景上,勃朗宁与浪漫主义爱情观的裂痕扩大。
原先,浪漫派观点认为理想世界是和谐的,代表至美至善神性的爱情也是绝对和谐的。然而现代工业化社会改变了人的全部关系,摇摇欲坠的神性王国不得不让位于拔地而起的钢铁企业,书写浪漫主义诗篇的洁白鹅毛笔也不得不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冷峻钢笔了。于是勃朗宁开始直面不完美人生,形成了他的“不完美”世界观,包括探索他的“不完美”爱情诗。
《荒郊情侣》的核心是人的孤立处境和沟通困难。这一主题是超前的,它预示着20世纪现代派文学异化主题的出现。而勃朗宁选择“爱情”这个“最不孤立”“最能融合”的情境来表现孤立主题,尤其显出了他的现代敏感。
是的,爱情意味着沟通和理解,但“理解”只是两个个体经过努力达到部分的有限的交流,而永远不会是绝对的沟通或“融合”(例如,我们作为现代人都知道:任何读者对作品的理解都不可能等同于作者的理解)。与把孤立推向绝望境地的卡夫卡不同,勃朗宁虽已知道理想永远不可企及,却仍保持着永远追寻不息的勇气。
要论勃朗宁夫妇的爱情,那么他们不愧为文学史话中的伟大情侣。他们的爱情专一执著,感情丰富真挚;不论是意见分歧或是《荒郊情侣》,都不能破坏他们的爱情,而只能打破既要有爱情就不许有分歧的童话。
勃朗宁与夫人一样也是儿女情长的人。这位在文学史上终结了浪漫主义的诗人,其实藏着一颗浪漫主义的心。不仅是深情的《你总有一天将爱我》,你瞧他在《忏悔》和《在贡多拉船上》赞美爱情至上价值观,在《骑马像和胸像》中嘲笑缺乏勇气的情人,在《青春和艺术》与《体面》中批判贪图富贵,在“争吵系列”中支持女性而谴责男性霸权——他那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拐带恋人私奔的“骑士精神”,不是呼之欲出么?更值得称道的是:勃朗宁和夫人互相是对方诗的知音,而且有互相“仰视”的关系,这才是真正难得的爱情基础。
伊丽莎白去世时勃朗宁只有四十九岁。从意大利返回英伦的他已是众人仰慕的文坛大师,他也曾“为了儿子”谈过对象但又中途放弃,终身没有再婚。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勃朗宁夫妇的深厚感情。
读这本诗让我们感到:勃朗宁夫妇的爱情诗以诚挚的真情和深刻的探索,为神秘的爱情做了一幅“磁共振”的全息图,为我们留下了珍贵而永恒的文学财富。
本书由飞白统一编注。对方平译的部分,是在综合方平原有注释和赏析的基础上加注的,飞白根据需要作了少量增补。两诗人的姓氏,方平原译作“白朗宁”,现按通用译名统一为“勃朗宁”,谨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