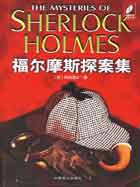(美)马克·萨弗兰科
登上飞机离开洛根国际机场时,司多普教授一直和他的未婚妻柯温德林在玩名字游戏。他还没做出任何决定。他最先想到的是非科学的“赭色喉蜂鸟”,但望着机窗外面五月的天空呈现出迷人的蓝绿色,他觉得还可以用更华丽一点的词,给一本小说加上一个华丽的名字将会使他流芳百世——他脑海中早已掠过“红棕色喉咙标记”这个词——因为这种名字才会给他的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如果能加上他的姓的话,就更好了,但他还没想好怎么弄。他曾写过一本介绍加拿大鸟的手册:“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比根据自己的姓名给鸟起名更能流芳百世的了。”但他先要看看那鸟,仔细研究它的细微变化。
寻找某样东西,使自己名垂青史。这就是司多普教授此次旅游的目的。和伟大的奥尼尔一样,他在学生时代也曾经长途跋涉穿过亚马孙雨林,并且获得了哈佛大学一个专业的教授头衔。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自己以前上当受骗了。现代鸟类学原理告诉他,你要么有所新发现——发现新的鸟类——要么一无所获,但在数学这一学科中,是没有这种要么要么、非此即彼的理论的。第一次的新发现被记载下来并被定为权威时,他还只是个助手,正好也参与其中。但是在那次,他的名字并没有和那新鸟的名字一同写入书中。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私下里研究这一理论:他的赭色喉蜂鸟会在一年正值春暖花开的时节栖息于佛罗里达州西南海岸的一小片土地上,它是由两种罕见的秘鲁鸟交配后产生的混血儿。他的根据是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传说,从有关异类鸟交配、迁徙路线及食物来源这诸种复杂的母体中所产生的信息,以及他一位患病的同事赠送给他的一本笔记。那同事声称,他确定无疑地在某一个场所看到了这种鸟。等这次旅行结束,等他的发现成功地证实并公之于世后,他的那些同事们和竞争对手们将会像一群贪食的、迁徙中的鸟一样,成群结队地赶往那一地区。
下了飞机没多久,他们就已经坐在一家旅馆的餐桌边,一边聊天,一边喝着摩卡咖啡。这家旅馆不但提供住宿,还提供免费早餐,因此,他们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就住在这里。
已经喝到第三杯了。
柯温德林热情地说道:“亲爱的,你一定很兴奋。”她还像年轻人一样耸了耸肩。
一只灰色的非洲鹦鹉正在笼中单调地啄着挂在它头顶上的一些种子的外壳,然后用厚厚的黑舌头把里面的肉吸入口中。司多普教授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看着它。
“兴奋?我当然兴奋喽,但奇怪的是——我又觉得不是真正的兴奋。”
柯温德林说道:“是吗?这可真是奇怪。”
她的心中充满着温馨的友情之火。她有一双与众不同的蓝眼睛,此刻正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姿势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
“嗯,我们这次去那儿一定会成功的,我坚信这一点。”司多普教授伸出舌头把沾在胡子上的一滴咖啡舔掉,“要知道,我为此已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已知的结论,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们迟早会发现这种赭色喉蜂鸟的,只是希望能早些发现。”
他说的“那儿”指的是马克岛的最北端一直延伸到巴尼斯珊瑚岛的一片海边区域。第一天早晨,他们将到离格莱兹顶端不远的环状珊瑚群岛上去,那儿是B·B·威士野生动物的栖息区。格莱兹是个鲜为人知、无人管理的群岛,不大但又互相连接。由于离海岸遥远,区域广阔,因此用肉眼是望不见的。如果想到达那里,必须从海边走过去。
天气真不错,湛蓝清澈,万里无云。柯温德林去年遇见司多普教授的时候,只是个刚毕业的助教,但野外旅行对她来说并不陌生。淡水,三明治和煮鸡蛋,双筒望远镜,太阳帽,笔记本,照相机,驱虫剂,诱饵和捕捉机。这两位科学家准备齐全了这些外出要带的必需品。当他们把租来的运动货车停在路边时,都已经汗流浃背了。
她抱怨说:“上帝啊,这儿真热。”
她沿着满是泥沙的小径往前走着,这条小径将穿过第一个环状珊瑚岛,通往墨西哥海湾。她不停地用她的花色丝质大手帕擦着白皙的额头。
她的丈夫兼良师回答说:“离雨林越近,气温就越高。”
他从头上摘下崭新的旅游帽,摇了摇头,甩落了一地的汗水。
“但是这种热好像要热死人一样。在雨林中,你至少可以有高大的树荫来遮阳,有时甚至能碰上一连几英里的浓荫。但现在的热是不一样的。这种灌木丛,”他用手指着茂密的矮树丛的枝藤说,“一点都不能遮阳挡暑。”
长期以来,司多普教授一直梦寐以求的都是能找到那只珍贵但尚待发现的鸟,因此,他不会因为像酷暑这种微不足道的事半途而废的,也不想被这种不合逻辑的酷热耽搁掉哪怕是一会儿的工夫。
汗出得太多了,他戴的那副无框眼镜已滑落到湿漉漉的鼻子上,眼镜后面是双朦胧的灰眼睛。柯温德林觉得,自己将要做的是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甚至称得上是伟大的事业,她就是从他坚定而沉稳的步伐和这双眼睛中看到了他那种毅力和超人的信念,没错,就是他那坚定的信念。
沿着小路没走多远,他看到一串从灌木丛上重重垂挂下来的淡紫色管状花朵,就停住脚步,用手指着说:“这些花和长在里奥舍砂的植物很相似,是我们要找的鸟儿的最佳食料。”
柯温德林不像教授一样博学多才,她渴望能在天才身边尽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在南美待过,因此柯温德林对他这一番话点了点头。想到他是属于自己一人的大师,她不由得再次激动不已。
她那浓密而金色的波浪形长发如今已经变得脏兮兮的,脸庞纯洁而可爱,四肢美丽而修长,散发出诱人的气息。尽管司多普教授满脑子都被他手中的任务所填满,但也不时地被他这位年轻的伴侣吸引住目光。真不敢相信自己人到中年,竟然还能奇迹般地在不经意中得到一位女神。他摇了摇脑袋,他不过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上被中途搁浅的男人,妻子因患癌症离他而去,没有留下孩子,他的人生从此不知何去何从,陷入了绝望之中。柯温德林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他的身边的,就像来自遥远的幸运之星上的一道金光。为何在人的生命中,当你并非有所努力时,美好的东西就会落入你手中,而另一方面,你为一个既定目标已做出艰苦努力,但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挫败?有时,他会变得烦躁不安,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好运能持续多久……、
柯温德林对他像是动了真情。在离他的那只鸟,那只他知道正在等待他的鸟很接近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阵无法控制的激情。他亲吻了她的嘴巴。自从他们相遇以来,她已唤起了他对异性的渴望。望着她裸露在外的白皙细腻的双腿,他真想马上就拥有她。但这一天至关重要,于是,他们又很快继续上路了。
他一边穿过阴森可怕、毫无动静的沼泽地,一边咯咯地说笑着,样子真像个小混混:“我觉得,我们快要有个孩子了。”。
不管是否疲乏,今晚,如果柯温德林愿意并有精力的话,在那张能俯瞰墨西哥海湾的有着四根帷柱的大床上,他知道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不过他并不为这个假设而担心,她可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姑娘。
小路两旁的灌木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无规则的沼泽地。阴暗的死水面上,一些绿草的藤蔓点缀在上面,看着就像是婴儿那被梳理过的头发。除此之外,还到处飘荡着一枝枝颜色艳丽的花朵,像是被从花束中扔掉的。
柯温德林站在两根已腐烂的古老光秃的柏树桩间没有动:“看,是鳄鱼,不是吗?”
司多普教授正在仔细观察那些长在前面海岸线周围的灌木丛枝藤,听她这么一说,便回过身来向她走去。他心不在焉地咕哝道:“啊,没错,是长在密西西比河一带的短吻鳄,我怎么没注意到……”
离他们十英尺、或许是十二英尺远就是那群鳄鱼的身影。他们那显赫的远古时代的眼睛闪着光亮,像被忘在游戏室地板上的两颗玛瑙那样一动不动,而棕灰色的水面上漂浮着大型美洲鳄鱼特有的岩石般的头颅和口鼻部分。
柯温德林觉得,那鳄鱼正在注视着他俩。“这儿没有警告的牌子,我只是碰巧看到……尽管我知道我们会看到短吻鳄,但还是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碰到。能在它们的自然产区附近看到一只真是令人兴奋。”
她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短吻鳄在世界上的真正产地一个是美国的东南部,另一个是中国的扬子江,在那里可以看到较小的扬子鳄。”尽管司多普教授知道,作为动物学家,这些都是柯温德林应该掌握的知识,但他还是耐心地叙述着。
酷热使她觉得浑身不舒服,而且有些眩晕,柯温德林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是的……但是,我以前从未如此近地接触过这类家伙,除了在动物园里。”
教授用讥讽的口气纠正道:“是爬行动物。”
他那样子仿佛在说逃学的男孩子。
他晃了晃脑袋,继续说:“事实上,外来鸟成了其中一些家伙开胃的美食。在南美洲,都是爬行动物,就在你的脚下。那儿有矛头蛇、大毒蛇、蟒蛇、毒蛙。当然,还有生长在南美的美洲鳄的堂兄凯门鳄。从凯门鳄在力气和奸诈上,比不过这些残暴成性的畜生,但它们也有令人生畏的一面。”
司多普教授再一次把目光移向茂密的树丛中,似乎不想被打搅。他守望着他的战利品蜂鸟。“爬行动物……任何珍贵之鸟的所在地都会出现这些爬行动物,真是不幸……不管是在非洲、巴西,还是……”
柯温德林学过爬行动物学,对于一头饥饿的短吻鳄在干涸的陆地上一小时能爬行多少英里,她一清二楚,也知道为了补充巨大的体能,它需要吃多少肉。一想到在这头一动不动的畜生前,在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走动,她突然不安起来。她曾经在田野里待过,她并不是荒野里一朵娇弱畏缩的紫罗兰,但她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
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偶尔司多普教授会停下脚步,举起他那野外双筒望远镜,向远处沼泽地对面一个发出亮光的地方看去,他一下子就看出那些是什么了,但每次都是以失望而告终。
他叹息道:“不,不是,那只是些漂亮而古老的鲜红色喉蜂鸟。”
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出差错了,自己辛苦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白忙了。他知道,作为一个领导者,没有比犹豫和疑惑更糟糕的了。况且,在这次远征中,还剩下许多天让他有时间找到他的宝贝,他一定能找到他的宝贝的。所以他还是决定不让自己的沮丧表露出来,而是继续向前走去。
他们继续往前赶路,有时用手把挡在路上的枝藤蔓叶清理掉。这条通往墨西哥湾的小道越来越狭窄,最后几乎分辨不出来了。长途跋涉了几个小时后,一块绿草地出现在一个较大海口的边缘处。司多普教授和柯温德林就在这儿停下来,吃着夹有素菜的三明治。
司多普教授轻蔑地说道:“这儿是珊瑚眼镜蛇的最佳栖息地,环境真美。”
他脸对着天空,柯温德林看不到他的眼睛,但也发现他不是真的在关注毒蛇的出现,而是全身心地沉浸在他的探索中。
她刚把三明治送到嘴边,就发出了一声惊叫:“天哪——快看!到处都是……”
“嗯,短吻鳄……”司多普教授朝水面望去。
奇怪的是,柯温德林却一下子变得高兴起来:“艾里思……你觉得危险吗?”
“危险?什么危险?”
“一个人在这里,和这些——”
“爬行动物?不,当然不……我是说,嗯,它们也许是危险的,但是别担心,我并不觉得这些动物对我们特别感兴趣,它们只是在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