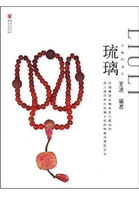十月的美浓,仍然热气蒸人,除了那不能蔽日的椰子叶,连一片凉快的云彩也不会飘来,荷包花被太阳晒低了头。在大陆的北方,已是深秋赏菊的季节了,在这里仍然是盛夏的花朵,其中只有暗中的销凝转换,看不到枝叶的凋零与更新,就像半日的谈话,很难看到老年的台妹展露过一丝笑颜。
走出作家的故居,台妹并没有远送,她的儿子钟铁民在前引导。我走过一段泥土路,铁民说这是他父亲在下田或收工的路上构思小说的路,路边扑扑栩栩的大小蝴蝶,沿着这条花堤之路,似乎朝向钟台妹的破旧藤椅飞去。这些飞蝶,就这样每日不停地在为坠入思念深渊的钟台妹递送着亡夫的信息,使台妹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念,增强了母子相依为命而生存下去的勇气。
【作者简介】王学仲,当代书画大师。1925年10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滕州。出版有诗集《三只眼睛看世界》,长篇小说《吼哈》以及数十部书画作品集。现为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人子课程肖克凡
我抵达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任务是来做儿子的——当我呱呱坠地时就已注定。没有人告诉我当时大家是否吃了喜面,但我敢断定我的到达没有引起他们更多的反感。
只是这个人间又多了一个男婴罢了。
我就开始做儿子了,自觉不自觉便到了如今,很匆忙的。父母没有留给我任何“遗产”,因为他们还都分别活着,不很健康。
很久以来,见过我父母的人,有的说我长得很像父亲,有的说我长得很像母亲,看法很不统一。我想:一定是因为父亲与母亲生得就有些相近吧?才有了这两种殊途同归的说法。
我想我是更像父亲的,我是他的复制。
对于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印象不深。据说四岁时我随母亲去车站送过他。他去了很远,到大西北边疆去工作了。
然而我对母亲也没有更多的印象,这很令我感到遗憾,似乎缺少了许许多多东西。
我在没有父亲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做儿子。几乎没有男性可供我摹仿,我居然一天天成长起来,如今也做了父亲——有了自己的儿子。
我做起父亲来常显得力不从心。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说不清楚。
记忆之中有了父亲,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个隆冬。一个头戴大皮帽身穿皮大衣的人推开了我家的门,他提着肩着许多东西,呼呼喘着粗气。
我问:“同志,您找谁呀?”
这个人就冲着我笑。他很高很瘦,就像今天的我一样,更合秩序地说,今天的我就像当年的他一样。
外祖母在一旁大声说:“他是你爸爸呀!”
我至今没有忘记这句话。这的确是一个开始。
于是有了父亲的起初印象,当时我正读小学一年级。别人都有父亲,我也有了。
我因此而激动。
生平首次看到那么多饼干,是在父亲从新疆带回来的那只小皮箱里。在我眼中那只装得满满的小皮箱简直大得胜过一家糕点店。我一头扎进去,吃了许久才恢复常态。父亲笑了,他当然没有告诉我他在新疆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松了松裤带,只知道在“节粮度荒”年月里我是个最为幸福的儿子。
几天我就吃空了那只小皮箱,像一只耗子。
父亲返回新疆时没有带走那只空空荡荡的小皮箱,他说,明年我还回呢。于是我又成了他遥远的儿子,他又成了我遥远的父亲。
我继续混沌地做儿子,时常想起那一箱不复存在的饼干。班上有几个同学患了浮肿病,我没患。我想这与那一皮箱饼干有关。
而父亲却是两手空空返回新疆的,没带一块干粮,也没带一两粮票。那路,多遥远。
有时我回想那不是一皮箱饼干,决不是。而是父与子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物质。
后来我在母亲授意下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内容我已忘了,大约是告诉他我期末成绩优秀并希望他多多寄些钱回来。这是我识字以来所写的第一封信,也是至今写给父亲的唯一的信。他读信时的复杂感受,如今我已能够大体揣摸出来了。
因为我也做了父亲——身兼两职了。
至今我也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让我给父亲写信。可能是有意训练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吧。
我依然遥远地做着父亲的儿子,很难进入“角色”。那时我学会了看地图。地理课的成绩全年级我一枝独秀,有一次居然问倒了老师。
老师不知道我的“地理情结”,面有愠色。
父亲的再一次出现是很突然的。当时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他在我一次放学的路上候着我,像个伏击者。塞给我一把糖果,他笑着说,我从新疆回来了,我再也不回去啦。
我知道已经属于父亲了,心中十分害怕。这害怕源自一种深深的陌生感。
我给一个陌生的父亲做了这么多年陌生的儿子,陌生得近乎无有。该实打实做儿子了,前景难卜,我在路上偷偷哭了。
我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大街上见到成年男子,便从心底羡慕,只恨自己长得太慢。
难道是我不愿意做一个儿子?至今也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做儿子是人生法定的事情。
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他就另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一段时间是短暂的,就好像我与他从未一起生活似的。
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他再生个儿子将我替换下来,就如足球场上的换人。
然而终于没有“替补队员”将我换下场来,我只能继续下去,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当儿子。
父亲偶尔来看望我和祖母。我仍然觉得他是我遥远的父亲,我是他遥远的儿子。
有时我为自己感到庆幸。
什么是儿子呢?
我长成了,进入社会谋生。先后挪动了几个机关,当小公务员。渐渐,我体味到了人的痛苦,心底很是迷乱。这时我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只是偶尔才想起他来。
其实我根本没有理解“儿子”一词该有多么沉重。它不只说明着一种血缘,一种秩序,还标志着一种角色和角色感。每当我做思想深刻状时,才会切肤感到:做了这么多年儿子,却不是给自己的父亲。我可能永远丧失了,不可追补。就像我不可能退回幼儿园去表现童贞一样。因此我又怀疑自己长得太快,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如此成熟的“儿子”。
我可能永远丧失了。与父亲共同生活的那一段时光,已成为一个常数和恒量,像“兀”值一样不可变更。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光的推移,与他共同生活的那一段时光就愈发显得短暂。
有时我想,我还不如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儿,便用不着在两难处境中而不得要领了。
“儿子”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为复杂的字眼儿。我身为人子却又从未去深深地体验它。
这是一种轻松,也是一种沉重。
你一生都没有实实在在做上他一场儿子,该是多么可悲呀。
为了生存,你早早就将儿子这个字眼儿大而化之而成为一种谋生意义上的心理身份,又是多么可叹呀。
我以为我一生都不可能拥有那种真正父子的体验了。我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儿子”呀。
今年父亲生病了,挺重的。我却忙着在家中给自己的儿子做父亲——全日制,挺忙的。
父亲见了我,说胃疼。其实他已病了多年,很是潦倒的。我说该去医院查一查了。
他没说话,而是将我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们。
“这就是我的大儿子。”
其实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孤本。
我为父亲预约了医院,他拗不过,就随去了。我们一前一后走着。那一天阳光灿烂。
我在前,他随后。这时我蓦然觉出自己很是有些威武的,比父亲强大了许多。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上帝赐给我的一次“补课”的机会。在此之前我已经永远地丧失。
父亲不多言不多语,随着我的安排一项项查体,有时看我一眼又迅速挪开目光。
不知为什么我激动起来。这么多年了,我们第一次共同做着一件他乐于做我也乐于做的事情。这么多年了,我们从未这么长久地相处着,合作得那么好那么成功。
我居然十分感谢医院这个白色世界。
父亲住院了,他的那个家庭似乎忘记了他,无人光顾。我每餐都去病房给他送饭,为了他那多灾多难的胃口。往往返返,我每天要骑行三个小时的路程,这些年我从未这样奔波,很累的。病友们见每天都是我反反复复出现在病房中,从未见“换人”,就常用目光询着。
父亲就说:“这是我的大儿子。”之后就有些自得地笑一笑。
有一次我走出病房就哭了,为了自己。
我懂了,我终于获得了这个机会,走出“儿子”的阴影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自主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从中体味到什么是爱。我不是为了什么社会称谓做着儿子而是为了自己做着儿子。这不是一种称谓而是一种实在。
我终于获救。我因此而激动。
他很瘦我也很瘦,我庆幸上帝如此公平。
他说:“大手术,要花很多钱吧。”
我说:“我有稿费。”在此之前他从未读过我写的小说,可能也不知道我是个作家了。
手术后一次他下床我为他穿鞋,他躲闪着说我自己穿我自己穿。这时我才想到:我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做了这么多年儿子,他也是在儿子不在场的情况下做了这么多年父亲呀。
于是我也懂了什么叫做人子的课程。
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强迫我做他们的“儿子”。
因为我有自己的“父亲”。
我居然在病床前体验到一种苦涩的幸福。
我是个大器晚成的儿子。不是吗?
【作者简介】肖克凡,1953年生,男,一级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鼠年》、《原址》、《尴尬英雄》、《浮桥》等五部,小说集《黑色部落》、《赌者》、《人间城郭》、《中国作家·经典文库·肖克凡卷》、《蓝色鸟》等八部,散文集《镜中的你和我》、《我的少年王朝》。总计五百余万字。中篇小说《黑砂》、《最后一个工人》分别被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改编为话剧上演。有的小说则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作品数次在国内获奖。小说《黑砂》和《都是人间城郭》分别获得“天津市鲁迅文艺优秀作品奖”,小说《都是人间城郭》和《大水泡》分别获得《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小说《最后一个工人》获得《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三八驾校》获第四届“特区文学”奖,2002年获得首届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的文学因缘温皓然
1
被注定的,永远是注定了的。
就像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如此痴迷无悔于写作,就注定要出生在那样一个“被注定”的家庭,历经那些似乎是必须要“被注定了的”、最终使我坚定意志的特殊的人与事一样。
我的妈妈是老三届下乡知青,她在5岁之前(我外公在世之际),是住在小洋楼里的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公主,虽说我外公的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却也很算得上是“活的丰实”了,否则,他那个当时鼎鼎盛名的大资本家真要将生命延长至文革期间,那么,等待他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外公去世之后,我妈妈的生活立刻发生了一连串的惊天之变,然而,还未待她从那些惊变、动荡之中完全回过神来,便不得不瞪着茫然无措的眼睛,响应伟大号召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乌中旗某兵团支援边疆建设去了。时年,她16岁。一年之后,初来时的那个“颜如玉,肤如米”摘自谯达摩《剥玉米@新娘的衣服被单身汉们剥得精光》中的诗句。的城市知识青年早已被一个让蚊虫叮咬得满身都是累累伤疤的小村姑所代替,而就在那时,她与邻村一个出了名的美少年相识了。几年之后,他们在一个名叫“刘蛇”的村庄共同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我出生之时,父母已经将日渐富裕起来的家安在了一个名叫“四牛头儿”的地方,这座小村庄,便是多少年之后我在《箜篌引》里倾尽满腔热情所讴歌描绘的“花溪渔村”——传说中若干年前的“牛头村”——小可爱秦婳的天堂和乐土。由于内蒙话常常是“头儿”、“藤儿”、“屯儿”不分,而我又在那里仅仅生活了不上5年的时间,因而,为了在文章中保证确切,写作前我特地打长途向我的铁面严父(家父为人的冷峻严厉与他那副清雅英俊的外表很是不相称,以致我小的时候常常怀疑自己是被捡来的)请教,并最终得到了圆满确定的答案:我的第一故乡名竟是源于若干年前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名叫“四牛”的有为青年,当时,众人都服他,认为跟着他干有奔头,便推举他当了大家的“头儿”——就是这么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缘起,竟就让我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地写下了洋洋35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