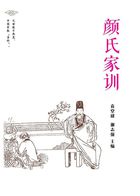诗
漫言真假最难防,不是名花不异。
良璧始能夸绝色,明珠方自发奇。
衣冠莫掩村愚面,鄙陋难充锦绣。
到底佳人配才子,笑人何事苦奔。
话说张轨如同董荣竟往白侍郎府中来,不多时到了府前,下了马,董荣便引张轨如到客下,即忙入去报。白公听了,慌忙走出厅来相见。立在厅上,仔细将张轨如上下一看,只见他生形神鄙陋,骨相凡庸。盖藏再四,掩不尽奸狡行踪;做作万千,装不。书气味。一身中耸肩叠肚,全无坦坦之容;满脸上弄眼挤眉,大有花花之白公看了,心下狐疑道:“此人却不象个才子。”既请来,只得走下来相见。张轨如见出来,慌忙施礼。礼毕,张轨如又将贽见呈上。白公当面就分付收了两样,随即看坐。如又谦逊了一会,方分宾主坐。白公说道:“昨承佳句见投,真是字字金玉,玩之不忍释手!”张轨如道:“晚生末学,偶尔续貂,又斗胆献丑,不胜惶恐!”白公道:“昨见尊作,上写‘丹阳’。既是近又这般高才,为何许久到不曾闻得大名?”张轨如道:“晚生寒舍虽在郡中,却有一个前面白石村中。晚生因在此避迹读书,到在城中住的时少;又癖性不喜妄交朋友,所以不能上达。”白公道:“这等看来,到是一个潜修之士了。难得,难得!”说不了,左上茶。二人茶罢,白公因说道:“老夫今日请贤契来,不为别事,因爱贤契诗思清新,尚恨不,意欲当面请教一二。幸不吝珠玉,以慰老怀。”随叫左右取纸笔来。张轨如正信口儿,无限燥皮,忽听见白侍郎说出“还要当面请教”六个字来,真是青天上一个霹雳,吓都不在身上,半晌开口不得。正要推辞,左右已抬了一张书案放在面前,上面纸墨笔砚正正。张轨如呆了一歇,只得勉强推辞道:“晚生小子,怎敢在老先生面前放肆;况才步,未免一时遗笑大方!”白公道:“对客挥毫,最是文人佳话。老夫得亲见构思,兴浅。贤契休得太谦!”张轨如见推辞不得,急得满脸如火,心中不住乱跳。没奈何,只连打恭,口中糊糊涂涂说道:“晚生大胆,求老先生赐题,容晚生带回去,做成来请教白公想一想道:“不必别寻题目,昨日《新柳诗》和得十分清新俊逸,贤契既不见拒,是新柳之韵,再求和一首见教罢。
张轨如听见再和《新柳诗》,因肚里记得苏友白第二首,便喜得心窝中都是痒的。定了,便装出许多文人态度,又故意推辞道:“庸碌小巫,怎敢在班门调斧!然老先生台命,又不敢违,却将奈何?”白公道:“文人情兴所至,何暇多让!”张轨如忙打一恭道:此大胆了。”遂了笔,展开一幅锦笺,把眉皱着,虚想一想,又将点了两点,遂一直写去。写完了,便亲自起身,双手拿着,打一恭,送与白侍白公接了,细细一看,见字字风骚,比前一首更加隽永;又见全不经想,立刻便成——见张轨如人物鄙琐,还有几分疑心,及亲见如此,便一天狐疑,都解散了,不觉连声称:“好美才!好美才!不惟构思风雅,又敏捷如此!我老夫遍天下寻访,却在咫尺之间,失了贤契!”又看了一遍,遂暗叫人传进与小姐看。遂分付排饭,在后园留张相公小酌。一边分付,便一边立起身,邀张轨如进去。张轨如辞谢道:“晚生蒙老先生台爱,得龙,已出望外,何敢更叨盛款!”白公道:“便酌聊以叙情,勿得过让。”遂一只手挽轨如,竟望后园中来。正雅意求真才,偏偏遇假钞。非关人事奇,自是天心。张轨如随白公进后园来,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婚姻有几分指望;惧的是到恐怕触着情景,又出一题欲做诗,却不将前功尽弃?满肚皮怀着鬼胎。不多时,到了后仔细一看,果然千红万紫,好一个所在!怎见。桃开红锦柳拖金,白玉铺成郁李。更有牡丹分不得,珠玑错落缀花心。莺声流丽燕飞忙,蜂蝶纷纷上下。况是阳春二三月,风来花里忽生。二人到了园中,白公领着张轨如各处赏玩,就象做成了亲女婿一般,十分爱重。又攀谈会闲话,左右排上酒来,二人在花下快饮。
且说红玉小姐,这日晓得父亲面试张轨如,却叫一个心腹侍儿,暗暗到厅后来偷看。这叫做嫣素,自小服侍小姐,生得千伶百俐,才一十五岁。这日领了小姐之命,忙到厅后张轨如细细偷看,只等张轨如做过诗,同白公到花园中去吃酒,方拿了诗回来,对小姐:“那人生得粗俗丑陋,如何配得小姐?小姐千万不可错了主意!”小姐问道:“老爷可他做诗?”嫣素道:“诗到一笔就做成了在此。”随即拿出来,递与小姐。小姐接诗细看一遍道:“此诗词意俱美,若非一个风雅文人,决做不出。为何此人形象来却又不对?”嫣素道:“此事若据嫣素看来,只怕其中还有假处。”小姐道:“诗既面做的,声口又与昨日的一般,如何假得?”嫣素道:“肚皮中的事情,那料得定?只是副面孔是再不能够更改的了。若说这样才子,莫说小姐,便叫嫣素嫁他,也是不情愿的小姐道:“你听见老爷看了诗说甚么?”嫣素道:“老爷只是看诗不看人的,见了诗便称好。此事乃小姐终身大事,还要自家做主小姐因见字迹写得恶俗,已有几分不喜;又被嫣素这一席话说得冰冷,不觉长叹一声,素说道:“我好命薄!自幼时老爷就为我择婿,直择到如今,并无一个可意才郎。昨日此诗,已万分满愿,谁知又非佳婿!”嫣素劝道:“小姐何须着恼!自古说‘女子迟归终,天既生小姐这般才貌,自然生一个才貌相配的作对。难道就是这等罢了?小姐又不老须这等着急。
正说不了,只见白公已送了张轨如出去,便走进来与小姐商议。小姐看见,慌忙接住。道:“方才张郎做的诗,我儿想是看见了?”小姐道:“孩儿看见了。”白公道:“我还疑他有弊,今日当面试他,他全不思索,便一笔挥成,真是一个才子!”小姐道:“人之才,自不消说。但不知其人与其才相配否?”白公道:“却又作怪!其人实是不及其”小姐听了,便低头不语。白公见小姐不言,便说道:“我儿既不欢喜,亦难相强,但失了这等一个才人,却又难寻。”小姐只不做声。白公又想了一会说道:“我儿既狐疑,我有一个主意:莫若且请他来,权作一个西宾,只说要教颖郎,却慢慢探他,便知端”小姐道:“如此甚好。”白公见小姐回嗔作喜,便又叫董荣进来,分付道:“你明日书房写一个关书,备一副聘礼,去请方才的张相公。只说要请他来教公子读书。”董荣白公之命,出来打点关书、聘礼。却说张轨如见白公留他酒饭,又意思十分殷勤,满心欢喜。回到家已是黄昏时候,只友白与王文卿还在亭中说闲话等候。他便扬扬走进来,把手拱一拱说道:“今日有偏二多得罪了!”苏友白与王文卿齐应道:“这个当得。”因又问道:“白太玄今日接兄去定有婚姻之约了?”张轨如喜孜孜笑欣欣将白公如何待他、如何留饭,——只不提起做其余都细细说了一遍,道:“婚姻事虽未曾明明见许,恰似有几分错爱之意。”王文卿:“这等说来,这婚姻已有十二分稳了。”只有苏友白心下再不肯信,暗想道:“若是一首诗便看中了意,这小姐便算不得一个佳人了。为何能做那样好诗?又何消择婿至今?见张轨如十分快畅得意,全不采,便没情没趣的辞了出。
张轨如亦不相留,直送了苏友白出门,却回来与王文卿笑道:“今日几乎弄决裂了!”白侍郎如何要面试他,恰恰凑巧的话,又说了一遍。王文卿便拱他道:“兄真是个福人造化!这也是婚姻有定,故此十分凑巧。——又早是小弟留下一首。”张轨如道:“今谓侥天之幸。只愁那老儿不放心,还要来考一考,这便是活死!”王文卿道:“今日既过,以后便好推托了。”张轨如道:“推托只好一时,毕竟将何物应他?”王文卿道:个不难。只消在小苏面前用些情,留了他在此,倘或有甚疑难题目,那时叫他做做,却一个绝妙解手?”张轨如听了,满心欢喜,道:“兄此论有理之极!明日就接他到园中来”到次日清晨起来,恐怕苏友白见亲事不成,三不知去了,便忙忙梳洗了,亲到寺中来此时苏友白尚未起身,见张轨如来,只得忙起来说道:“张兄为何这等早?”张轨如道小弟昨日回来,因吃了几杯酒,身子倦怠,不曾留兄一酌,甚是慢兄。恐兄见怪,只说为婚姻得意,忘了朋友,因此特来请罪。”苏友白道:“小弟偶尔识荆,便承雅爱,十感,怎么说个‘怪’字?”张轨如道:“兄若不怪小弟,可搬到小弟园中,再盘桓几日不枉朋友相处一场,便是厚情。”苏友白因此事糊涂,未曾见个明白,也未肯就去。听轨如如此说,便将计就计,说道:“小弟蒙兄盛情殷殷,不啻饮醇,也未忍便戛然而去恐在尊园打扰不便。”张轨如道:“既念朋友之情,再不要说这些酸话!”遂叫小喜道:“小管家,可快快收拾行李过去!”苏友白道:“小弟偶尔到此,只有马一匹在后面,并带得行李。”张轨如道:“这一发妙了!”便立等苏友白梳洗了同来。苏友白只得辞谢心,叫小喜牵了马,同到张轨如园中来作寓。张轨如茶饭比先更殷勤了几分。正有心人遇有心人,彼此虚生满面。谁料一腔贪色念,其中各自费精。
三人正在书房中闲谈,忽家人报道:“前日白老爷家的那一位老管家又来了。”张轨如,喜不自胜,便独迎出亭子来。只见董老官也进来。相见过,董老官便说道:“老爷拜公,昨日多有简慢!”张轨如道:“昨日深叨厚款,今日正欲来拜谢,不知为何又承小顾?”董荣道:“老爷有一位公子,今年一十五岁,老爷因慕相公大才饱学,欲屈相公一年。已备有关书聘礼在此,求相公万勿见拒。张轨如听了,摸不着头路,又不好推辞,又不好应承,只得拿了关书与聘礼,转走进来王文卿、苏友白商议道:“此意却是为何?”苏友白道:“此无他说,不过是慕兄高才亲近兄的意思。”张轨如道:“先生与女婿大不相同,莫非此老有个‘老夫人变卦’之”王文卿笑道:“兄特想远了!此乃是他爱惜女儿,恐怕一时选择不妥,还要细细窥探请兄去,以西宾为名,却看兄有坐性没坐性、肯读书不肯读书。此乃渐入佳境,绝妙好,兄为何还要迟疑?”张轨如听了,方大喜。复走出来对董荣说道:“我学生从来不轻人家处馆,既承老爷见爱,却又推辞不得,只得应允了。但有一件事,要烦小老禀过老须得一间僻静书室,不许闲人搅扰,真读得书方妙。”董荣道:“这个容易。”遂起身,竟来回复白。白公见张轨如允了,满心欢喜;又听见说要僻静书房好读书,更加欢喜。遂叫人将后园收拾洁净,又拣了一个吉日,请张轨如赴。张轨如到了馆中,复装出许多假老成、肯读书的模样,起坐只拿着一本书在手里,但看便哼哼唧唧读将起来。又喜得学生颖郎与先生一般心性,彼此到也相合。家中人虽有一得破的,但是张轨如这个先生与别个先生不同,原意不在书,又肯使两个瞎钱,一团和肯奉承人,因此大大小小都与他讲得来,虽有些露马脚的所在,转都代他遮盖过了。这工夫只到读书浅,学问偏于人事。既肯下情仍肯费,何愁奴仆不同。
一日,白公因梦草轩一株红梨开得茂盛异常,偶对小姐说:“明日收拾一个盒儿,请张赏红梨花,就要他做一套时曲,叫人唱唱:一来可以观其才,二来可以消遣娱情。”白才说出,早有人来报与张轨如。张轨如听了,这一惊不小,只得写了个帖儿,飞星着人苏友白到馆中一。苏友白正独坐无聊,要来探一个消息,却又没有头路,恰恰张轨如拿帖子来约他,正中这日要来,却奈天色已晚,只得写个帖子,回复张轨如说道:“明早准来。”张轨如恐了误事,急得一夜不曾合眼。到得天一亮,便又着人来催,自家站在后园门口探望。喜友白各有心事,不待人催,已自来。张轨如看见,便如天上吊下来的,慌忙迎着,作下一个揖,便以手挽着手儿,同走到书来,说道:“小弟自从进馆来,无一刻不想念仁兄。”苏友白道:“小弟也是如此。几来看兄,又恐此处出入不便。”张轨如道:“他既请小弟来,小弟就是主人了,有甚不”正说话,只见颖郎来读书。张轨如道:“今日有客在此,放一日学罢。”颖郎见放学喜去。张轨如道:“许久不会,只在小园题咏一定多了?”苏友白道:“吾兄不在,小弟独处,没甚情兴。兄在此,佳人咫尺,自然多得佳句。”张轨如道:“小弟日日在此,被学住,那里还有心想及此。昨日偶然到亭边一望,望见内中一树红梨花,开得十分茂盛,要做诗赏之,又怕费心,只打点将就做一只小曲儿,时常唱唱。只因久不捉笔,一时再出。”苏友白道:“兄不要将词曲看容易了。作诗到只消用平仄两韵,凡做词曲,连平、入四韵,皆要用得清白,又要分阴阳清浊,若是差一字一韵,便不能协入音律,取识诮,所以谓之‘填词’,到由人驰骋不得。”张轨如道:“原来如此繁难!到是小弟不乱做出来,惹人笑话。兄如不吝金玉,即求小小做一套,待小弟步韵和将去,便无差失不知仁兄可肯见教?”苏友白道:“做词赋乃文人的家常茶饭,要做就做,有甚么肯不肯不知这一株红梨花在何处?得能够与小弟看一看,便觉有兴了。”张轨如道:“这株梨他梦草轩中的。若要看,只消到百花亭上一望,便望得见了。”二人同携着手,走过园到了百花亭上,隔着墙往内一望,只见一株红梨树高出墙头,开花如红血染成,十分可苏友白看了,赞赏不已。因说道:“果然好花,果该题咏!只可惜隔着墙,看得不十分。怎能得到轩子中一看,便有趣了。”张轨如道:“去不得了。这梦草轩是白太老的内,内中直接着小姐的绣阁,岂肯容闲人进去?”苏友白道:“原来与小姐闺阁相通,自不得了。
二人又在百花亭望了一会,方才回到馆中坐下。张轨如一心只要苏友白做曲子——又恐了,苏友白一时做不完;又恐怕做完了,仓卒中一时读不熟,便只管来催。苏友白亦心着小姐,无以寄情,遂拈起笑来,任情挥洒。只因这一套曲子,有分教:俏佳人私开了,丑郎君坐不稳东床。正从来黄雀与螳螂,得失机关苦暗。漫喜窃他云雨赋,已将宋玉到东。不知苏友白果然做曲子否,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