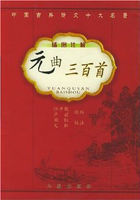诗
冷暖酸甜一片心,个中别自有知。
樽前听曲千行落,花底窥郎半面。
白璧岂容轻点染,明珠安肯乱浮。
拙鸠费尽争巢力,都为鸳鸯下绣。
话说苏友白被张轨如催逼,要做曲子,也因思想小姐,便借题遣兴,信笔填词。只见楮笔墨淋漓,不消数刻工夫,早已做成一套时曲,递与张轨如道:“草草应教,吾兄休笑张轨如接了,细细一看,只见上写“步步娇咏红素影从来宜清夜,爱友溶溶月。谁知春太奢,却将满树琼姿,染成红烨。休猜杏也与桃班班疑是相思。沉醉拟霜林娇红自别,着半片御沟流叶。俨绛雪几枝斜,美人亭榭。忽裁成绡衣千叠。明霞,凝脂艳些,恰可是杜鹃枝叫。好多时云魂瘦撒,因何事汗透香颊?想甘心殉春,拼红雨,溅香雪,断不许痴蜂蝶作残红月上。痕拖缬,春工细剪春心裂。遍水边林下,锦沓香车。掩朱帘醉脸微侵,烧银烛新妆深射魂者,定是怜才呕心相。五红哥绛姐,便丛丛深色,别样豪奢。雨晴肥瘦靥,红白主宾递。嗔娇怨冶,似不怕东风。想人静黄昏后,月光斜,疑是玉人悄立绛纱。玉芳心难灭,任如堆浓艳,犹存淡洁。伤素心薄事铅华,逗红泪深思钻穴。只知淡不与浓不信东皇多转。水红眉儿压雪儿睫,换春牒。花神扭捏,丰姿元与冷相协。为情竭,嫣然脱卸。因甚当年,今日忽解?想于归绣裙揭。
双改妆聊自悦,吊影忽悲咽。十二重门深深设,是谁遣红线红绡来盗。衔杯细究花枝节,又添得诗人一绝,真不负红梨知己也。张轨如看完了,满心欢喜,不住口的称赞道:“兄真仙才,小弟敬服!”苏友白道:“适兴之词,何足挂齿!”张轨如拿着看了又看,念了又念。苏友白只道他细看其中滋味知他是要读熟了,因说道:“游戏之作,只管看他怎的?兄原许步韵,何不赐教?”张轨:“小弟凡做诗文,必要苦吟思索,方能得就,不似兄这般敏捷。容小弟夜间睡不着,请教罢。”遂将曲稿又看了一遍,就折一折笼在袖中,又将些闲话与苏友白讲。不多时,忽一个童子走将来说道:“老爷在梦草轩请张相公去说话。”张轨如道:“在这里,怎么好?”苏友白道:“既是东翁请兄,小弟别过罢。”遂要辞出。张轨如欲苏友白去了,又恐怕一时间有甚难题,便没有救兵,只得留苏友白道:“兄回去也无甚何不在此宽坐一会?小弟略去见见主人,就来奉陪。况此间甚是幽静,再无人来,兄尽览。”苏友白本要寻访消息,见张轨如留他,便止住道:“既这等说,兄请自便,小弟此闲耍。”张轨如说一声“得罪了”,遂同童子竟往梦草轩。到了轩子上,白公接着,说道:“又有几日不会先生,顿觉鄙吝复生。今见红梨盛开,先生来赏玩片时。”张轨如道:“晚生日日叨陪公子读书,并不知春色是这等烂漫了。先生垂爱,得睹芳菲,不胜厚幸。”白公道:“读书人也不要十分用工,太急伤损精神着花晨月夜,还要闲闲散散为妙。”随叫左右在红梨下排开一个攒盒儿,同张轨如看花饮了数杯,白公说道:“先生在馆中,读书之暇,一定多得佳句,幸赐教一二。”张轨:“晚生自到潭府,因爱花园清幽,贪读了几句死书,一应诗词,并不曾做得。”白公“今日花下,却不可虚度。”张轨如见白公说的话与传来消息相近,料定是这个题目;袖中有物,胆便大了,遂说道:“老先生倘不嫌俚俗,晚生即当献笑。”白公道:“先精于诗赋,这歌曲一定也是妙的了。前日因吴中一个敝年家送了两个歌童,音齿也还清只是这些旧曲,唱来未免厌听。先生既有高兴,就以此红梨为题,到请教一套时曲,叫唱出,得时聆珠玉,岂不有趣。不知先生以为何如?”张轨如听见,字字打到心窝,便答应道:“老先生台命,焉敢有违?但恐巴人下里,不堪入钟期之听。
白公大喜,随叫左右取过纸笔,铺在案上。又叫奉张相公一杯酒。张轨如吃干了,便昂提起笔来竟写。不期才写得前面三四个,后边的却忘记了,想了半晌,再想不起。只得手,起身走到个僻静花架背后,暗暗将袖中原稿拿出,又看了几遍,硬记在心。忙忙回上,写完了,递与白公看。白公细细看了,大加叹赏,道:“此曲用意深婉,吐辞香俊生自是翰苑之才,异日富贵,当在老夫之上。”张轨如道:“草茅下士,焉敢上比云霄之惶愧!”二人一问一答,在花下痛饮。且说红玉小姐自从得了两首和韵的《新柳诗》,因嫌他写得俚俗,遂将锦笺自家精精致原唱重写在一处,做一个锦囊盛了,便日夕吟讽不离,以为配得这等一个才子,可谓满愿。但闻此生有才无貌,未免是美中不足,因此时时心下有几分不快,每日没精没神,闷闷不乐。这一日午妆罢,忽思量道:“前日嫣素说得此生十分丑陋,我想他既有才如此,纵然丑必有一种清奇之处。今日嫣素幸得不在面前,莫若私自去偷看此生端的如何。若果非佳率性绝了一个念头,省得只管牵肠挂肚。”主意定了,遂悄悄的开了西角门,转到后园。忽听得百花亭上有人咳嗽,便潜身躲在一架花屏风后,定睛偷看。只见一个俊俏书生亭子上闲步,怎生模。书生之态,弱冠之年。神凝秋水,衣剪春。琼姿皎皎,玉影翩翩。春情吐面,诗思压。性耽色鬼,骨带文颠。问谁得似?青莲谪。红玉小姐看了,只认做张轨如,心下惊喜不定,道:“这般一个风流人物,如何嫣素说陋?”——那晓得是苏友白在书房中坐得无聊,故到亭子上闲。
小姐偷看了半晌,恐怕被人瞧见,便依旧悄悄的走了回来。只见嫣素迎着说道:“饭有小姐却独自一个那里去来?我四下里寻小姐,再寻不见。”小姐含怒不应。嫣素又道:姐为何着恼?”小姐骂道:“你这贱丫头!我何等待你,你却说谎哄我,几乎误我终身!素道:“小姐说得好笑!嫣素自幼服侍小姐,从不晓得说谎,几时曾哄小姐?”小姐道:不哄我,你且说张郎如何丑陋?”嫣素笑道:“原来小姐为此骂我。莫说是骂,小姐打死嫣素,也难昧心说出一个‘好’字来!”小姐又骂道:“你这贱丫头,还要嘴强!我看见来了。”嫣素道:“小姐看了来,却是如何?”小姐道:“我看此生,风流俊雅,无双。你为何这等毁谤他?”嫣素道:“又来作怪!小姐的眼睛平日最高,今日为何这样?莫要‘错认刘郎作阮郎’!”小姐道:“后园百花亭上,除了他,再有谁人到此?”嫣:“我决不信,那副嘴脸风流的!待我也去看看。”遂慌忙到花园里此时苏友白已走下亭子,到各处去看花。嫣素到了亭子上,不见有人,便东张西望。苏看见有个侍妾来,到躲入花丛中去偷看。只见那侍妾生。梨影拖肩柳折腰,绿罗裙子系红。虽然不比婵娟贵,亦有婀娜一种。
苏友白看了半晌,恐怕走出来惊了他进去,到让他走过亭子来,却悄悄的转到他身后,叫一声:“小娘子,寻那一个?这般探望。嫣素急回头一看,看见了苏友白是个年少书生,心下又惊又喜,道:“你是甚么人?为在此处?”苏友白道:“小生是和《新柳诗》不第的举子苏友白,流落在此,望小娘子。”嫣素道:“我看郎君,人物风流,不象个无才之人,为何到被遗了?”苏友白道:生荒疏之句,自不能邀小姐见赏。只是小姐何等高才明眼,所赏之人却又可笑。”嫣素君到不要轻薄!那张家郎君,人物虽万分不如郎君,然其诗思清新,其实可爱。小姐只不见人,所以取他。”苏友白笑道:“倘因人物取他犹可,若说因诗句取他,一发奇了嫣素道:“妾闻‘诗有别才’,或者各人喜好不同。”苏友白因叹一口气道:“我苏友生一点爱才慕色的痴念头,也不知历多少凄风苦雨,今日方才盼望着一个有才有色的小想小姐十年待字,何等怜才,偏偏遗落我多情多恨的苏友白!”又叹一口气道:“总是无福,说也徒然。嫣素看见苏友白说到伤情处,凄凄恻恻,将欲吊下泪来,甚觉动情。因安慰他道:“我君之言,愤懑不平,似怨小姐错看了郎君的诗句。我小姐这一片爱才心肠,可质鬼神;识才俊眼,犹如犀火。既郎君不服,何不把原诗写出,待妾送与小姐再看。倘遗珠重收不见得。”苏友白听了,慌忙深深一揖,说道:“若得小娘子如此用情,真死生不忘!素道:“郎君不要耽迟,快快写了来!妾要进去。”苏友白急急走到书房中,寻了一幅,写了二诗,叠成一个方胜儿。忙走出来,递与嫣素道:“烦小娘子传与小姐,求小姐细心一看,便不负我苏友白一段苦心。”嫣素道:“决不负郎君所托。”苏友白还要缠话,忽听见张轨如吃完了酒,一路叫将来道:“莲仙兄在那里?”嫣素听见,慌忙往亭躲了进。
苏友白转迎出来道:“小弟在此闲步。”张轨如道:“小弟失陪,多得罪了。”苏友白“当得。”张轨如道:“白太老还要留小弟谈讲,是小弟说兄在这里,他就要接兄同去;又见席残了,恐怕亵渎,才肯放小弟出来,又送了一个盒儿在此。我们略去坐坐。”把手挽了苏友白,到书馆中去吃酒。二人说说笑笑,直吃到日色衔山,才叫人送苏友白园去。且说嫣素袖了诗稿,忙走回来,笑对小姐说道:“我就说是小姐错看了。”小姐道:“错看?”嫣素道:“张相公若是这等一个人物,到好了。”小姐道:“既不是张郎,却人?”嫣素道:“他是张相公的朋友,姓苏。”小姐道:“他为何在此?”嫣素道:“他和《新柳诗》而来,只因不中小姐之意,故流落在此。”小姐听了,不觉柳眉低蹙,杏愁,忽长叹一声道:“似张郎这等有才,却又无貌;似此生有貌,却又无才。何妾缘之命之薄也!”嫣素道:“若论那生人品,便是不会做这几句诗,也配得小姐了。”小姐“我非不爱此生之貌,但可惜他这等一个人,为何不学?”嫣素道:“我也是这等说他到不说自家诗不好,转埋怨小姐看错他的。”小姐道:“我与老爷爱才如性命,虽一字,必拈出赏玩,安能错看?”嫣素道:“我初时也不信他。因见他行藏文雅,举止风骚话字字关心,象一个多情才子,故叫他将原诗写了来,与小姐再看。不要埋没了人。”袖中取出,递与小姐。小姐展开一看,大惊道:“为何与张郎的一字不差!”嫣素听说,也惊讶道:“这等一做不出,盗窃来的了!”小姐细想了一想,又将诗看了一遍,道:“这诗乃张郎盗窃此。”嫣素道:“小姐怎么看得出?”小姐道:“张郎因此一诗,已为入幕之宾,谁不晓得生既与他为友,必知其详,焉肯又抄写来,自贻其羞?况张郎写得字迹鄙俗可憎,此生匆潦草,却不衫不履,笔笔龙蛇。岂不是张郎盗窃?”嫣素道:“小姐这一想,十分有何不速与老爷说明,把张相公抢白一场,打发了去,早早嫁了此生,岂不是一对有才有好夫妻!”小姐道:“想便是这等想,如何便对老爷说得?”嫣素道:“怎么说不得?”道:“今日传此二诗,乃是私事。若对老爷说了,倘老爷问此二诗从何得来,却怎生答况此生之才,未知真假,若指实了他有才,老爷必要面试;倘面试时做不出来,我们明私,却不到有私了?老爷岂不疑心。
正说未了,忽一个侍妾拿了一幅稿儿递与小姐道:“老爷说,这是张相公方才在梦草轩做的,叫送与小姐看。”小姐接在手,打发那侍妾去了,就展开一看,却是一套咏红梨曲子。小姐细细看了一遍,称羡不已。心中暗想道:“我的《新柳诗》久传于外,还说盗窃。这曲子乃临时因景命题,难道也是盗窃?”便只管沉吟。嫣素见小姐沉吟,便说小姐不要没主意,辜负那生才貌。”小姐道:“我的心事,你岂不知?倘此生才不敌貌了他,不独辜负老爷数年择婿之心,就是我一腔才思也无处吐露。岂可轻易许可?”嫣:“据此生说来,百分才学,甚是讥笑张相公。难道一无所长,敢这等轻薄?”小姐道我也晓得必无此事。但终身大事,不敢苟且,除非面试一篇,方才放心。”嫣素道:“不难。我看此生多情之极,他既贪想小姐,必定还要来打探消息。待他来时,小姐出一题目,等我传与他,叫他立刻就做一篇,有才无才便晓得了。”小姐道:“如此甚好。做得隐密些,不要与人看见方妙。”嫣素道:“这个自然。”二人商量定了,方才欢欢。正只为怜才一念,化成百计千。分明访贤东阁,已成待月西。二人只因算出这条计来,便或早或晚,时时叫嫣素到后园来探望。争奈苏友白因是个侍家,不好只管常来。就来两遭,或是张轨如陪着,或是颖郎同着,嫣素只好张一张又躲,那里敢出头说话?所以往往不得相。
忽一日,白公在家,有人来报道:“杨御史老爷由光禄卿新升了浙江巡抚,今来上任。金陵,特特枉道来拜老爷。先打发承差来报知,杨老爷只在随后就到了。”白公笑道:中到此,有六七十里。此老特特而来,可谓改过修好矣。若是怠慢了他去,到是我的器了。”因分付家人,一面收拾书房留住,一面打点酒席款待;又叫了一班戏子俟候。因人陪他,欲要到村中请两个乡宦,又无大乡宦,又不相知,反恐不便;莫若只叫张郎来到是秀才家不妨。打点停当,到了午后杨巡抚方到。白公与他相见过,叙了寒温,就设大厅上做戏,留他饮酒,命张轨如相陪。却说苏友白打听得有这个空,便悄悄闪入后园来。后园管门的见苏友白时常往来,也不。况此时前厅忙乱,无一人到后园来,故苏友白放心大胆,走到亭子上来,四下观望。嫣素有心,正在那里窥探,刚刚撞着。苏友白喜不自胜,慌忙上前深深一揖,说道:“自前日蒙小娘子错爱之后,朝夕在此盼望,并无空隙能见小娘子之面,忘餐废寝,苦不。今日侥幸前厅有客,故得独候于此。多感小娘子见怜,亦如有约而至,诚万幸也。但前日荒疏之句,曾复蒙小姐一盼否?”嫣素道:“诗到见了。只是郎君二诗,与张郎二字不差,不无盗窃之弊。小姐见了,不胜骇异,正要请教郎君,此何意也?”苏友白惊:“原来如此!我说张轨如之诗如何入得小姐之眼!烦小娘子达知小姐,此二诗实小生所不意为张轨如所窃,非小生不肖。”嫣素道:“谁假谁真,何以辨别?”苏友白道:“辨也。此二诗若果张生所作,已为老爷、小姐所赏,小生复盗窃以献,乃真愚也。”嫣:“前日小姐亦作此想,又因面试张郎《红梨花曲》,乃一时新题新制,与前二诗若出,岂复是盗窃郎君之作耶?”苏友白笑道:“若说《红梨花曲》,一发是盗窃小生之作了嫣素惊讶道:“那有此事!《红梨花曲》乃老爷见梦草轩红梨花盛开,一时高兴,要张的。此种梨花别处甚少,郎君何以得知,便先做了与张郎盗窃?”苏友白道:“此曲原生宿构。就是遇小娘子的这一日,张轨如绝早着人请小生来,就引小生在此亭子上,望中红梨花,勒逼要做。小生因慕小姐,见物感怀,故信笔成此,谁知又为张郎作嫁衣裳殊可笑!殊可恨!小娘子若不肯信,况张郎不死,小生现在,明日当面折对,真假便见了嫣素道:“原来有许多委曲,老爷与小姐如何得知?不是这一番说明,几落奸人之局郎君勿忧,待我进去与小姐说知,断不有负郎君真才实貌也。”苏友白又深深一揖道:仗小娘子扶持,决当图报。
嫣素去了一会,忙忙出来说道:“小姐说,张郎踪迹固有可疑,郎君之言亦未可深信,勿论。但问郎君:既有真才,今有一题,欲烦郎君佳制,不识郎君敢面试否?”苏友白,笑容可掬,欢喜无尽,道:“我苏友白若蒙小姐垂怜面试,便三生有幸了。万望小娘成,速速赐题。”嫣素笑道:“郎君且莫深喜,小姐的题目,也不甚容易。”因于袖中出花笺一幅,并班管一枝,递与苏友白;随又取出小小古砚一方,并水壶、黑墨,放在石上,道:“小姐说,古才人有七步成诗者,郎君既自负,幸不吝一挥。”苏友白接笺,展开一看,不慌不忙,便欲下笔。只因这一诗,有分教:佳人心折,才子眉扬。正巧之胜拙,不过一。久而巧败,拙者笑。不知苏友白可能做诗,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