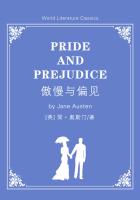诗
一段姻缘一段魔,岂能容易便谐。
好花究竟开时少,明月终须缺处。
色胆才情偏眷恋,妒心谗口最风。
缅思不独人生忌,天意如斯且奈。
话说张轨如因一时醉后高兴,便没心把白小姐的事情都对苏友白说了。后见苏友白再三,又见和诗清新,到第二日起来,思想转来,到有几分不快。因走到亭子里来,与王文议。只见王文卿蓬着头,背剪着手,在亭中走来走去,象有心。。张轨如见了道:“老王,你想甚么?”王文卿也不答应。张轨如走到面前,王文卿恼道:“我两个聪明人,为何做出这糊涂事来!”张轨如道:“却是为何?”王文卿道:“那个姓苏的,又非亲又非故,不过一时乍会,为何把真心话都对他说了?况他年又少,又生得俊秀,诗又做得好,若同他去,却不是我们转替他做垫头了?”张轨如道:“小在这里懊悔,来与你相议。如今却怎生区处?”王文卿道:“说已说出了,没甚计较挽”张轨如道:“昨夜我也醉了,不知他的诗毕竟与小弟的何如,可拿来再细看一看。”卿遂在书架上取下来,二人同看,真个愈看愈有滋味。二人看了一回,面面相张轨如道:“这诗反复看来,到转象是比我的好些。我与你莫若窃了他的,一家一首,风光一风光,燥皮一燥皮,有何不可!小苏来寻时,只叫小厮回他不在便了。”王文卿“小弟昨夜要他做第二首,便已有心了。今仔细思量,还有几分不妥。”张轨如道:“不妥?”王文卿道:“我看那苏莲仙,年纪小小,也象个色中饿鬼。你我不同他去,他得踪迹,难道就肯罢了?毕竟要寻访将去。他若自去,这两首诗岂不弄重了?一对出来,便有许多不妙。”张轨如道:“兄所虑亦是。却又有一计在此:何不去央央董老官,但莲仙来,便叫他一力辞去,不容相见,不与他传诗。难道怕他飞了进去不成?”王文卿“此计虽妙,但只诗不传进去,里边不回绝他,苏莲仙终不心死。到不如转邀他去,明做罢。”张轨如道:“怎生明做?”王文卿道:“只消将这两首诗留起一首与我,将一了你的名字;却把昨日兄做的,转写了苏莲仙名字,先暗暗送与董老官,与他约通了,只回‘白老爷不在家’,一概收诗。然后约了苏莲仙,当面各自写了,同送去。董老官‘不在’,自然收下,却暗暗换了送进去。等里面与他一个扫兴,他别处人,自然没趣。那时却等小弟写了那一首送去,却不是与兄平分天下了。
张轨如听了,满心欢喜道:“好算计!好算计!毕竟兄有主意。只是要速速为之!老董那那个去好?”王文卿道:“这个机密事,如何叫得别人?须是小弟自去。只是董老官是个,须要破些钞方才得妥。”张轨如道:“谋大事,如何惜得小费!称二两头与他,许他再谢。”王文卿道:“二两也不少了。只是那老奴才眼睛大,看不在心上。事到如今也得了,率性与他三两,做个妥贴,或者后边还用得他着。”张轨如无法,只得忍着痛称两银子,用封筒封了。就将苏友白的头一首诗,用上好花笺细细写了,却落自家名字;自家的诗,叫王文卿写了,作苏友白的,——却不晓得苏友白的名字,只写个“苏莲仙。写完了,王文卿并银子同放在袖中,遂往锦石村来。正损人偏有千般巧,利己仍多百样。谁识老天张主定,千奸百巧总徒。原来这董老官却是白侍郎家一个老家人,名字叫做董荣,号叫做董小泉。为人喜的是银爱的是酒杯。但见了银子,连性命也不顾;倘若拿着酒杯,便头也割得下来。凡有事寻只消买一壶酒,一个纸包,便连府中匙大碗小的事情都说出来。就是这《新柳诗》,也抄与王文卿。
这日王文卿来寻他,恰好遇着他在府门前背着身子数铜钱,叫小的去买酒。王文卿走到将扇儿在他肩头上轻轻的敲了两下,道:“小老好兴头!”董老官忙回身来,看见是王,便笑道:“原来是王相公。王相公来下顾,自然就有兴头了。”王文卿道:“要兴头要在小老身上。”董老官见口声是生意上门,便打发了小的,随同王文卿走到转湾巷里小庵来借坐。因问道:“王相公此来,不知有何见谕?”王文卿道:“就是前日的《新成了,要劳你用情一二。”董老官道:“这不打紧。既是诗和成了,若要面见老爷,只坐一坐。老爷今日就要出门,只待临出门时,我与你通报一声,便好过去相见。”王文“到不消见得老爷,只劳小老传递一传递就好了。”董老官道:“这个一发容易!”王道:“果然容易。只是略略有些委曲,要小老周旋。”董老官道:“有甚委曲?只要在的来,再无不周旋的。王文卿遂在袖子里摸出那两幅花笺来,说道:“这便是和韵的两首诗。一首是敝相知张一首是个苏朋友的,小老可收在袖里。过一会,待他二人亲来送诗,烦小老回一声‘老门了”,一概收诗;待他拿出诗来,再烦小老将他送来的诗藏下,却将这二诗传进,与、小姐看,便是小老用情了。”董老官笑道:“这等说起来,想是个掉绵包的意思了!王相公来分付,怎好推辞作难,只凭王相公罢了。王文卿来时,在路上已将三两数内称去一两,随将二两头拿出来,递与董老官道:“这敝友的一个小东,你可收下。所说之事,只要小老做得干净、巧妙,倘或有几分侥幸,一大块在后面哩。”董老官接着包儿,便立起身来说道:“既承贵友盛情,我便同王相前面一个新开的酒楼上去,领了他的何如?”王文卿道:“本该相陪,只是张敝友在家,还要同来,工夫耽阁不得了。容改日待小弟再来请罢。”董老官道:“既是今日就要连我也不敢吃酒了。莫要饮酒误他的事情。”王文卿道:“如此更感雅爱!”遂别了董,忙忙来回复张轨。
此时张轨如已等得不耐烦,看见王文卿来了,便迎着园门问道:“曾见那人么?”王文:“刚刚凑巧,一到就撞见。已与他说通了。怎么小苏这时候还不见来?”正说不了,苏友白带着小喜走将。原来苏友白只因昨夜思量过度,再睡不着,到天亮转沉沉睡去,所以起来迟了。梳洗毕了饭,随即到张家园来,恰好相遇。三人相见过,张轨如道:“莲仙兄为何此时才来?友白道:“因昨夜承二兄厚爱,多饮了几杯,因此来迟,得罪!”王文卿笑道:“想是见白小姐了!”苏友白笑道:“若是二兄不要见,小弟也就不要见了。”张轨如道:“去,也是时候了,不要说闲话误了正事。”王文卿道:“小弟诗未和,已是无分,只要快快写了诗同去。倘那一个讨得好消息回来,好打点酒肴贺喜。”遂同到亭子上。张轨苏友白各写了昨夜的诗句,笼在袖内。张轨如又换了一件时新的色衣,叫小厮备了三匹一同出园门,竟望锦石村来。正游蜂绕树非无意,蝼蚁拖花亦有。攘攘纷纷眷春色,不知春色许谁。
原来白石村到锦石村,止隔有三四里路,不多时便到了村里。将到白侍郎府门前,三人了马,步行过来。此时董老官已有心,正坐在门楼下等。忽见三人走到面前,便立起身佯问道:“三位相公何来?”王文卿便走上前,指着张、苏二人说道:“这两位相公,姓张,一位姓苏,特来求见老爷。”董老官道:“二位相公早来一刻便好,方才出门赴了。有甚话说,分付下罢。”张轨如道:“也无甚话说。因闻得老爷要和《新柳诗》,人各和了一首,特来请教。”董老官道:“二位相公既是送诗,只消留下,待老爷回来,再请相会。”张轨如回头与苏友白商议道:“是留下诗,还是等一等面见?”苏友白“面见固好,但不知可就得回?”董老官道:“今日吃酒,只怕回来迟,见不成了。”卿道:“留下诗也是一样,何必面见?”二人遂各自将诗稿递与董老官道:“老爷回来烦禀一声。”董老官道:“这个自然,不消分付。但是二位相公寓所要说明白了,恐怕诗,要来相会。”王文卿道:“这位张相公是丹阳城中人,读书的花园就在前边白石村这位苏相公也就在白石村观音寺里作寓。”董老官道:“既在白石村,不多远,晓得了位相公请回罢。”三人又叮嘱了一回,方才离了白侍郎府前,依旧上马回白石村去,不正弄奸小辈欺朋友,贪利庸奴误主。不是老天张主定,被他窃去好姻。却说董老官见三人去了,随即走到门房里,将才来的二诗藏在一本旧门簿里,却将早间卿的二诗拿在手中,竟送进来与白公原来白公自从告病回家,一个乡村中,无处择婿,偶因红玉小姐题得一首《新柳诗》,一个和诗之门,以为择婿之端。又一远族送了一个侄儿,要他收留作子。这侄儿才一十,名唤继祖,小名叫做颖郎,生得顽劣异常,好的是嬉游玩耍,若提起读书,便头脑皆终日害病。白公撇不过族中情面,只得留下。其实虽有如无,不在白公心下。正生男只喜贪梨栗,养女偏能读父。莫笑阴阳颠倒用,个中天意有乘。这日白公正在梦草轩看花闲坐,忽见董荣送进两首和韵《新柳诗》来,随即展开一首来看了一遍,不觉大笑起来道:“天下有这等狂妄的人!这样胡说,也送了来看!”再看名却写着“苏莲仙题”,便放开一边,又将这一首展开来看。才看得头一联,便惊讶道:诗清新可爱!”再看后联、结句,便拍案道:“此异才也!吾目中不见久矣!却从何处得来忙看名字,却写着“丹阳张五车题”。白公更惊讶道:“丹阳近县,为何还埋没着这等?”随叫侍婢去请小姐。
小姐闻父命,慌忙到轩中来。白公一见小姐,便笑说道:“我儿,今日我替你选一个佳!”小姐道:“却是何人?爹爹从何处得来?”白公道:“方才有两个秀才送和的《新柳来,一个甚是胡说,这一个却是风流才子。”随将“张五车”的递与小姐看。小姐接在看了两遍,道:“这首诗果然和得有致,自是一个出色才人。但不爹曾见其人。”白公道:“我虽不曾见他,然看此诗,自不是个俗子了。”小姐又将此诗看了一遍道孩儿细观此诗,其人当是李太白一流人物,但写得浊秽鄙俗,若出两手,只恐有抄袭之爹爹还须要细加详察。”白公道:“我儿所论亦是。只消明日请他来面试一首,便真伪了。”小姐道:“如此甚好。”白公随又叫董荣进来,分付道:“明日清晨,可拿我一个侍生的帖子,去请今日送诗的位张相公来,说我要会他一会。”董荣道:“那一个苏相公可要请么?”白公笑将起来“这样胡说的人,还要请他?这等多讲!”董荣慌忙去了。白公又将“苏莲仙”这首诗递姐道:“我儿,你看好笑么?”小姐看了,亦笑起来。父女二人看诗赏笑,不且说苏友白自送了诗回去,张轨如又留在园中吃了半日酒,只到傍晚方才回到寺中。静:“苏相公那里饮宴回来?”苏友白道:“学生今早即急急要回去,只因昨晚看月,遇面园中张相公、王相公,留下同做和白小姐的《新柳诗》。今日同送去看,不觉又耽阁日。”静心道:“苏相公这等年少风流,却又高才,白小姐得配了相公,也不负白老爷一场。”苏友白道:“事体不知如何,只是在老师处搅扰,殊觉不安。”静心道:“苏说那里话?就住一年也不妨!只是寒薄,简亵有罪!”苏友白道:“承老师厚情,感谢不后来倘得寸进,自当图报。”静心道:“苏相公明日与白老爷结成亲,便是一家了,何话?且去吃夜饭。”苏友白道:“饭是不吃了,只求一杯茶,就要睡了。”静心又叫人,与苏友白吃了,方别了去。
到次日,苏友白起来,满心上想着《新柳诗》的消息。梳洗完,正要到张轨如园里来访忽见静心领着张轨如与王文卿走进来,道:“苏相公在这一间房里。”苏友白听见,慌来相见。张轨如便笑说道:“苏兄今日满面喜气,一定是《新柳诗》看中了意!”苏友:“小弟如何有此等福分,自然还是张兄。”王文卿笑道:“二兄口里虽然太谦,不知如何指望哩。”二人都笑将起。正说笑间,只见张家一个家人跑将来说道:“锦石村白老爷差人在园里,要请相公去说”张轨如听了,就象金殿传胪报他中状元一般,满心欢喜。因问道:“莫非是请苏相公这狗才错听了?”家人道:“不曾说请苏相公。”苏友白听见,转惊呆了半晌,心下暗:“为何转请他?有这等奇事!”又不好说出,只得勉强说道:“自然是请张兄,若请小一定到寺里来了。”王文卿道:“二兄不必猜疑,只消同到园中,一见便知。”三人遂同到园里来。只见董老官已坐在亭子。三人进来相见过,董老官便对着张轨如说道:“昨日承相公之命,老爷吃酒回来,小的诗笺送上。老爷接了进去,在梦草轩与小姐再三评赏,说张相公高才,天下少有。今日过去会一会。”就在袖中取出一个名帖来,递与张轨如。张轨如接了一看,只见上写着侍生白玄顿首拜”八个大字。张轨如看了是真,喜得眉欢眼笑,即忙叫家人去备王文卿假意问道:“昨日这位苏相公的诗,不知老爷曾看么?”董老官道:“送进去便,怎么不看?”王文卿道:“老爷看了怎么说?”董老官道:“老爷看了,想是欢喜得紧觉大笑起来。”王文卿道:“既是这等欢喜,为何不请苏相公一会?”董老官道:“在曾问过可请苏相公,到被老爷骂了几句,不知为甚。或者另一日又请,也不见得张轨如连连催饭,董老官道:“饭到不敢领了。老爷性急,恐怕候久。张相公速速同去。”张轨如道:“是便是这等说。只是小老初次来,再没个白去的道理。”董老官道:“公恭喜,在下少不得时常要来取扰,岂在今一日!”王文卿道:“董小老也说得是。张到老实些折饭罢。”张轨如忙忙进去封了一两头,送与董老官道:“因时候不待,只得了。”董老官又假推辞,方才收。
苏友白便要起身出来,张轨如留下道:“苏兄不要去!小弟不过一见便回,料无耽阁。先生或者要小弟与兄作伐,亦未可知。不要这等性急。”王文卿道:“说得有理。待小着苏兄在此玩耍。兄速去便来。”苏友白也就住。张轨如又换了一件上色的新衣,又备了许多礼物,以为贽见之资,又付嘱备了两匹马,一匹,却将一匹与董老官骑了。别过二人,扬扬得意,竟望锦石村来。张轨如这一番到村来,不知比昨晚添了许多的兴头!正世间多少沐猴冠,久假欣欣不赧。只恐当场有明眼,一朝窥破好羞。不知张轨如来见白侍郎,毕竟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