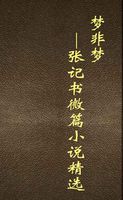井老师讲分数四则混合运算。四喜的脑子里也混合起来了。太阳为什么在那边,一点儿也看不清黑板,先通分先乘除先小括号,先小括号先乘除先通分……分不清,看不清。大师傅老金记住我的饭罐没有?那是干麦仁饭,不能煨大火,热灰儿热着就中。三斤九两鳝鱼,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减去一斤四两拐篓,三斤九两……一斤四两……
井老师说,退括号时,应该注意:一……二……三……
四喜做了第一个小动作,他攥了个小拳头砸起额头。他警告自己集中精力听课。
井老师刷刷刷,粉笔灰一片雾,板书毕,布置了五道课堂练习题。井老师说“四喜你过来”,四喜就“过来”。井老师没停下,四喜也没停下。
筷子桥小学没有围墙,学校四周,竹子长得像围墙。井老师钻进竹丛,头上的斑鸠、八哥、画眉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它们一点也不怕人,一只比一只唱得水灵灵的。
井老师靠着一棵竹子,四喜觉得老师真好看。腰细细的,腿长长的,脸白白的,鼻梁高高的。四喜一直在村上吹,说他们班今年来了个姑娘伢老师就跟瞎子说书讲的一样儿:才貌双全。四喜想不清楚,井老师靠上竹子,为什么更加“才貌双全”?
井老师:“为什么迟到?”
四喜:“蓝带子河那地方,北岸一条黄鳝都没有,我就白丢了时间,南岸黄鳝又好得很,我就又花多了时间。”
井老师:“我批评过你没有?批评过几回?是怎么批评你的?”
“批评过了。三回。老师说,学生就是学生,鱼老鸹就是鱼老鸹。要当好学生,就别那么馋鱼儿。要当鱼老鸹,就别飞往学校念书。”
井老师看看孩子的大脑壳,真想赞扬他的学生记性好,背得一字不差。井老师看过孩子脑袋,就数起孩子身上的鱼血点子,就瞪着孩子脚背上泥巴都没洗尽,便匆忙胡乱穿起的鞋。
“你哪像个学生。”
四喜没做声,默认着。老师又没讲错,每天早晨上学,他都是书包带子拴着拐篓绳子,捎马儿一样前胸后背搭拉着。手上还拎着个四耳罐罐,别说城里分来的井老师,就是别处乡下人瞧上了,也不晓得这一带娃儿们如此作何营生。
第一回,是启发。那次井老师说,四喜,你聪明,基础好。那也不能三心二意。好比一棵树,一干儿往上长,就是栋梁材。分杈了,就尽是烧火用的树枝了。第二回,是劝诱。四喜,你只要不迟到不贪玩,就不会是第三名,就一定是第一名。第一名就能考上重点中学,日后就能考上大学。国家需要你的才能,你也需要国家待遇,这多好。
这一回,井老师不了,这一回,井老师说:“我要处分你。我要报告校长教导主任,你不是影响自己一个人,你破坏了我们班。我想最好是开除。最好是我当不成你的班主任,你也当不成我的学生……”
四喜突然警惕地竖起眼珠。这是个阴谋。
井老师和我爹一起喝过酒——我爹请了她的客?她晓得不晓得,她下酒的鳝鱼丝儿,是我一条一条从冰冷冰冷泥水里抠出来的?
爹一次一次说过:“念什么书?念书是城里人的事。我们庄上,有哪个伢念书念成了干部?念书象念咒,越念越穷光蛋。四喜给我摸螺蛳养鸭,一年还挣不下千儿八百?明儿起,不念了。”
“明儿起不念了”像两挂耳坠子,时时刻刻叮叮当当耳门边响着。四喜要么是惨惨地哭,要么是硬硬地犟。好几次,脚打跛了,还是硬性地拐进学校还是偷着溜进学校。晚娘起先是出点子,要爹断他的书,晚娘这时候又伤心了:“那就……让四喜念吧。”爹说:“这哪还像老子的种?好吧,念!念!每天给老子交两块钱,他就念!”
……四喜:“井老师,你上过我家了?你跟我爹……谈过?”
“这不需要上你家。这是我们学校的事。”
四喜觉得阳光从竹叶间漏了下来,明亮多了暖和多了。四喜还觉得,脑门上那几颗细碎冰凉的汗珠,失去了光泽、敏锐、坚硬。脖后根和脊沟里,终于涌出了热的蒸腾。
孩子很有经验很老练地想,学校不要紧,学校我有后台。孩子放松地望着远处,一朵白云和一只白鹤,并排儿悠着翅膀。田野里,稻草人可爱地挥着扇子。牛们的大草滩,牛角上拴的纸鸢子,时低时昂。
饭罐子果然叫老金煨炸掉了,麦仁饭,两块咸鱼,几筷头苋菜儿,全成了柴禾。“老金,你是怎么搞的吗?”四喜像校长、老师一样,他喊他“老金”。烦了,就叫熊老金。
老金果然晦气:“中午带饭的人越来越多,灶膛里,加热的饭罐子快摆满了,顾了这个顾不上那个,不信你自己看看。”
他不看。不怜悯这如同孩子般的老头儿。“我不看,你赔我。我中午不能回去,七里,来回十四里,还一个山头两条河。我的饭带来了,回去,家里也没我的中午饭。”
老金认为孩子说得在理,实事求是。老金说:“我赔。”四喜就一旁瞄着老师们都吃过了,溜进大师傅房里,和老金一起吃。
老金:“黄鳝称了,整秤二斤。”
四喜不客气地顿了顿饭碗:“我也在路边店称了一下,连篓子三斤九两。”
“没那么多,连篓子是三斤四两。”
“那不中,半斤,你贪了我一块五,加上三角钱‘服务费’,一支两用笔呢。”
老金每天总要和这个孩子讨价还价,每次总能占去一两二两。老金想,一二两鳝鱼,平均五角钱,外加三角服务费,不到一块,能算多少?老金也想,孩子也可怜,他是急急忙忙、不顾水深水浅水冷水寒地抓,抓了还要一溜烟往学校里跑。孩子就总是抓得不多,差不离就一斤左右。他赚了七角八角,总得剩个两元让孩子交给父亲。
老金没想到四喜今天捉了二斤五两鳝鱼。老金决定增加“提成”。
现在老金有点汗冒冒的:“路边店使小秤,总有一天遭罚。”好像他自己已经遭罚,心里又鬼又虚,“你以前在路边称过没有?”
孩子貌似直率,其实,他是没想那么多:“我又没同你算老账。我是说二斤五两鳝鱼,你交给我七块五,不应该六块。”
老金说,扯不清了,扯不清了,以后我也不给你帮忙了。孩子果然焦急甚至有些恐慌。老金说,好人做不得。孩子说,我有个“活儿”,你要是肯帮忙,做好人,今儿的事结了,日后咱俩生意嘛,还继续做。
老金听了不惊不乍,他从来就把这个古怪的孩子当作大人。
四喜就要老金到校长那里“帮忙”。“小事,就是逮黄鳝迟到了,井老师不够意思,她要开除我。”
老金一脸为难,心里却很快活。他晓得这是老师吓唬学生整治学生。这点事哪能开除?当然,真开除,老金也真帮忙。一次一次捉鳝鱼,一次一次迟到,一次一次也多多少少好像和他老金有点关系。怕卵,校长和他不也是“关系”吗?他暗中给校长做的“垫碗菜”,差不多是三百六十五天秘密,要不,校长不增加一文生活投资,就能长得那么油光水抹?
老金倒霉相十足:“那我就到校长那里碰碰钉子吧。”
四喜说:“老金,你别来这一套。你跟我吹过,你说校长家有妹子,你也能娶到手。”
老金想起来了,有天好酒喝光了,醉话变成胡涂话,开心开到了校长头上。
老金脑子灵,遇上什么赚点什么:“你把我这句话包庇了,我就劝校长不开除你。”他要叫孩子明白,他不是怕买卖黄鳝有干系,他是怕一句糊涂话惹麻烦,才仗义帮忙的。
孩子愉快极了。他管那么多屁事干什么?他想,我又能念书了!
过了暑假,又过了中秋。四喜左肩背书包,右肩背的不是拐篓了。这季节,黄鳝渐渐难抓了。抓那么一两条,拐篓还是空空荡荡。学校后头那家餐馆老板就催老金,老金就催四喜。“催个屁!回到家里爹催,上了学校你催,我不干了。”
四喜不干,老金觉得损失大大的,他当大师傅,一个月才五十个元,四喜每月给他捞二十几元外快,真不是小事。
老金说:“不干了,你还怎么念书?”
小男子汉四喜,一下子哭了。
隔了一天,四喜背着个特大书包,跑得一头大汗,脸色煞白,气喘得像老金锅里烧的开水泡儿。他拖来一只盆子,打开书包就倒。一会儿,倒出了半盆蘑菇。
老金看着这么新鲜的雁蓝菌子和松花菌子,知道都是好价钱的俏货。
四喜:“老金,我没吃早饭,提前儿上学,绕道儿爬山坡,捡了这包蘑菇。你看看我的腿,饿得晃晃颤。你要是来个瞎价,我放学就去调查。”
老金总觉得这孩子日后要当大官,你看,别的娃儿讲不到什么“调查”,他讲到了。老金说:“你就放心。快,我这里还有半碗饭,你吞了吧。”
“你有一碗人参汤我也来不及吃了。你想让井老师把我搁在门外?”
四喜就和井老师差不多一起钻进教室。井老师瞪了瞪他,不凶,四喜就觉得井老师香喷喷的了。
这堂数学,讲的都是复习题。四喜每天晚上要把书上的各类复习题,做过的再做做,没做的多做做。爹说:“草稿本练习薄用得太费了。”那个星期天他就爬树捉那只绿头鸟儿。上学路边上有个庄子里回来一位退休老工人,那老头可爱养鸟了,都晓得他买鸟舍得花钱。四喜估计,抓上这只希罕鸟,一张票子(拾元)没说的。结果出了事,下树时滑了脚,鸟没摔死,他差点儿摔死,屁股蛋开了花,他拐到个僻处,脱掉裤子一把儿一把儿抹血沫子,胡揪瞎抠掉扎进肉里的树茬尖儿和碎沙粒儿。他果然得了拾元钱,可惜只能拿出一半买练习薄,剩下五元,变成中药店大大小小膏药。
……井老师还在情绪饱满神采飞扬讲复习题。不过每一题都不难。他盯着井老师,思想集中地开小差。大概六七年后,我就能是井老师那样儿。给许多人讲让许多人听,讲得手势一扬一扬好看得很。井老师又有学问又漂亮,井老师是女的,我要胜过她,我还要比她多念个大学……孩子忘记了父亲忘记了老金忘记了饿和“腿肚子晃晃颤”,孩子望着井老师睡着了。
井老师很仔细地看了看四喜,同学们都一片紧张。井老师可能晓得孩子还在美丽地梦她,井老师就没叫他责备他。
下课了,井老师说:“四喜,你来一下。”
四喜站在备课桌边,很痛苦:“老师,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上课不打瞌睡。”
井老师摸了摸孩子的头:“四喜,你诚实吗。”
这叫孩子很茫然,他也就顺着意思——茫然点了头。
“那你告诉我,老金总共赚了你多少钱?”
“这……”
“老金很坏。我们每月伙食费都让他克扣了。我们都应该向他斗争。”
四喜很少见到过“斗争”,他只在书上念过“斗争”。他晓得,老师的伙食让老金做了校长的“碗底菜”了,那碗底总有蛋呀肉呀鱼呀什么的,总共才八九个老师,一日三餐这么干,算是不小的“摊派”。四喜想,井老师,我比你早就晓得老金很坏。
但四喜想,把老金斗争走了,我的黄鳝我的蘑菇托谁卖呢?我的学费我每天交两块钱哪来呢?老金走了,我也就真的“开除”了……
四喜说,老金没要我的钱。
井老师就流出了眼泪。
后来井老师不那么严峻了,后来井老师平和多了。后来井老师说,我实习时,下到外婆那里。我外婆也在乡下。我外婆那里好多好多孩子,也是背鱼篓、挎猪草篮子上学……
后来井老师说:“四喜,好好念……噢,要好好念……噢……”话音拖泥带水,完全没有课堂上干净、清脆。脸色也不神采飞扬,额头失去了光泽,眼睛雾雾的丢了晶莹明亮。
四喜就听得心里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