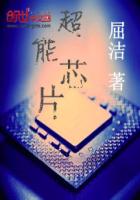每人借了三元钱,头一件要买的东西就是肥皂;
从湖南醴陵来的红卫兵,走到了井冈山,还要走去红色故都瑞金。一路上没少淋绵绵秋雨,他们想来借几件雨衣,没有雨衣,能借上一块尼龙布也成……
自红卫兵开始来井冈山大串连后,江西省商业部门便绕过吉安地区,直接向井冈山投货。无论是一般商品,还是紧俏商品,只要省里有,就一定给,而且是无偿的。为了这场已经闹腾了近半年、而且还不知道要闹腾多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井冈山竭尽自己的人力,而江西省则竭尽自己的有限财力……
似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有过初期的亢奋。紧接着,井冈山人的脸上,亢奋渐渐剥落了,而代之以急切,代之以困惑,代之以憔悴!
宣传组的头头跑了,秘书组的头头跑了,保卫组的头头跑了,或是揭竿造反,或是也干脆出去串连,出去周游“列国”……
不能跑的,是管理局的几个负责人。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度过红卫兵大串连那段日子的——山上的造反派来找,串连的红卫兵也来找;不接待是“对抗革命”,接待多了是“破坏生产”;批斗会得准时参加,散了会摘下高帽还得工作!
不开会各个环节协调不了,一开会则说是“走资派在策划阴谋”……因此,他们常碰头的地点是气象台、医院手术室。如同爬上了蜘蛛网的虫子,他们明知越走缠得越紧,可只有走下去。他们设想过,如果自己丢下井冈山跑掉,如果接待系统一旦全部瘫痪,那么在偌大一个中国,他们将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像一颗内部已经发生金属疲劳、却仍忠贞地铆在机器上的铆钉,生活组副组长徐勉同志也没有跑。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如果生活组的摊子也散了,虽说棚子搭起来了,粮食也有十几天的储备,一时还冻不着、饿不着红卫兵,可山上十几万人拉下的大便,有一天不及时组织拉下去,就足以臭倒井冈山!
1966年11月的井冈山,被方兴未艾的红卫兵大串连给摇撼了……
八
此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方兴未艾。
仅用革命导师的号召和发动,一代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和现代迷信,来解释这一运动,是浅薄的、不完全的。
无疑,没有毛泽东主席,就不会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任何历史的活动,都不是个人的活动。这正如同中国有一块广博的土地,不仅仅只是为数几个人的舞台。如果说,某种激进思想,一开始只存在于紫禁城那间堆满古色古香线装书的书房,那为什么它能如此迅猛地辐射到远离紫禁城、并对最高层政治舞台上愈来愈激烈的权力较量一无所知的亿万青少年中去呢?
现代迷信的本质是专制。专制的基础是农民平均主义,是“传统的村社精神”。
而“文化大革命”不但发动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幕幕波澜云诡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响应,也越是强烈。这不禁令人回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这些“无主的自由人”,并不是穷苦人,而多半是商人和绅士阶级……
要理解红卫兵运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诸种矛盾激化的产物。
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有如车水马龙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决非是“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五”,同时也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几乎从一生下地就蒙受歧视的孩子。他们从懂事起、就隐隐约约觉得社会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省自身,以证明自己“脱胎换骨”。
他们内心鄙视某些干部子弟,却不得不整日凑起谦卑的笑容,以证明自己“靠拢组织”。
从《中国青年报》上的通栏标题——“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对待一切,分析一切”,到毛主席写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们总感到风声鹤唳。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他们总有芒刺在背。
压抑感与不安全感,将他们的灵魂绞成麻花,把他们的言行捆成粽子……
无数严峻的事实在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铁打的,铜铸的,而“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不过是沙上的塔,纸糊的墙。因此,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了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周总理也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了的双重人格,一边得像狼崽一样撕咬出父母心头的血泪;一边又得像羊羔一样依靠着长辈的养活……
在共和国的宪法上,他们和其他公民一样,都是站着的人,但在现实社会里,他们却是跪着的人。
在形形色色“百分之五”的子弟与革干、革军子弟之间的,是大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子弟。知识分子。职员子弟就不必说了,就是工人、农民子弟,除了不多的出身于纯血统的无产者以外,也有着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或是父亲是下中农,祖父却是地主;或是叔叔是共产党员,大伯却逃去了台湾……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运动,同样在他们心灵里投下或重或轻的阴影。
他们是经不住摔的豆腐干,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们总还是块看上去洁白的豆腐。他们不用低着头走路,夹紧尾巴做人,有了远比前一部分人多得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需求与现实,常常发生矛盾——
简陋、拥塞的斗室。干了一辈子建筑工的父亲,干到背驼腰弯了,还得不到两间新房……
粗糙、乏味的饭食。为别人端了几十年碟子的母亲,临到退休了,还未带过孩子们去下过一趟馆子……
从大哥鬓角早生的银丝里,看到了那间坐着一个沉重躯体和同样沉重的档案柜的办公室,诚实、热情与才智,要走出这间办公室,犹如一条鱼要游过一堵墙……
从大姐跑回娘家的失声痛哭里,听到了那个铺着地毯,摆有景泰蓝花瓶的客厅里一声声泼水般的呵责,犹如荣宁二府里,皇亲国戚们在使唤丫鬟……
不是人家有的,大家都有。不是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的,都有结果。有时,种豆的,不收豆,未栽花的,却有花。
不是共和国宪法上写明了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真正享有主人的权利。常常主人的头上还有一批颐指气使的“公仆”。
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起,对当时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少数人的“特权”深恶痛绝!
他们在理论上对“人”字也许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集体无意识层次,他们却要求做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中国的国粹之一,就是无论历史上演悲剧,还是演喜剧,都能找到某种优越感,甚至连阿Q也有优越感。尽管这后一部分人与前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有某种相联系的东西,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与前一部分人保持了一定距离。
红卫兵的诞生,打破了这一距离。红卫兵习惯性地沿用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划分政治标签,“黑五类”,“黑七类”,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划出了“黑九类”,并将这种做法,推到极端荒谬的境地,而且还有了血腥气,这无异在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红卫兵们也将自身推至一个“红司令”难以容忍的境地。毛泽东主席是为了击败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自下而上地发动这场“革命”的,可是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不断涨潮的政治热情,在“破四旧”里、横扫“牛鬼蛇神”中酣畅地挥洒到顶点之后,很快就像沙漠里的水一样消失了……他们曾相信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曾有亡党亡国可能性大大逼近的严峻感。但是一旦超出了“百分之五”,而且“资产阶级司令部”竟像一个无边的魔袋,能把他们的父辈都给装进去,于是无论就感情,还是就理智,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的父辈;无论是因为习惯性的政治敏感,还是因为眼前家庭沉重的氛围,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去注意林彪、江青等一批政治新贵身上被时髦理论遮住的究竟是一块怎样的纹章……他们大多成了“保爹、保妈”派,加上全国相当一部分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人们,有着既得利益的人们所组成的“保守派”,使本来轰隆隆开始转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车轮,突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于是,毛泽东主席打了一张牌。
他愤怒地斥责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去了工作组,号召为被这条路线迫害的群众平反。在《十六条》中,他明确主持制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必须享有的权利——毛泽东主席既熟读诸子百家,在青年时代也受过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当他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几次极度孤立时,民主总是他最喜爱的武器……
似乎改变了历次运动的做法——它不整人,却整那些想整人的人。
它像阴冷的、灰沉沉的雨季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霞光般新鲜,令人温暖,令人鼓舞……
这是一张民意牌。毛泽东主席利用它来“炮打司令部”;而亿万群众则利用“炮打司令部”来发泄对当时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懑,来争取自己真正回归做人的权利。
至此,亿万群众才真正充分发动了起来。
一般来说,越是知识层次高的人,越是具有人文主义倾向,或者称作是“右”的倾向。于是,知识分子们成了其中最活跃的一群。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莱奇(Morc Blecher)和戈登。怀特(Gordon White)在研究了某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后发现:该单位中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的人加入了保守派组织,而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
由此,也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的纷纭、复杂——“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条极“左”路线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们,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阶段里,反倒成为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支持者。历史就这样向人们开着残酷的玩笑!
在准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中,如果说运动初期上面提及的前一部分人,因为脸上的红字更加夹紧了尾巴,犹如惊弓之鸟;后一部分人的大多数也因为饱经政治运动的父母们的提醒,对文化大革命持观望态度,担心这将是又一次“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那么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作组一夜之间撤走了,红卫兵们挥舞的“血统论”的大棒不灵了,学生们自组各种兵团、战斗队的自由已成既成事实,甚至一个人也能拉起个“战恶风”、或是“炮声隆”战斗队——他们再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
蓄之愈久,发之亦猛。据一位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现在中央某大报工作的记者告诉我们:当时清华园内没有卷人红卫兵运动的学生,千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也是此时“破门而出”的——看着平反大会上一包包烧毁的“黑材料”,我们觉得自己身上也有某种扭曲了的东西,随着那腾空的火苗一下释放了……
看到班上几个仅仅叱咤校园风云几个月的革干子弟,一夜之间变得神情猥琐,我们感到了自己的恶毒——好啊,你们也有今天!不能有人的意义上的平等,那就让你们也成为“狗急子”吧,与我们有“狗崽子”意义上的平等。不,今天我们也不能讲平等,我们在你们面前也找到了某种优越感。这又是一种阿Q式的——“造反派”的“狗崽子”面对“保守派”的“狗急子”的优越感。
当听说刘少奇主席被拉下马了,当目睹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我们并没有这场动乱结束后人们常常自称的震惊之后的痛心,有的却是振奋之余的期待:也许这条又粗又长的嘿线将会得到彻底清算?我们父辈头上的那顶石磨般的帽子,有朝一日会纸片般地吹落?
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们使甘于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而我们,虽然看不清楚未来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但眼前的三倍的兴奋——能做个“人”的兴奋,能当一个“革命者”的兴奋,既能摆脱些什么、又能期待些什么的兴奋,就足以使当年十八岁的我们,投身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了……
毛泽东主席不但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还是个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熟捻这一代青少年的心理,犹如他早年在湖南熟捻如何从事学生运动。
至此,一个成份广泛、成员迅猛发展的红卫兵运动,取代了原来的仅以革干、革军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
九
也许,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目睹了: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杂乱无序,犹如蛛网,从年轻的革命者曾饮马的源头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诗章的名胜古迹,从被红海洋卷得晕糊糊的繁华都市到边境果林下那似剥开的荔枝一样水灵灵的小寨……
突然间,线条呈现了某种有规律的变化。多少旗帜立马转向,多少步履日夜兼程,多少征尘扑上双肩……似乎一场宏伟的战役前,千军万马在紧急集结!
传单、号外,因为有一条消息而捏在手里发烫;信件、电报,因为有同一条消息而被扑籁籁的泪水打湿——
12月9日,毛主席要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
后起的红卫兵中有两句很流行的话:“造反倍觉主席亲,革命方知北京近”,“红司令惦记红卫兵,红卫兵思念红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