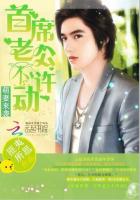“老哥,你不是说真的吧?”
看着哥那阴森的笑容,我不禁打了个颤。他该不会是来真的吧?我东张西望,准备如何安全可行地逃出这个鬼地方。当我看到门就在哥后面的时候,我的脸色可想而知。逃不了了!栽定了。
“我这样也是为了你好啊。去学农几天,有益身心啊!况且我也会和你在一起,没事的。你放心就好。”
哥在说服人的笑容越是灿烂就表示对方的下场会越惨。他现在简直笑得比拿了一百万还灿烂。他要整的对象,该不会是我吧?我们可是双胞胎啊!可是愈亲近的人就愈是糟糕,那可只是对哥这一个人而言。
“但是爷爷不是说以自愿性质为基准吗?我还有自主选择权吧。”我露出一个不算是太难看的笑容。
“可是他说男生是一定要参加的。而我们是双胞胎,更应‘有福同享’。”
我挑着眉斜睨着哥哥,是有难同当吧。有福的时候咋会想到我这个妹妹呢?现在还推我进火坑。哥你好恨心啊。呜呜呜……
哥哥二话不说,抓着我的后衣领把我拖了出去。看来,这回是跑不了的了。天可为证,那学农的生活和地狱是划上等号的。可我每次都逃了。根据可靠人士报告,的确是人间炼狱。而这次,还是哥哥和我一起去。我会死得更难看。
我衔着一根草坐在禾秆堆上呆望着天空。自从到了这个鸟不生蛋的学农基地后,我便天天如此。女生们只负责给庄稼浇水,吃饭的时候洗碗烧菜。怎么看也像个家庭主妇。唉,我倒没那么笨,可也好不了多少。毕竟我那个比恶魔还恐怖的哥哥也在这里。
“雨儿,有点事,过来一下好吗?”
我眉头紧蹙,好灿烂的笑容啊。这次又是什么啊?前天老哥找我割禾差点连手臂都砍下来了。现在手臂上还留着一道还渗着血的刀痕。这回倒好,什么也不用干了。哥倒是一直在照顾我。割禾这些事,哥也不适合去干。我都差点把手臂砍下来了。我可不想他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哥,咋事了?”我吐掉嘴里的草,侧着头望着他。
“也没什么事。你想象一下,一个文质彬彬的少年在烈日下滴着汗在田里拿起锄头松泥是什么模样。那是任谁看了也会心疼哪……”
“好了。不用再说了。这回要锄泥是不?可是有老师看着。我也帮不了你。你多说些什么也是白费力气的。”我比起眼睛直接躺在禾秆堆上,不打算去帮老哥干活。
“你忘了我们是双胞胎吗?到更衣室把衣服换转就完全毫无破绽了。”
晕倒。好真是亏他想得出来。我砍到手的时候怎么不见他感同身受。真是活见鬼了。明明就是双胞胎。偏要弄得我好像很好欺负的样子。
换完衣服出来,照了照镜子,也互望了对方一下。真的是毫无破绽啊……奇怪!突然好想揍他一拳。看着那张脸,忽然觉得好欠扁啊。
我把锄头拿起来称了称,这重量。不是哥能承受得了的。刚举起来向开始干活,从手臂上传来的疼痛感令我向后倒退了几步。忽觉有些暖暖的液体从手臂上顺着流到肩上。伤口,该不会是裂开了吧。身体突然失衡往后倒。糟了!
还好在锄头落地的时候,有人扶住了我和在身后的锄头。
定了定神,放下锄头转身想向那个人道谢:“谢谢。”
嘎?天晓?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启夜,没事吧。”阿清跑过来担心地问道。“你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不然雨夜可会宰了我。”
“你放心,我不会宰了你。”我顺手把帽子摘掉,长发垂了下来。
“凭你的力道,想要拿起那个锄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我望了望手臂上的伤口,朝他笑了笑,没有答话。血正从指尖滴到地面上。我半眯着眼,好难受的感觉。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哥哥的白色衬衫。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啊,雨夜姐姐前天割禾的时候割伤了。”
忽然有人从后把握腾空抱了起来。我错愕地望着天晓。他这是在紧张我吗?哥哥没说什么,一脸自责地跟在后头。
换了绷带,我坐在床上望着他。他什么话也没说,而我也不想说些什么。前些天的事我似乎变得不再在乎。也不再介怀些什么。只要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可以了。只要有解释,无论如何,无论是真还是假都没关系了。只要不要再骗我就没问题了。
“为什么要逞强?明知道手臂上的伤还没好。”沉寂的房间里忽然冒出的一句话顿时令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哥他拿不起锄头的,而且那些事他也做不来——”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听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行星都凉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光良《童话》)
“……说好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他也偷偷的掉泪了/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听着风我也笑了/他一定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光良《约定》)
发自两部手机的不同和弦铃音充斥着房间里的静谧。我们互忘了对方一眼,才撇过头拿出手机。
“喂?”我侧身倚着门框沿。
[是雨夜吗?]是泰锡哥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了?这么急。
“我是,有什么事吗?”
[伯母她进了医院,医生说一定要让和她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来才说出病情。你看看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赶过来。]
“好,我知道了。我会赶来的。”
我手机放回裤袋里。抬头便瞧见哥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我望了天晓一眼,他似乎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脸色不大好看。希望妈没事就好。一定要平平安安啊。
“知道了吗?妈她进了医院。”哥一脸担忧的。看得出来,他也很担心哪。
“嗯,刚才泰锡哥打电话来了。我们最好现在就回去。我不太放心。”心里总是很不安。不要有事啊,一定要平平安安。等我……
“我和你们一起去,我很担心伯母她。刚才接到萝莉的电话了。她已经回去了。”天晓突然插话。
“嗯。我打个电话。”我转身拿出手机安妥好一切。“行了。过一会会有车来接我们的了。先回房间收拾好东西。现在四点二十五分,五分钟后大门口集合。”
我说完便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房间里收拾好所有物品到门口等他们。毕竟我没带多少东西来。日用品这里也有提供,只有随行的几件便服等。而哥他们则不知道了。反正车还没来。也不管他们了。望着哥他们跑过来的身影,我颇有感想。运动果然不适合哥哥。
在车上我一直都望着窗外,诺大的车厢里一直都显得沉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有心情去说些什么。
“不要太担心,不会有事的。”天晓紧握着我的手,安慰着。
“谢谢。”
我望了他一眼便又继续望着窗外。他的安慰给了我无言的支持。一股无言的力量支撑着我临近崩溃的心。哥好不容易才醒了过来,妈你可千万不能发生什么事啊。
回到加拿大,我们打算先见了妈妈,确定她没事之后再去找医生询问病情。推开病房的门,看着妈苍白的容颜。愧疚的感觉便一拥而上。妈年纪大了,我和哥又不在她的身边好好地尽孝道。是我的错,那时候更是不应该离开。
“妈。”
“小夜?你们怎么都回来了?你们不用担心,我没什么事。只是有手流了点血而已。”妈笑着。她一直都很和蔼,就好像没有脾气一样。这才让我担心哪。总是那样装着没事的样子。
“是泰锡哥他叫我们回来的。忘了吗?你的生日就在后天。”我编了个不错的理由。而妈的生日也的确是在后天。不然又怎么能瞒过去呢?我并不想让她知道些什么。
“你们一定很困的了。时差能习惯吗?”妈抚着我的长发,轻声道。
“还好。我们中午再来看。好吗?”我笑着。
哥和天晓站在一旁始终都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们的心情都和我一样——好不到哪去。医生刚好来巡房。我关上了门。和哥他们走到医生的办公室才询问起妈的病情。
“你们是病人的直系亲属吗?”
我和哥点点头。
“病人之前有没有什么家族病史?”
“没有。我妈她到底是什么病。”哥急促地问着。脸色很不好看。
“我们希望再和病人做一次全身检查和验血。过几天你们最好过来一下。但在那之前我希望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从医院出来,我便一直很不安。哥变得沉默,也不再展露笑容。只是一直在说些我不懂的话。也一直在拜托我要照顾好妈。他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好像在说着遗言一样。
回到家中,哥有点事出去了。只剩下我和天晓。我回房间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果然还是有点不适应时差啊。
嗑——嗑——
是叩门的声音。大概是天晓吧。
“门没锁。”
天晓走了进来,坐在床沿担忧地看着我:“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有什么你就说吧。我不想被骗。”我坐直身子望着他。
“你大概忘了吧。你哥他小时候一旦受伤便会流血不止。而你妈也一样。那是低血蛋白症。不幸运的话,大概过不了二十五岁。但发病到死亡也只是很短的时间。我希望你能接受现实。遗传率百分之五十。你似乎没有这种状况。”
“遗传率……百分之五十……”我低喃着。
我的思绪快接近崩溃了。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哥他承受了一切。那一切该是我的。不是吗?我们是双胞胎,不是吗?泪水完全模糊了我的双眼。那是死亡的宣判。我所爱的人哪,为什么都不能平平安安呢?
“做手术可以令他们活下来。因为你没有遗传,所以……你能帮他们。但是,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天晓伸手抚着我的泪。
“我愿意,就算会死,只要能救他们。我也会做。”诅咒般的语句从我口中说出。是啊,就算会死,为了他们我也会愿意。只要他们平平安安。
“不要伤心,我会很难受。我和萝莉的事如你所见,我们是兄妹。和你一样的同父异母。说起来,也挺可笑。为什么有钱的人都喜欢拈花野草呢?而且,我有件事要跟你说。记得那天那个叫宇的男生吗?他是我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说真的,他母亲说他自上了中学就一直把你当成偶像。”天晓笑着。
“嘎?不是吧?”我惊愕道。那男生给我的感觉不像啊。那种深藏不露的感觉好像阿天啊。
他轻搂着我,一直都在我耳边低喃着一些话。一些叫我不要哭泣,不要自责的话。我轻轻地靠着他。
我享受着,享受着这种温馨而又甜蜜的感觉,享受上天赐予我这美好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