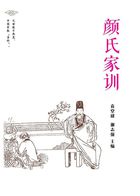诗曰:
时事犹如风与波,炎凉忽见世情多。
仙郎无计寻乌鹊,织女复思渡碧河。
黄叶寒林蝉噪语,青松绿竹鸟吟哦。
夫妻本是同心结,父母嫌贫无奈何。
却说康梦鹤,既葬了父,家业罄空,穷困彻骨,无以糊口,居则忽忽若有所忘,出则昏昏不识所之,起坐明月之中,吟诗二道:
其一
薄宵睡不得,起坐独悲吟。
明月照吾门,清风吹我襟。
运穷身自健,命蹇事多临。
静诵“白云”句,古人可慰心。
其二:
寂寂银钅工悬,泪垂飞杜鹃。
出门尽荆棘,举目有深渊。
昔虑风连雨,今忧雨接烟。
太行山绝望,空守齑盐煎。
至明早,陈氏呼梦鹤来前,因劝他道:“吾儿须觅一个生活计,不可困守诗书,坐以待毙。”梦鹤道:“儿非不想这事,但思要去舌耕,则无人荐引。要去肩挑,则身体懦弱。要承父之业,则不谙药性。若要著自己之艺,则突然而出,未免怕羞。犹豫数日,不知怎生的好,望母亲指示。”陈氏道:“吾儿多才多艺之人也,既不愿出头面以求蝇头微利,何不效班超、萧何,笔吏佣书,后为宰相、封侯者乎。”梦鹤沉思了半晌,说道:“儿虽不材,不过命运未亨而已。亦犹‘明月暂被黑云遮’,‘黄河尚有澄清时。’今既不得上登云路,已可愧矣,而乃故意入幽谷,毋乃贻讥士君子之林乎?”陈氏道:“吾儿虽贤,未及文宣万万。文宣又常为委吏乘田,不避羞辱,即子舆氏所谓‘抱关击柝,其职易称。’大凡君子有经有权,今正吾儿行经权之时也,羞胡为哉?”梦鹤想了一想,说道:
“也罢。儿思府县衙门政事纷繁,易扰心神。儿父临终之时,叮咛儿不可荒废诗书,氵风氵风在耳。倘入此途,便废本业。不如投在巡检司,衙中清净,庶不失棘闱素志。敢问母亲尊意何如?”陈氏道:“儿自思稳时便好。不过要求锥刀之末而已,岂要吾儿终身就此为活哉!”那知衙署淡薄,虽入去佣书,而所衣者百结之衣,所穿者东郭之履,往往见弃于群小。不幸又遇此巡司,为人暗昧贪酷。一日,上司差督民夫,往筑城池。一名夫,私放银五钱。那一日,点少了三名夫。你道这三名人夫,原来差役收折作银,称要交康相公过付。谁知此差人复往别乡,银尚未交巡司。巡司辄差内丁去问乡民。乡里的人都说:“康相公遣人来折去了。”那巡司竟不待分辩,默然具一禀帖报县。县主大怒,朱批即拿康梦鹤回话。至晚坐堂,衙役拿到,站在阶下。县主道:“你为何不跪?”康梦鹤道:“童生无罪,何跪之有?”县主怒道:“敢说你无罪?朝廷民夫,你好大胆擅自私放,是何道理?”
康梦鹤道:“情实虚诬,有谁见证?”县主道:“你本官现证。岂有你本官自卖,而诬赖你乎?”掷下四枚签发打梦鹤。梦鹤坚执不屈,说道:“饱学书生打不得。小童生不过暂屈佣书而已,非比衙役之辈,且实无弄权真情,决打不得。”县官愈怒,喝差役将竹板乱打,打得一身黑烂,走亦走不动。着差役赶出回家免究。嗟嗟梦鹤,真个可怜,以平日激昂慷慨,英雄自命。至此,因家贫之故,而受这苦楚羞辱,如之奈何!时师友怜惜之,各有诗慰问,其诗甚多,不录,惟记得吴先生一首,诗云:
停杯不饮意殷殷,思象有牙身致焚。
欲效执鞭希求富,何如闭户勤论文?
虽云穷困正相迫,孰识智愚自此分。
甚负性心应增益,古来俊杰多如君。
又有一友郑判枢,乃锦园之子,心虽侥险,文理稍通,与康梦鹤世交,亦慰一首,诗云:
问君何事蹙眉贫,且向花前看暮春。
岁月易迁人易老,乾坤当阔志当伸。
难缺必须缺,皎皎无尘终有尘。
吾辈未亨多偃蹇,可怜和寡辱金身。
又有一友,姓洪名初中,其为人好险骄傲,腹无点墨,好交高明贤士,久慕虚名,并不自知其分量,亦勉强作一首来慰,诗云:
祸不单行运未来,福无双至且有灾。
劝君休得多愁虑,有山不怕无烧柴。
却说梦鹤被打之后,母子相抱而哭。亏了他母亲,与邻里辟径佣雇,食一餐,饿一餐,养了数月。稍能行动,即到师友书馆中谢诗。见了洪初中,说:“多谢兄盛心,做诗相慰。愧弟袜线短材,有辱一二知己。休笑休笑。”初中有夸己能之意,说道:“总是命运未亨,谁敢笑兄。昨日之诗,弟甚爱惜兄,未知兄晓得否?”梦鹤道:“弟亦知是爱惜,但其中有蔼然深沉处,弟未曾觉悟,愿兄勿吝云沾开塞。”初中道:“弟这诗不只矜怜兄,且愿兄后日发达。”梦鹤道:“多谢多谢。敢问兄做诗,学业是谁?”初中道:“诗不过字要多寡相对,词要长短相参,便尽了诗之能事,何必学业?弟皆‘聪明句’也。”梦鹤道:“兄差了。俗云:三年读成举子,十年学不成诗翁。诗非锦心绣口,旷达不羁之才,不能道只字。诗正未可容易轻之也。”初中怪其有藐他之意,遂拂然道:“论兄之才,是欲压倒元、白乎?”
梦鹤道:“弟不愿自比杨汝士,兄亦安可自称元、白乎?但朋友之义,有善相赏,有疑相析。要愿兄后日推敲为佳。”梦鹤知其无受益之心,礼意稍疏,遂拱了一拱,告别出门。初中亦不眷恋他。初中窃自说道:“有病不能医,沿街卖嗽药。他自己把一书算尚做不成,还敢夸他才学!明明是奚落我了。”遂抱恨在心不题。正是:
奸人匿怨外相亲,弄起祸胎有一因。
玉石相须各从类,才高难合庸流身。
他日,康梦鹤抑郁在家,闷闷不乐,含羞忍耻,出游街市。忽见一簇旌旗伞盖,坐着一位官人,前呼后拥,乘马而来。梦鹤冷眼一觑,乃岳丈蔡斌彦也,遂要躲闪。藏拙间,已被他瞩目看见了。蔡斌彦心中自思,要问他又不便,乃扬鞭过身去。但眼中观其衣衫褴褛,状如丧家之犬,心内十分不快。原来蔡斌彦因吊征山贼有功,除授湖广指挥,现今又超升广东都司,才给文凭,告假归家。却说这斌彦,一武夫之流,那里晓得甚么才子,不过趋炎避冷而已。见康梦鹤这等穷酸落薄,归来对他妻许氏说道:“你知康家贫辱之事乎?”
许氏道:“自夫君别后,俺母子只是闭户勤针指,窗前观古书,并不管一毫闲事。但前日闻得行路人叹道:‘康其祥有这般丰采伟略,无故充为书役,于今被打,深可痛伤。’未知其祥是何人。”蔡斌彦道:“其祥即是梦鹤的字。我昨日去拜客,在街上遇着他,看他形体枯槁,衣冠破烂,不知羞耻,还敢在街市中摇摆!这样人,终非发达之器。我今想了一计,唤家僮去请他来,把聘礼假做送他为家资,还他去别娶。你母子好同我一齐到任。我可在那任中,选一个膏梁子弟,匹配吾儿,亦不负吾儿一生受用,岂不是好?”许氏力劝道:“他亦是富贵儿子,今虽落薄,安知后日不富贵乎?当日成亦是君,今日要改也是君。姻缘大事,那里这等儿戏!”蔡斌彦道:“你不晓贫穷之艰苦,一日难度过一日。今我把银子与他生涯,庶免饥饿他,吾儿亦可得了一个佳婿,岂不是两便?”平娘侍在母亲身傍,闻他爹这等言语,粉头低垂,蛾眉颦蹙,既而两颊通红,正色说道:“儿闻‘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既受了聘,千金不移,岂容变更。”蔡斌彦道:“妇有‘三从’:在家从父,你父主意是要你好处。吾儿苦甚么?”平娘道:“共姜其生死且不改。纵连理之枝可破,而比目之鱼难分。之死矢靡,铁石之矢,只何不谅儿乎。”蔡斌彦低首无言,心内思想,忽叹一声,说道:“闷杀我,闷杀我。罢了罢了,我自有道理,不过多些金帛酢他。”正是:
冷暖顿殊深可忧,天时人事两悠悠。
花枝失却东皇主,雨雨风风那得休!
且说平娘,自幼从母教养,到十四五岁时,果真秀气所钟,天地阴阳不爽。有百分姿色,自有百分聪明,便知书能文,竟已成一个女流学士。是以蔡斌彦爱宠他,不忍堕落贫贱之家,使之憔悴劳苦,误了一世风光。至明日,斌彦默遣家僮往康家去请梦鹤。梦鹤对母亲说道:“蔡岳丈除升广东都司,领文凭归家。儿为半子,愧无樽酒洗尘,及蒙辱爱先施,如之奈何?”
其母陈氏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俺家淡薄,你岳父谅必闻知。他念及表亲,重之以婚媾,况你父在日,与他把臂谈心,如胶如漆。今来请你,必是不怪你。我这头上一枝簪,你可持去买几件礼物,付他家僮带去送他,聊表一片悃忱之敬。”梦鹤领命,遂借了衣冠,同他家僮往见斌彦。那知斌彦备了白金五十两,绫缎款端。及家僮报说:“康相公到了。”斌彦出门亲迎,入堂坐定,茶罢,说道:“多烦台下贲临。”康梦鹤道:“岳父说那里话。愚婿不孝罪深。缘父弃世,家事萧条,礼意疏阔,徒郁结心血耳。幸得岳父高升,方恨拜贺无具,非不欲通殷勤,但寻思了无进取。今岳父念及先父前交之情,遣使宠召,则大幸焉,何出此言?谨备些菲仪,聊表鄙忱,万望叱存,幸幸。”蔡斌彦道:“何须多费。请问贤侄如今作何生涯?”康梦鹤思量道:“此人必有异志。怎么叫我‘贤侄’?且莫管,看他是何举动。”乃应道:“儿不过一介书生。日以笔墨为钩距,以诗书为田畴,囗情耕耘,无时休暇。儿之生涯,如斯而已。若别有生涯,必多本钱,儿所不谙。”蔡斌彦道:“吾亦知贤侄无本钱,是以备白金五十两,要付贤侄去生理。倘大发财时,要择佳配,岂无贵宅豪门之女儿?你表妹平娘要随我上任去,未知何年何月得回,恐误贤侄青春。未卜尊意如何?”康梦鹤听得这话,心胸涌然,正容危坐,说道:“岳父,你晓得,‘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你勿轻视儿处今日穷苦,有辱蒹葭倚玉乎?”斌彦道:“不然。吾闻君子当知变通,今贤侄这等贫穷,权将这银去做本钱,倘后日发达,再择佳配,讵不善甚?何必执一。”康梦鹤道:“岳父非此之意也。岂不闻自古英贤多磨挫,大困之后必有大亨。我学成满腹文章,胸罗象数,气吐云霞,思入云中,今虽困抑,譬鹄未羽,不日定夺锦标,劳力一击。万里之遥,岂藩篱之晏鸟所能料乎。”蔡斌彦道:
“不必夸口,做过才是。如我当日,数百盟兄弟,只得我一名侥幸,官正未易做也。”梦鹤道:“岳父这等说,是欺儿日后不能成名乎?就将今日来论,你虽区区做了一个武夫,岂遂能胜我堂堂一书生乎。即我之家风,有不若你乎?抑我之品诣,有不若你乎?”斌彦艴然变色,默默不语。梦鹤道:“罢了。你要退亲,凭你退亲。我何慕金帛之有,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乎。”遂忙忙抽身出门去了。斌彦楚其狂妄,对家人道:“这个人,整日夸言大语,胡思乱想。不久恐到疯癫。不要管他,等他疯癫了,再来处置未迟。”嗟嗟,富贵则亲戚畏惧,贫穷则婚姻不许。正是:
反躬自问信真贤,不必求人然不然。
富贵吐言颠亦正,贫穷出话正犹颠。
许氏与平娘在后堂,听得梦鹤这话,对平娘说道:“这人雄才伟略,言谈皆琳琅,唾笑成先王,不坠青云之志,愈令人可爱可敬,决不可轻忽他。我自然一一区处。”即唤一个丫环,去等他出门,请住他到这花园私轩中。“我可说些言语安慰他,并可与之设下一策来娶。倘跟你父亲去广东,大为不便。”乃吩咐丫环去候他。那知丫环候他已久,坐在此石上打睡。
梦鹤怒气汹汹,向路直走,足如蓬转,挨在丫环身边过。那丫环醒时,梦鹤离身已远,任丫环叫梦鹤,绝不回头。丫环回报,说他不肯来。平娘柳眉低蹙,杏脸生愁,忽长叹一声不题。那许氏亦尝力劝斌彦,说:“这婚姻乃凭天后娘娘为媒,签诗为记。未出母胎时,已先注定了。况且当日与表舅相交,如‘雷陈’,如‘管鲍’云。你我之私,到于今变了卦,倘我君百岁后,何面目见舅亲乎?”斌彦沉吟半晌,喟然叹道:“叫他有银子,火速来娶去就罢。不然,若随我到任里去,那时关山阻远,悔之无及。”许氏即退与平娘商量,如此如此,唤丫环去请梦鹤。未知梦鹤来否,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