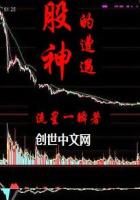眼泪不过是忘了关门的月亮河,
我很难过,挡不住的是星星——
滴答,再滴答,回响做钟的遥远。
——摘自江沁的博客《泪河》
我曾听说过一个忧伤的日子,那是白色的情人节,我常想,这样子的名词约莫是只属于我的,所以终年如一日,我吃着一个人的饭,唱着一个人的歌,洗着我一个人的衣服,和看着我一个人的镜子。从那一刻,我开始明白了独角戏的含义,我始终是那么难过,很多天过去了,我和汪洋的关系,终于是冷得仅局限于见面打打招呼这么简单。
哦,到底有多简单呢?这样子简单的一个为题,时时刻刻都把我的脑子绞成只有一根线的神经质。似乎不晓得为什么,他已经开始刻意地疏远我了,就好像刚才的那个样子,他只是从楼梯上上来,寒暄了几句,然后就同我说再见。
我失落极了,我却没能告诉他,我失落极了。
我掰着指头算了算,这是这个月以来第七次碰头,每一次他都是笑着,然而就匆匆地离去。渐渐地,他在我的印象中,也桎梏地:只剩那么一个背影而已。就好像是黄昏的最后一道光,无端从生命中狠狠抽离一样。于是我开始哭,习惯性地缄默而泣。眼睛为此而红的吓人,很多的红血丝带着泪爬上眼球。我买了好多的眼药水,蓝色的液体有着很土的名字,叫——珍视明。我想我认得广告纸上的那个矮个子,他曾写过很多的小说,于是郭敬明三个字儿,成为了最浪漫的字眼。
不能否认,我好喜欢浪漫的事儿,然而滴着眼药水哭泣真真算不得什么浪漫的感觉。您说,有没有那么一刻,他会观察到我为他而哭么?似乎还真是没有的,或许我还能更肯定些——是一次,都没有。您看得到,不是么?他一走开,我就会带着湿润地难过望着他。远远地,几步路,仿佛隔着比星星还要遥远的距离那般。
我没敢追,也不敢叫,只是心里总是会呐喊着:“回头,求你回头啊。”
可是,您看,每每他带着笑容别过头去,就会一路坚定地走开,恍惚间,我不是什么学生,他也不是什么老师,我们只是一对曾经熟悉彼此的陌生的孩子,瞬间长得太大了,所以世界容不下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彼此远离着——去寻找另一个不会再碰头的世界。
“唉~”我很轻很轻地吁了口气,然后望着镜子里头悲哀得不像话的自己。就在半个多小时以前,我还在美术课上头埋着头画了好久的自己。很久很久后的几分钟,我才迟钝地发现我画的根本不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没法离得开他了,因为很大很白的一张纸,都被他的面孔给填充满了——蓝色的彩色铅笔,蓝色的轮廓,这一张俊朗的肖像像是抽象到极致完美的海,他是人形化的,这位这世上没有比他更独一无二的人,所以我爱他爱得要死。
哦,疯了么?我想我已经疯了。即便是一个区区的美术老师都冲着我的作品指指点点。
“哎呀,谁教你用彩色铅笔画素描的?我要得是意境,意境懂吗?”
“重画,难看死了。”
“你到底会不会画画,我没见过你这么难教的学生。”……
她骂了一节课,没和一口水。记性一直不好的我没能记得住她为我浪费的每一个唾沫星子。
只是她说:“你就是个爱搞四不像花明堂的怪女孩儿。”
这让我的耳朵疼的不舒服。我从想过会是什么四不像,尽管当所有人的素描里都是成片黑白的世界时,我已经拿着蓝色的刷子为那片大世界里隔离出去的这片小世界染色了。我不属于欢乐,所以注定孤独。我也不属于悲伤,所以注定更加悲伤。
我不想这样的,我常常这样无聊地假设,如果从未认识他,我还会是一个开心的姑娘,听着一首不想长大的歌儿,然后也就不会长大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为着这样子类似而一次次无言的邂逅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他叫汪洋,而我是一个爱海的人,所以沉溺是我在死之前都没办法摆脱的命罢。他彻底走远了,我恍惚间想起了他手上一直紧拽着的一束花,它是白色的,我又看了看洗手池旁的镜子,里头的自己湿湿的眼睛像泛滥的水花一样。我挤了挤湿哒哒的袖子,蓝色的水滴答答的掉下去。
“他是有喜欢的人了么……”
我不敢想,因为看到了他买的花不是给我的,我又哭了。
可是——我凭什么奢望他会给我买花呢?就因为他买了花么?
这是没道理的。
“哎哟哎,你~是在哭么?”
很突然的一刻,我猛地抬起头。
镜子的映像里头,多出了一张脸。他撅着嘴,插着裤带儿在那个不远不近的水池子旁看着我。我以为是大白天撞了鬼了,猛地回过头去,才发现真的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