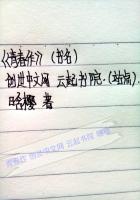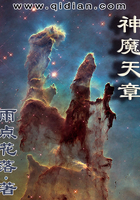你给我一滴泪,我返你一片汪洋。
这是别人的句子,我曾经拿着蓝色的画笔,把它抄的满墙都是。
你一定觉得我疯了,可是上帝作证,我真的没有。客观的来说,我上辈子是水里的鱼,因为蹦跶久了,所以这辈子离开了水也照样没办法活的。
“你是牛变得吧!”那甘甜就常常讽刺我说:“喝得多,也属水。”
我没有为此生气过,因为我一天真的要喝下起码三大杯的温开水。
“人要喝水,猪要喝水,蚂蚱也要喝水……”
琼瑶一些地讲,这无可厚非。因为破电视机里一遍一遍重播的台词已经烂到耳朵里了,不听也能晓得,其实水也算是个蛮重要的东西。不得不补充的是,就像我先前提过的那样,我爱带海的句子,也爱带海的书。好比一副插图,再好比就书名上头比较吸睛的一个字儿,我都会买下来,最后搞得一天的晚饭钱都扣得拘谨。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而哪怕到现在,一本接一本买来的书也都新的跟没翻过似的。灰尘积得算少的,还是一本絮絮叨叨的散文。我不怎么看,只是依稀记得那书的名字是特别好听的,叫——“左手倒影,右手年华。”
长这么大,那是我唯一一本一抱就是一下午的书,当然,能看的全部也只是封面上那几个带着阴影的字儿罢了。它们像人的影子,挨着脚后跟,也就甩不掉了。
我拿着妈妈留下的一个旧盆子,对着水里的影子数着头发,于是有小半年都没有正儿八经地照过一次镜子。我不大喜欢镜子,因为只有水里才会有影子,碰一碰就涣散开了。镜子的映像看着不是我,倒像是怪科学里的克隆小怪兽。而甘甜是不同的,她喜欢背血红色的包包,像一个女人一样的在包里背一个镜子。那里头还有一个带齿的大梳子,她时常拿着它梳着粗粗的大辫子,然后在后脑勺上挽起一个瘤子一样大的苞。
瞧,她又在梳了,她是那么用力地梳下去,细齿的木梳上头就多了一把干干的头发,而她还在开心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才心满意足的收起她的梳子,笑眯眯地拖着腮帮子傻笑。我似乎发现了她一个小小的秘密,此时此刻,站在台上的海浪皱着眉头,显然被她看得不自然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那样子望着一个男生笑呢?我觉得她心里头住着一个爱穿透视装的小女人,就像不能说的秘密一样,因为不会想让人晓得,才会笨得把口红吐在了牙齿上。
“老师~,脚疼。”
我懒懒地趴在了桌子上。海浪举着手打了个报告,听着像个笑话。
“咋呢?还想坐?”
美术老师这时候在座位上翘翘了她踩着高跟鞋的粗大腿,啪一本书就砸到了课桌旧旧的一个角上:“忍着!”我把脑袋从臂弯里抬起来,不露声色地朝着海浪望过去。那里的他,站得懒洋洋,好像是海面上快要下沉的太阳,斜斜的漂浮在了几个快要破碎的泡沫上。
“他…很累吧…”
我对自己的心这么说。
也不晓得为什么,居然有些同情起这个没心没肺的人了。他从不像个好心的人,所以每一个笑都像是撒旦的给予,看着是那么地坏。而他今天的出现,却像是一场慈悲的以外,上帝给了他一对翅膀,于是他做了我身边的黑天使。偶尔的时候,他会这么鸟一样地飞过,我悲惨的世界,却因这算不得福音的声响,得到了我原以为没办法企及的庇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