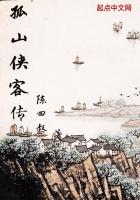云是我的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一直相随。可能是性格差别的缘故,我与云的交往,很平淡,有点顺其自然。
与云第一次发生矛盾,是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刚刚盛行种植蓖麻,学校组织各班级在离校园两里开外开辟了一块空地用以挖坑播种。一次,上体育课,安排大伙自由活动,因为天气炎热,我提议去蓖麻地附近的水塘里游泳,伙伴们齐声叫好。而云和金两个人闪在一边,默不作声。有人问:“云,你们怎么说?”云毫不犹豫地摇头。我说:“那好,有话在先,不准告密,否则,变成小狗。”然而,事与愿违,泄密的事很快发生,正当我们欢快地在水里游弋时,班主任的身影朝这边晃动过来了。我无意间瞥见,惊慌失措,大叫一声,抓了衣服就往旁边的林子里狂奔。尽管没有当场“人赃俱获”,但老师还是处罚我们一干人站在讲台上“示众”,并在课后背诵《英雄陶绍文》等文章。我坚定地认定是云告的状,并从此将他列入甫志高之流,敬而远之。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不知不觉间,我与云都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广西的一所学校;而云,则去了省城的一所中专就读。据说云的父亲每次必送,好像生怕他唯一的儿子有所闪失。
我们恢复了来往,经常互致书信,沟通信息,彼此之间变得友善起来。假期里,我们会上对方家里小坐,甚至吃上一顿便饭,双方的父母也笑在脸上、乐在心里。尤其是云的父亲,一位个头不高、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对我格外的热情。印象中,他算是村里极有学问、涵养的男人。毕业后,云被分配到了一个叫杨桥的小镇,在供销社里厮混,而我则去了赣江之滨的一座古镇工作。不幸的消息很快传来,云的父亲竟然英年早逝。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上有体弱多病的母亲,下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妹妹,云不能不经常请假回村,甩起了牛鞭,耕田、种植、收割。我们见得是越来越少了,大多情况都是从我的父亲母亲那儿断断续续听来的。末了,我们总忍不住一阵叹息。
我调到新余一家铁路单位的机关后,云来看过我一次,是带了他的女友同行的。记得那女孩瘦高如竿,落落大方,嘴快而脆,像炒锅里骤然蹦出的毛栗子。云倒是依然那副不紧不慢的模样,说话轻声细语,温文尔雅。两个人看上去感情不错,连看电影的路上,手都舍不得分开。我为云庆幸。接下来很自然,云结婚生子,为人夫为人父了。他的妻子依然是那样的营养不良。一次,在老家的路上相遇,发现她出奇的高。我问:“云呢?”她干干脆脆:“他哪有你安稳啊,单位效益太差,早就下广东打工去了。”我才知道,云为了生计,不能不远走他乡了。毕竟在国企待惯了,“皇粮”吃得从来不慌,我愣怔了半晌,一身技术的云,想不到这样被命运捉弄。
关于云的消息越加少了,每次获悉片鳞只爪的传闻,却着实令我吃惊,比如,云在老屋旁边建了房子;又比如,云又养育了一个儿子。最近,听说云在故乡的公路边又建了一幢楼房,有些花园洋房的韵味。我看得越来越像雾里了,不知是他故乡情结太重,还是农民的意识太强烈。云可顾不得许多,在村人疑惑的目光里,他一边在异乡打着工,一边将责任田里的庄稼侍弄得有模有样。云的母亲,一位几乎皮包骨的女人,在儿子的努力下活得极阳光。
寻思开来,有七八年没有见云的面了,更无从得知他在外面的艰辛和无奈。随着工作的变迁,我回家的次数也稀少了,夜深人静时,会常忍不住想起童年的事,一种暖暖的感觉渐渐漫溢在全身。
云,何时能相聚在故里,共同举杯,为我们的过去也为我们的未来干杯?
2007年10月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