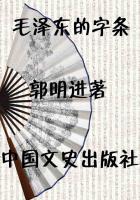久别了故乡,一切变得生疏,许多情况,是从父亲的手机里听来的。每次与父亲通话,便似乎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芬芳,耳边飘来熟悉的俚语,乡亲们的音容相貌一一浮现在眼前。手机里的故乡,像攫取童心的动漫,气韵生动,富有张力。
“那位独眼的老人也过了。”前几日,父亲在手机里告诉我,他是刚赶回彭家园参加葬礼的。
我忍不住又将脑海里那些熟悉的乡亲过筛了一遍。老郭!我忽然怔了一下,那个许久未曾谋面的老郭,他现身在何方?
我没有问,因为不愿意再听到什么不幸的消息。
老郭是那种天生乐天派,尖尖的脑袋上残存的几根头发早早白透了,风起时,犹如扎在头上的银针。一件深蓝色的上衣,永远显得过于肥大。高而奇瘦,使老郭一看去便像遭了天灾一般。走动起来,直令人感觉一个稻草人缓缓地飘过来。
老郭住在村东头的一座老宅子里,到处黑糊糊的,仿佛永不见光。据说年轻的时候,老郭便出去闯荡,至于干什么营生、到了什么地方,似乎没有谁去打听,他自己也无意四处炫耀。在我开始学会记事起,老郭带着女人回来了。印象中,女人身体不是特别健壮,经常在灶前咳嗽,不知是被柴草的烟熏的,还是她生来就是林黛玉的坯子。
那时,乡村的夜晚没有多少可消遣的节目,看不见电视,难得见一回露天电影,当然,麻将也未兴起,因为大家手头都没有可供挥霍的余钱。星光灿烂之际,大伙喜欢聚集在空旷的场地海聊。这时候,那个稻草人一般的影子飘过来了。老郭,很快成了话靶子。他似乎乐于被别人取笑,往往在别人尚未来得及擦拭掉眼角的笑泪时,又以他特有的语言强调一句:真的,上次从水东看戏归来,我确实从上搭(丘)店(田)里跌到了下搭(丘)店(田)里!
于是,场地上更是轰地笑炸开了。
记忆中,老郭与老满十分要好,像一对难兄难弟。不同的是,老郭似乎不专注于土地,甘于青菜汁南瓜汤的日子。农忙时,我见过老郭站在犁耙上鞭打着老牛,一身溅满泥巴,瘦伶伶的身架好像一副圆规。我怀疑一个不小心,他便要倒栽葱下来。老郭却若无其事,活稻草人继续在希望的田野里懒洋洋地甩起鞭子。不管人们露出怎样怀疑的目光,老郭的庄稼终究有一茬没一茬地长起来了,一家的口也糊过去了。何况,老郭的可爱,并不在于他是否是侍弄庄稼的好把式,而在于他那张太能爆笑的嘴、那种永远不计屈辱的性格。
遗憾的是,老郭与老满殊途同归,一对同命鸟,先后还原为“单身贵族”。
我曾经无意间走进那栋老宅子。里面一片死寂,冷锅、冷灶、冷屋,破旧的农具泛出森森的冷光,一种逼人的寒气扑来。我情不自禁打了个冷噤。我无法猜想,乐天派的老郭原来生活在如此毫无生气的地方。那个活的稻草人,他真的就是我们眼里的那副面孔吗?
忽一日,那个女人神秘失踪了。我几乎就没有见过那个女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她犹如一个传说、一个影子。
没有多久,那老宅子的门上重新挂了一把大锁。老郭也走了。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再也不曾见到那个活的稻草人。空阔的场地上,再也没有那种爆笑。而我只记得他那一句:背时噢,我从上搭店里跌到了下搭店里!
2007年6月1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