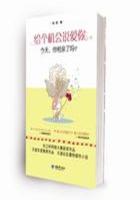“药药,真……真没什么不……不适吗?”花香立起身,对药药上下其手,仍不无担心道。
“你别打岔……”药药坐回椅子上催道:“快说快说,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
花香瞧药药神态往常,知道是没甚事了,心里是又拜菩萨又拜佛祖,又谢天又谢地的。怕药药又要去问李才洋,加紧道:“你走后,才洋哥情绪很低落,他经常来找我,只叫我陪陪他,然后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才洋哥和你打小一起长大,情同兄妹,你突然离开,如人间蒸发了似的,怎么找都找不着,不仅才洋哥着急难过,我也一样难过着急,所以哪还说得出什么话来,再有安慰效果的话语皆是枉然。有一次,我去厨房拿东西,见着别个人在架柴生火,心里泛起了嘀咕,以前都是李才洋负责这活儿的,换了别人做不来,除非才洋哥有特殊情况,否则这活儿谁都不让干。可能才洋哥家里有事儿,告假回家去了。我心是这样想,脚已走到了才洋哥居的屋前,见屋门虚掩着,猜才洋哥还没走,就推门进去,进去后看到才洋哥躺在床上睡着了,我想才洋哥可能是太疲惫了,回来躺躺,幸好我没敲门,不然就把才洋哥吵醒了。待我要轻悄悄退出去的时候,才洋哥忽然……忽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口里直叫我别走别走。我被才洋哥拉住,又为了不惊醒他,我就定定的站在那,由他拉着。恰在我站得脚有些酸时,拉力蓦地加大,我一个不注意就……就像今天这样,跌到了才洋哥身……身上。”说到这,花香倏然停住,白皙的面庞烧得一片火红。
药药的脸也微微泛红,明知道将要发生的是什么事,她还是问:“才洋哥他把你怎么样了?”看来是存心想窘窘花香了。
花香转过身去,绞弄着手指娇羞满然并不答话。
药药‘扑哧’一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继而摸了摸肚子又道:“花香姐姐我真的很饿了,可以吃了吧,恩?”语调煞是嗔恳。听药药这般说,花香登时松了口气,既庆幸药药不再咄咄逼问,又庆幸这一跤幸好没摔出个罪大恶极大祸临头来。
“可以了,可以了。”花香一边勺汤进碗里一边道。
药药等不及了,把一盅汤直接拉到面前,拿过花香手中的勺子就座喝起汤来,谁知才喝了两口就没胃口了。把瓷盅移到了一边,拿起筷子夹菜吃,五盘佳馔一一只尝了一口,药药无奈地放下筷子道:“吃不下……”明明肚子饿得可以,汤菜也美补得可以,可她怎就一点食欲都提不起来呢?药药无助地看向花香。未及花香答话,药药忽感不适,只手撑着桌子,俯身呕吐起来。
花香见状赶紧过来,一面柔柔拍药药的后背,一面关心道:“药药,你怎么样了?”药药干呕连连,哪有功夫答话,只是抬手摆摆,随即又撑住桌子呕得翻江倒海。
好一阵子才缓和过来道:“我是不是吃错什么了,吐得我都快断气了。”
花香摇摇头道:“你也没吃什么呀……”手指朝桌面在空中画了个圈接道:“这些汤菜可都是上等佳菜,既营养滋补又美味妙口,是老夫人特地叫厨子为你烹饪的。老夫人说,吃了只有补得份儿,一点儿害处都没有。”
药药更是困惑了,不及细想又干呕起来,又是一阵天翻地覆,吐得直要晕了过去。连花香都焦忧起来,手脚不知所措。她哪里想得到这是有喜的正常症状,只道真是这些汤菜的问题,忙一面叫人撤去汤菜,一面要唤人去告知老太太,一面要呼人去请大夫。后两个都被药药摇手止住了,又干呕几下渐渐转好,神色惊疑,左手往右手脉上一搭,心中一凛表情俱僵,一颗心突突突直跳:是喜脉!她好生糊涂,怎么连自己有喜了都不知道,怪不得近几日总感觉全身怠怠,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动,吃的也不多还道是自己的食欲问题,熬药时也会干呕几下,不似刚刚那般严重,还道是闻到那难嗅的药味的自然反应,谁知道会是……
忽然想起那夜与龙石延的缠绵,药药登时腮浮红晕耳赤面红,她怀上了龙石延的孩子!这一惊不小,但接着就为欢喜所代替。药药迫不及待地想和人分享这个初为人母的欢喜,当下拉住花香激动道:“花香姐姐,我要做母亲了,我要做母亲了。”花香听了,亦心中一惊,睁大了眼睛:原来她自己都还不曾知道。
“药药,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亏你还是大夫呢,连自己有喜了也不知道,我都羞你了。”说着,便在脸上划羞。
听花香的意思,明摆着是早就知道了,药药更是诧异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除了你自己,所有人都知道。”花香做了个无奈的表情道。
药药贼兮兮一笑又道:“那——你会不会也有啦,我给你搭搭。”言刚毕,就伸手去搭花香的脉,花香见状忙躲开了,脸兀自一片羞红。花香瞪眼赧羞道:“药药!”药药做了个鬼脸,格格笑了开来。
药药让人传厨房做了几样清淡的小菜,勉强吃了一些,不够饱,又吃了花香拿来的瓜果,才把肚子牵强填饱。药药吃完,在躺椅上休息了须臾,醒时瞥眼往门外一瞧,太阳西斜了,天金黄金黄的,看来天就快要黑了,突然想起她还要回去给金泽熬药,她得和老太太说一声。看花香躺床上睡着了,也不忍叫醒她,七月天是最让人犯困的,就由她多睡会儿。
药药轻悄悄合上门往老太太那去,跟老太太说一声,她要回金家去了。恰走到门口,听里面有人说话,靠在门栋悄悄觑眼往里边一瞧,见里边分宾主坐满了人。龙家一家老小都在,杜水笙也在,还有两张陌生的面孔,看年纪男的不过五十来岁,女的不过四十来岁,穿着打扮富贵华丽,显是有权有势的人家,又杜水笙和他们坐在一块,应该他们就是杜知府和杜夫人没错了。
谈论龙石延和杜水苋的婚事,但她还是想听。
厅里沉默了顷刻,倏然“哐啷……”一声,一个绣花瓷杯摔地粉碎。杜青频站起来,脸色铁青怒极气极道:“甭想,我们杜家是什么人家,岂能让你们所摆布,说退婚就退婚,门儿都没有。”
杜青频这个‘你们’是不是说重了些,从头至尾只是延儿在解说道歉,他龙鸿天二夫人还有老太太还未发一言,就摆起官架子来,未免太有些目中无人。要换作以前,龙鸿天势必会对杜家又忌惮又巴结,想方设法地讨好,是以才给儿子和杜水苋定结了这门亲事。可是现在不同了,他龙家的地位已经可以和他杜府相提并论了,即便杜青频是官他是商,尽管当时官贵而商轻,但钱银是个好东西,谁拥有得越多,谁就愈有权力说话,管你是官是商是农。钱银多了官府自然也敬你三分,不然何以获得免费送上门的银票。他龙家的丝绸生意近年来是越做越大,也逐渐脱离了官府的控制,开始了私人式的经营。别说是杜青频了就是朝中的二等官也不敢这般小觑他,可杜青频就是小觑了他龙鸿天,龙鸿天顿时拉下脸来,心中已然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