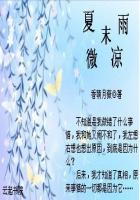待谭月筝从那故事中回过神,时间已经过去不少。
她只能起身,嘴角轻弯,不知怎得带上了几分淡然。“谢过光侍卫为我解惑,只是时辰晚了,月筝该走了。”
光玉堂还是看着她,那双眼睛中带着赤裸裸的情绪,像是能发出光芒,让谭月筝有些不自在。
“我知道《永寿天年》毁了。”他轻轻道了一句。
谭月筝抬起头,无奈地苦笑,“知道的人,已经不在少数。”
光玉堂突然向前几步,惊得谭月筝往后一退,右脚一滑,竟是要掉入湖中。
“啊!”她惊呼一声,光玉堂疾步向前,灵巧的一伸手,揽住谭月筝的柳腰,再一转,卸去惯性,稳稳地站在了湖边。
像是做梦一般,谭月筝许久没被一个男子这般护住,上一次的话,还是那个负心的左尚钦。
光玉堂的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香气,一身柔软的黑绸触感极好,胸膛宽阔而有力,这时候脆弱无比的谭月筝,自然是希冀这样一个胸膛可以让自己依靠。
再一回神,谭月筝冷汗惊了一身!
这可是太子东宫,太子良娣与太子侍卫举止亲密,这是大罪!
想到这里,谭月筝急忙用力挣脱,面色慌乱。幸好光玉堂也没有用力,倒是轻松地被她挣脱出来。
步子慌乱的退了几步,谭月筝一张俏脸还是微红,刚要告退,突然听见左光堂充满磁性的一句,“我定会帮你。”
谭月筝心下一乱,连告退都不说了,跌跌撞撞地跑了。
跑出湖边,正好碰上闻声赶来的茯苓,茯苓急忙问道,“没事吧主子?”
谭月筝强装镇定,步子缓了下来,眼角余光向湖边瞟了一下,道了一句,“没事。我们回去吧。”
茯苓依言点头,帮谭月筝又紧了紧华裘,方才随着她走了。
而那湖边,光玉堂还是站在那里,眼神迷蒙,手中攥着几缕方才不小心自谭月筝华裘上揪下的绒毛,细细地嗅了嗅,旋即浅浅一笑。
“哼,你可真有雅致。”一声冷哼自假山另一处传来。
光玉堂仔细地将绒毛收起,脸上波澜不惊,“你何时来的?”
只见一身黑衣的童谣轻巧地自假山上跳下,轻轻着地,眼中嘲讽之色深重,“从你开始编故事的时候,我就来了。”
光玉堂抿嘴一笑,“谁说我那故事是编的?”
童谣冷哼,俏脸绷得紧紧地,“我怎么从来不知这湖名为卸甲湖?”
光玉堂意味深长地笑笑,“你不知道的多了。”
童谣终于忍不住,低声喝道,像是压抑了许久,“三皇子,你可是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
光玉堂一张俊脸冷了下来,露出不容置疑的姿态,一身霸气也是油然而生,断然喝道,“我自然忘不了,倒是你,别忘了你要将傅玄歌牢牢掌控住!”
童谣怔住,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碎开,湖边又是起了风,吹得一股波光微微激荡,水花荡开,撞在一起,却不知为何,碎在她的心里。
眼睑微抬,童谣那双本是清冷的美目上兀得蒙上了一层迷蒙的雾气,睫毛微微颤着,像是压抑着什么,“你还是,爱上她了,对不对?”?
光玉堂也是一怔,璇即松身一叹,“童谣,你不该将我放得过重的。”
说完这句话,他也不待身旁的人再有反应,一踮脚,在假山石上借了个力,便隐没在无尽的夜色里。
湖仍是那湖,景仍是那般景,只是人不同,情自然不同。
“谭月筝。”
童谣轻轻叫了一句,这一声,却像是打开了她内心的某把枷锁,“你生于大富大贵之家,豆蔻年华便进选良娣,一生不曾奔波流离,为何要同我这苦命之人抢一个异国皇子?”
泪如雨下,童谣便是想止,也止不住。她曾经以为自己不惜一切,为了光玉堂荣登帝位背井离乡潜入嘉仪国皇宫,用这张还算清美的脸蛋用一具还算妖娆的躯体换的一些情报,一场大胜,这般努力,换来的会是自己荣归故国,常伴在光玉堂的身旁。
哪怕不为皇后妃子,哪怕只是为他执掌宫灯,点一炉香薰,只要能日日见到他,便也够了。
可如今看来,这都不能。
落泪良久,直到透了力,童谣软软地躺在湖边,月光本就清冷,却冷不过她眸中迸发的冷意,倏地,她忽然笑了,嘴角残留着几丝决然,“你既然让我不能如愿,我便让你万劫不复。”
小步走着的谭月筝自然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
她心里满满的都是疑惑,光玉堂为何要帮她,要怎么帮她?
她们不过初见几面,说过寥寥几句话而已,何来如此的深情厚谊?
“主子,小心水洼。”茯苓见谭月筝发着怔,马上就要迈进水洼了,急忙提醒。
谭月筝回过神,轻巧地避了过去,而后眉头又皱了起来,深深思索了片刻,“茯苓,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茯苓点点头,“那主子,我们要怎么办?”
谭月筝一张小脸上突然决然了起来,“找到陆三凡。”
茯苓闻言面露难色,“主子,这法子,等若没有啊。”
谭月筝娥眉轻蹙,“为何?”
“主子,您是没听过,这陆三凡也是个奇人呢。”
“怎么说?”
“这陆三凡一身画功,称得上是嘉仪一绝,但是这性格怪异,也是在王公贵族间有着诺大名声。他若不爽,纵然是皇上,也不会逼他去做什么。”
娥眉再蹙,谭月筝觉得事情越来越大条了,这件事不管是谁的手段,如今已经经她逼入绝路。
不管她如何挣扎,圣物被毁已是定居,这事一旦传到皇上耳里,凭她一个太子良娣的身份,未必可以保得住什么。
越想越是头痛,谭月筝只得轻抚额头,良久道了一句,“先回枕霞阁吧。”
翌日,宋月娥早早地便在丹凤殿候着,而且她分明用心打扮了。
左尚钏又是称身子抱恙,来不了了。搁在往常,宋月娥难免一怒,但今日她的心情像是出奇的好。
那是自然,按巧烟的消息而言,自己的计划已然完美实现。而谭月筝如今必然心急如焚,束手无策。
想到这里,她特意细描的丹凤美眸轻轻一眯,一束得意的冷光晃过。
“谭月筝,我看你,还能如何。”
可是不曾让她料到的是,谭月筝牵着袁素琴的柔胰,二人竟是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虽然吃惊,但宋月娥的面目上仍是不露分毫,抖抖宽大的纹丝袖袍,她款款起身,“二位妹妹,今日怎得这般开心?快坐快坐。”
谭月筝福身谢过,落了座便轻轻开口,“妹妹自然有好事。”
“哦,是吗?”宋月娥心下冷笑,但嘴角仍是迷人的翘起,“但我听闻太子之前存放在妹妹那里的《永寿天年》可是,毁了呢。”
此言一出,谭月筝嘴角微翘,真是急不可耐呢。
“姐姐那是听错了,毁掉的是我拿来练手的一幅画作,毕竟《永寿天年》何等珍贵,我岂会上来就绣。”
宋月娥一怔,心中陡然疑云重重。
“那这样说来,宫中那些侍婢太监都在乱说呢?”
谭月筝清秀的小脸神秘起来,微微俯着身子,压低声音说道,“那是我的疑兵之策。”
“哦?”这一句疑问竟是抬得过急,宋月娥都察觉出自己有些失态,赶忙轻咳了一下,“近日许久不曾出去透气,嗓子干了些。”
谭月筝将一双明眸的目光尽是放在自己如葱玉指上,玉指翻转,像是在细细观摩什么,看似不经意地道了一句,“可是最近天气无常,这般潮湿,姐姐怎么还会嗓子发干呢?”
这一句话,使得宋月娥身后的巧烟神色大变,谭月筝看似轻轻的一句话,竟是将松潮作用最为关键的一点说了出来。
她发现了什么?
虽然巧烟察觉失态,急忙扳回神色,但这一下,还是落在有心的茯苓眼中。
“哎呀,姐姐妹妹你们这是怎得了。怎么好好的打起哑谜来了。”袁素琴适时道了一句,缓和一下气氛,又娇笑连连,对着宋月娥神秘一笑,“姐姐你可知道,这宫中有人要陷害月筝妹妹呢。”
谭月筝面色一变,想要伸手去扯袁素琴的袖子。
但这一下,便落在宋月娥眼中,她当下神色肃穆起来,抢在谭月筝前说道,“袁妹妹你尽管说出来,谭妹妹若是真受了什么委屈,在这东宫之中,我还是可以为你们尽些薄力的。”
这一说,谭月筝更是不好去阻拦了。
袁素琴神色一喜,急忙开口,“这次圣上的《永寿天年》便是险些着了道。那日我们从姐姐这里离开,回去后便将那画忘在了轿上,待得取回来,隐隐觉得不对。”
宋月娥微皱眉头,有些愤怒一般,“怎么?被人动了手脚?”
“正是。那画上分明被撒了东西,事后我们寻了个太医院的熟识之人,他给我们出了一计。”
这下就连巧烟都是伸长了脖子。
“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先是将《永寿天年》恢复如初,又教我们另寻一画,假装中招。”
谭月筝像是索性也不拦着了,也是娇笑连连,“所以我放出了这疑兵之计,料想那人此刻正是极为得意。”
宋月娥听完,长长的指甲几乎刺进肉里,可她仍是眉头一舒,长出了口气,“那真是惊险。幸好两位妹妹冰雪玲珑,才能化险为夷。”
听到这里,茯苓却突然插了一句,“那是,幸好我家主子将画藏在抚月。。”
“大胆!”谭月筝突然大斥一句,“主子们说话,哪有你插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