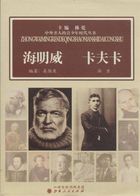我在崇实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曾给过我一种莫名的快乐。头几天,我们就动手制作彩色纸圈,排练唱歌,确实有一番节日气氛。小松树上缀满五光十色的灯泡,在我那孤寂的心灵里,添了不少喜悦。小耶稣在马槽里降生的故事也曾感动过我。他好像唤起过我的共鸣:他是个木匠的儿子,是在罗马霸权压迫下诞生成长的。《圣经》(尤其《旧约》)不少故事,像《创世记》中的约瑟,曾令我神往。《诗篇》、《箴言》和《雅歌》里那些抒情的诗句,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对爱的哲学的阐发,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最早对基督教的反感,并非来自它本身。我厌恶那位白天传基督教、晚上信佛的堂兄。进了洋学堂之后,我才发现,像他那样言行不一致、把宗教当饭碗的,大有人在。那所长老会学校的教务长和斋务长均有两副面孔:当着洋校长的面一套,背着是另一套;对阔学生一套,对穷的另一套。做礼拜时,他们满口“爱呀,爱”的,但除了自己,他们谁也不爱。
通过学习,后来我知道了从文学史、艺术史上看,基督教是从西亚到欧洲这一带人民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圣经》是希伯莱民族若干世纪积累下来的一部诗歌散文宝库。基督一生的事迹为但丁、达·芬奇乃至当代几百年来欧洲文学、绘画、音乐、雕刻大师们提供了重要题材。1517年马丁·路德给梵蒂冈贴的那张大字报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结束了中古的黑暗时代,导致了人类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耶稣本人真是位无产者。跟随他的门徒们也都是些打鱼、放羊、干力气活儿的。他也许还是反抗罗马帝国残暴统治的民族英雄。读到他把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商人们一下子从圣殿里赶出去那段,我感到痛快,觉得他很有些革命气魄。基督教曾使欧洲由野蛮走向文明,是西方人道主义的基础,尽管它也是多次战争的起因。
很不幸的是我早年接触的洋基督教徒,包括我十分敬爱的安娜堂嫂,无一例外地都是原教旨主义者。旅欧期间我才知道基督教徒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科学的昌兴,理性运动的推进,教会内也不断有人从各种角度在不同程度上造着反。有的扬弃了三位一体,也有的不再相信《圣经》里超自然的部分——如奇迹。然而我在旧中国的农村(仿佛是香河县)甚至还看到过一次神召会“作礼拜”。教堂院子里跪了几十个信徒,每个人面前摆了几块砖。信徒们祈祷时,就用头硬往砖头上撞,撞得青一块紫一块,以致鲜血淋漓。然后就像疯子般狂喊乱叫起来,说是在“讲万国方言”。
就我个人来说,能进崇实这个洋学堂,大大不同于呆在姑子庵里念《四书》。不论他们的主观意图如何,十九世纪以来教会在华办学,办医院,客观上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是起过一定作用的。然而不容否认,我在崇实所接受的宗教教育既是原教旨的,也是十足强迫性的。每天早晨要在学校作礼拜,星期天排队到二条礼拜堂;都先点名。我又像背“子曰学而”那样,背起《约翰福音》,背起《哥林多前书》来了。背不上来就挨板子。
牧师说,祷告时一定得闭上眼睛。我那时是个眼珠老在转的淘气鬼。越是逼我闭,我就越闭不住。班上像我那样的,还有好几个。我们不但不闭,还乘机挤眉弄眼。这可惹恼了老师。当牧师在台上领着祈祷的时候,他就在一排排学生中间转悠,看谁睁眼。抓住了,做完礼拜就罚在院子里站上几个钟头。然而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一走近,我们就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听到他的脚步声离远了,我们重新睁开。这是最初的一种反抗。
教会里有些做法,也使我气愤不已。
崇实有位女生,也是个孤儿,听说长得很秀气。有个仰慕她的男生给她去了封信。信她没接到,却给舍监拆开了。她根本不认识写信者,事情完全怪不得她。舍监却认为她犯了罪,并一连几天,用沾满肥皂的牙刷搓洗她的嘴和喉咙,刷得鲜血直流,说是替她洗涤罪愆!这事以及妙峰山所见所闻,使我觉得宗教讲的是爱,有时干得却十分残酷。
年纪大了些,问题考虑的就更多了。
做完礼拜,我们排队回学校,照例要穿过洋牧师们住的大院回学校。院子里是一幢幢两层洋房,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松木成行。家家门前都有专用的秋千和沙土地,经常有些金黄头发蓝眼珠的孩子们在玩耍。走过门前,总闻到香喷喷的肉味和奶味。阳台上摆满了盆花,厨师穿了洁白的制服,还雇有保姆和园丁,过的是与我们迥乎不同的阔绰生活。我回到堂兄家却只喝得上杂合面糊糊。我也有妈妈,但是她却得出去给人使唤,不能留在我身边。我想,倘若真有个神,他不该这么不公道,偏袒那些白皮肤的吧。
后来我又从政治和历史背景看宗教的来历了。没有十九世纪那些不平等条约,洋牧师能进来传教吗?都怪清朝腐败的皇帝和那些太监佞臣糊涂,订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基督教归根结蒂是跟在洋枪洋炮后头进来的。我在《皈依》那篇小说中,曾表达了自己对救世军的愤慨。在我眼里,传教的牧师同被传教的男女信徒之间,是一种强者与弱者的关系。1925年英国人在南京路屠杀中国工人学生之后,每当牧师在台上指着我们颤巍巍地说:“你们是有罪的人!”我心里就问:究竟是谁有罪呢?
基督教教义的中心是一个“爱”字。它还不仅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而是“如果你的敌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打”的爱。倘若这样,当初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逼中国赔款割地呢?他们报复起来跟不信教的一样凶狠啊!为什么偏偏在一个受尽欺凌的国家里。宣传这种他们自己根本不准备实行的奴才哲学呢?
我同三堂兄(也就是同“家庭”)终于闹翻了。他不知道那时候我已懂得了些反封建的道理。他逼我去当邮务生,说那是铁饭碗,要我挣钱养家。我听说邮务生成天坐在那里翻译国外邮件的地名,所以不愿干。他气哼哼地说:
“不然的话,就打折你两条腿!”
可是我那时已经不再是个温驯的受气包了。我造了他的反。我用红笔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长信,托支持我的四堂兄在一个远亲举办的婚宴上,当众宣读给所有的戚友听。记得信末写的是:
别了,你的雷霆。别了,你的棍子。我不但不会让你打折我的腿,我还要用它走自己的路。
就这样,我十四岁上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成为自己这只小船的主人了。
我开始注意起报纸后面的招聘广告了。我先考的是《世界日报》练习生,没考上。据说是嫌我个子矮。我继续留意,应征。终于考上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
北新书局那时在翠花胡同路北一个院子里。书局本身只占三间南屋,两间打通的是门市部,靠东一间是编辑部。老板李小峰和他的太太住在里院。书局只有一位编辑先生,就是现在语言研究所的袁家骅——1943年我们在英国牛津又见过面。这是五四运动后期带点同人性质的新型出版社,出过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江绍原、徐祖正的作品。鲁迅还为他们编了个刊物——《语丝》。
这是一家出版并代售许多新书的出版社,老板手里托着的却是一杆水烟袋。盖子突突地响,灰色的烟便由鼻孔里喷了出来。摆在他肘角的正是一只用得已经有些油亮了的算盘。他缓慢地抬起头来,在那动作中,像是带了不少严厉。然后。迎接我的,又是一张中年商人的脸,削长,尖瘦,布满了利欲的皱纹。
“来了啊,拿这稿子去校!”
于是,我走到靠墙的一张小方桌旁,对着一份陌生的工作坐了下来。我想他一定一面咝咝地吸着水烟,一面用眼睛偷看着我哪。那时我急得可什么也顾不到,我逐字对看着原稿(机械得几乎一点也捉不到字与字之间的意义),嗅着那使人头昏的油墨气味。随着那唏哩哗啦的算盘声,我额上的汗水簌簌地沿着腮帮流了下来。
如果把当时每天进出翠花胡同的文学界人物开列出来,也许会占那个时期半部文学史。那时周作人还为“三·一八”烈士写着挽联,同鲁迅一道笔诛女师大的学阀,兄弟二人(书局里分别称他们为“大先生”、“二先生”)在合编着《语丝》。1936年我在上海见到鲁迅先生时,曾问他可还认得我这个多次给他送过稿费和刊物的小徒弟。他定睛望了我好一阵,然后亲切地笑了起来。那时见的作家多了——除了冰心大姐,如今几乎全都早作了古。经常来的有大嗓门、连续喷着香烟的刘半农;细长身材、总穿着府绸大褂的章衣萍;最早写爱情小说《兰生弟日记》的徐祖正,《性史》的作者张竞生和哲理小说家冯文炳;还有江绍原、钱玄同……
练习生的工作当然就是打杂。有时给作家们送稿费,有时跑邮局。经常干的是校对:尤其《语丝》和多种图书。搞上一天,油墨气味常使我发昏。我尤其害怕送稿费。那么厚一叠子钞票,万一丢了我可怎么赔!每次都是请伙伴替我用手绢把钱绑在我的腕子上,这样好一路骑车死死盯住它。我去过多少趟八道湾周家,还特别喜欢去中剪子巷谢家,因为我同冰心的弟弟为楫在崇实从小同班同学。她收下钱并不马上让我走,总留我坐上一会儿,喝口水,亲切地问长问短的。
有一天,老板给了我一个新差使:到红楼北大图书馆去抄书。要求我:“不漏一个字,不错一个字,连标点符号也要一笔一划地不改样。”
这个差使不但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是极好的训练,也使我精读了一些作品。徐志摩译的《曼殊菲尔小说集》就是我一篇篇从《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抄下来的,那可以说是我最早精读的一部集子。
在海外,有人问起我受过哪些外国作家的影响,我的答复是:一个作家读他本国及外国的作品,就像一个人吃各种副食品:有蔬菜也有脂肪,有淀粉也有蛋白,有本土的也有舶来的(他的主食只能是他所经历的生活)。他把这些吃下去后,在胃里经过消化,产生热量。你不能断言这热量是来自哪样食品。对我来说,最早接触的外国作品就是那位新西兰女作家笔下的那些小故事。画面小,人物小,情节平凡。但它们曾使我时而感到无限欣悦,时而又感到深切的悲怆。
北新的门市部柜台上陈列的书籍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令我捧腹的《何典》,也有害我哭湿了枕头的《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喜欢C.F.女士的民间故事集《徐文长》,刘半农从巴黎图书馆抄来的《太平天国文件》也引起我的兴味。这些书,白天抽不出时间读,下班后照例可以选一两种带回公寓里去看。北新可以说是我的又一个课堂。在这里,我接触到“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各种思潮,也浅尝了一些文艺作品。思想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华林的《新英雄主义》。那薄薄一本书,我读了绝不止十遍。在读它之前,我脑子里净是些光宗耀祖、个人奋斗的思想。这本书谈到了比个人小圈子更高超的理想。现在回想起来,都谈得很模糊,很抽象,但它确曾领着我走入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我还贪婪地读过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曾把《国民公敌》最后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抄下来贴在墙上,作为我的座右铭。我的头脑那时是个大杂烩!
在北新干杂活的,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徒弟。我们年纪不相上下,工作内容也差不多。他们一个黑粗粗的,另一个白嫩嫩的。由于我是练习生,在待遇上就大不相同。徒弟晚上睡在办公室的长桌上,我则住在红楼对面的大兴公寓。我一个月五块钱,饭就和老板一家同桌而食。可徒弟要等我们吃饱了才准上桌。
记得第一天,那个面色黧黑的少年跑来招呼我去吃饭。我把校样放下,压上镇尺,才去就座。老板对我说:
“你只要好好干,生意兴隆了,会给你加钱。”
我只怯生生地提出了准许我晚上带回几本书去看的要求。老板含糊地答应了。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那招呼我吃饭的学徒却和比他矮小一点的伙伴一道在院里捆书册,及至我们放下箸,他们才被唤进来。老板剔着牙,晃晃悠悠地领头走了出来。两个徒弟用剩菜残饭填起肚皮。
我回头,看见那个粗壮的少年在狼吞虎咽,那肤色白皙的却尽对着屋角发愣。
“为什么不少吃点,多给他们留些呢?”隐隐像有个声音在责备我。
渐渐地,我对环境熟稔了。每天工作完了,总借回一本书,蜷在房里读。晚上有空也和伙伴谈谈天;由于年纪关系,我比较地和那两个徒弟接近些。这下子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那个“白徒弟”才十三岁,父亲死掉不久,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子。本来在一所高小读着书的,一场丧事后,学校的大门对他关闭了。家里以为这个行当高尚,就把他送来做学徒。但那个寡妇妈妈哪里舍得啊,三天两头地跑来书店看他,每次总在门洞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回到房里,“白徒弟”不是捧了一包点心,便是他妈亲手做的一双布鞋。再也没有比我的羡慕之情更难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