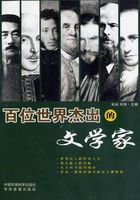这位老师每次进教室都满脸煞气,好像是横着闯进来的。他的脾气暴躁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干柴,一点就着。他靠的就是一把专打学生手心的板子。他脸上的麻粒总呈青紫色,几乎没见过他的笑容。当时我们用的课本是温德华氏作的。书挺厚,每本要一块多钱。每天上学我都小心翼翼地把那本书裹在蓝布包袱里,夹在腋下。
一天,我正走在东直门大街上,忽然迎面跑来一匹惊马,横冲直撞而来。我赶紧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迈沟的当儿,蓝布包袱散了。我慌忙把凌乱的书册拾起,晚上才发现,唉呀,“温德华”不见了。
好容易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他那本“温德华”放在两张小桌的当中,可那怎能逃掉讲台上那只目光炯炯的老鹰!两人合用一本书的情况很快被他发觉。老鹰就忽扇着翅膀扑了过来。几分钟后,我抚着红肿的手掌,淌着泪回到座位上。
老鹰叉着腰,在台上咆哮着:“哪天你不带书来,哪天我照样揍!”
刚好是月头交饭费的时候。当时每月的饭费是两块五毛钱。我苦苦哀求管膳务的老师让我只吃早晚两顿,用从中饭省下来的钱买了那本“温德华”。
于是,中午大家熙熙攘攘朝饭厅走的时候,我却独自踱到篮球场,在那里无精打采地投篮。有一天,高班一位教地理的贾老师从旁走过。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编造的鬼话,替我把饭费的差额补上,一定要我还是去吃全餐。
除了学校,我小时还上过另外一种课堂,那就是庙会。初一十五是东岳庙,七、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以及天桥、鼓楼后身。都是举行庙会的场所,也就是我的课堂。
那真是个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地方。走进庙门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这里有三尺长的大风筝——沙雁或是龙睛鱼,有串成朝珠一般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山里红;有香甜可口的“驴打滚”,也有一个大子儿一碗的豆汁;有粘破瓷器的鳔胶,也有能把生锈的器皿擦得锃亮的一包包粉末。一个角落是“动物园”——卖各种虫鱼禽鸟,毛兔松鼠;另一个角落是“植物园”——从各种奇花异草到一个小子儿一捆的“死不了”。还有算灵卦的,捏面人儿的。摔跤能手宝三和练十八般武艺的各路把式,都在这里大显身手。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蓝布篷底下围满一圈人的那些说书唱曲的。场子周围有一排板凳,那是给“正式”听众坐的。有两种人站在板凳后面,一种是打算听上两句就走开的,一坐上板凳再走就不那么便当了;一种是自知掏不出几个钱,不敢去坐。我就属于后一种观众。绰号“云里飞”的那位相声演员的机智多端,随口旁敲侧击,那是我最早接触的讽刺文学。评书快板、大鼓岔曲那丰富而生动的语言常使我听得着迷,归途不断回味。有一次听得出了神,竟然把身上穿着的布衫丢了,而且也说不出是给人扒去的,还是脱了拿在手里丢的。也难怪三堂兄狠揍了我一顿。
对我来说,那些曲艺比至圣先师的“子曰学而时习之”有意思多了。1963年,在出版社的一次晚会上,我竟然还唱得出一段岔曲——《风雨归舟》。1966年夏天那自然也成为罪状一条,说是同邓拓的风雨相呼应。然而中国的俗文学多了不起啊!短短那么一两百字,就衬着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描绘出老少两个渔人一天的生涯。有情有景,听得见冰雹的声响,看得见雨过天晴,挂在半空的一缕丹霞。
在庙会这个课堂里,我往往也是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演完一场,艺人照例拿着盘子或笸箩向观众打钱。我也偶尔从兜里摸得出一两个大子儿,一般情况下则只能站脚助威。看白戏的观众是不会受待见的,不是挨上几眼瞪,就是给赶走。好在庙会里棚子连棚子,处处是课堂。我时常从这一家又溜到另一家。那时候北京风沙可大啦!逛一趟庙会,回去就成了泥人。
我虽是北京人,可我不懂京戏,也不爱看。一则那时,戏馆子是阔人去的地方。由于穷,我没能接近京戏,白当了北京人。再则也还另有个原因。大约三四岁上,有个亲戚带我去过东安市场的吉祥。唱的什么自然早没印象了。倒是对场上提着长嘴壶沏茶的、卖糖果的很感兴趣;尤其使我眼花缭乱的是满场里飞着的雪白“手巾把儿”。可是正当肩上插了旗子、头上挺着长翎子的演员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举着刀枪在台上转悠时,忽然,观众席上也大打出手了。
原来那年头丘八老爷不但白看戏,戏院还得伺候得周到。一慢待了,就“砸戏馆子”。我那是头一回看戏,就碰上了。什么茶壶呀,茶碗呀,甚至板凳,都从楼上飞了下来。观众有哭喊的,也有哎哟的——大概砸在身上了——挤成一团。幸而我们的座位靠近窗户,那位亲戚赶紧把我抱上窗台,跟着他也蹿上来,把我抢出戏院。这当儿,向外逃的观众已经堵塞在戏院门口,呼天抢地。从那以后,我就同京戏没有了缘份。
1921年的一天,四堂兄带我去看一位姓孟罗的英国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西餐。事先,四堂兄教了我一通,还让我读了一本英文小册子《好礼貌》。他告诉我该怎样使用刀叉,一再嘱咐我,肉只能切碎了吃,可不准上手;刀不许碰嘴。那天我可紧张了。
主人是位牧师,十分和善。我用英语应对的也还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不晓得旁边盘子里的面包原来是可以用手捏的。我用刀一切,那个滚圆的小硬面包哧溜一下就滑到地上了。我急得满头大汗,抬头苦苦望着四堂兄,仿佛说:瞧,我照你嘱咐的做了,它不听话可怎么办!那晚我们还去东长安街一家电影院看了卓别林的《淘金记》。对我,那也是头一遭。看到银幕上甩着手杖的滑稽人跑来跑去,开心极了。
我不信鬼神,可小时又很迷信,而且惜命。小学毕业时,请来照相馆的用转镜照个全体师生相。事先我听人说,照相能够摄魂。照一回,会少活几年。照的那天,我盘腿坐在尽前边那排。转镜快转到我时,我忽然掉过身子,头朝里了。洗出来后,老师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
还有一回,冰心大姐的弟弟为楫请我乘电车:那时,北京刚有电车,是从北新桥通到东单。我们在北新桥头上搭的车。站在车首的司机叮叮当当地踩着铃驾驶着,十分有趣。突然,有个乘客自言自语道:“电这玩艺儿就是险。可千万别串电,一串,车上的人眼睛满瞎。”我听了,害起怕来,刚开到十二条那站就赶紧跳下去了。
我们班上有个既聪明又长得秀气的同学。他门门功课都是优等,每年运动会上,田径赛也一向跑第一名。忽然间,他缺席了,说是进了医院。过个时期,又听说双腿都锯掉了,原因是他父亲生活荒唐,时常嫖妓。后来我又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杨梅大疮患者的模型:鼻子、脸全糜烂了。这两件事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也使我后来在流浪生活中,不但自己不嫖,在接触有这种恶习的人时,也严加提防。
学校那时共有两座五层大楼。北楼是学生宿舍。冬天,暖气只能上到一二层,三楼就温吞吞的了。四五层楼冷得像冰窖。马斋务长(外号马猴)除了教职,还有个副业:贩狗出口。有些不那么阔的学生,倘若隔些日子奉献他一两条哈巴狗,倒也能邀到他的青睐。我是什么也贡献不出来的,每年照例被分在五层楼。恰好我又只有从妈妈那里继承过来的一条薄棉被,里面的棉絮早已滚成团团,大面积成了夹的。“暖”气管凉得不敢上手去摸,蜷缩在被窝里打哆嗦。所幸晚上熄灯以后,常有同学抱来大衣或棉袄,为我压在被子上。
在我早年生活中,宗教也曾给过我不少欢乐。至今,我仍然喜欢听古寺的钟声,圣诞节的歌曲。然而幼时宗教给予我心灵的主要不是慰藉,而是压迫、凌辱和创伤,因而它很早就引起我的怀疑和反抗。
五六岁上,家里抽冷子来了一位比我们更没有落子的姑姑。她没儿没女,又死了老伴儿,所以一进门就说:“投靠你们来了。”可是三堂兄那时正失业,家里靠典当度日,光凭亲属关系,这个姑姑是混不下去的。
不知怎么一来,她忽然有了资本,找到了一座靠山:她成了大狐仙的代理人。于是,家里谁有个灾病,就都由她来“治”了。她总烧上一炷香,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往碗里捏上一搓香灰,兑上清水,就是大狐仙赏的灵丹妙药了。这种香灰水我喝了不知多少碗。于是,她就由一个不受欢迎的穷亲戚,变为通身闪着灵光的活菩萨了。她不但能治病,还会卜吉凶。
她的地位稳固了,然而同她滚在一个炕上的我,可吓坏了。为了证明她同大狐仙有着一种特殊关系,她半夜里时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说是狐仙附了体。她一叫喊,我总觉得好像一个青面獠牙的家伙真的钻了进来,就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人贫困到一点没着落时,倘若又没有知识,就总要在人间以外找点依靠。闹了一阵子大狐仙,三堂兄又信起佛来了。对我,那是另一场灾难。
白天,我在洋学堂里死背《圣经》,傍晚回来,有时得跪在院里给各路神祇磕上几十个头。像姑姑那样靠神来发迹的人有的是。一个乞丐忽然倒在东直门外一座破庙里,数叨一阵,硬说菩萨在他身上显了圣。于是,四远传开了。失业的堂兄见了神就求,对这位乞丐少不得也要去巴结一番。于是,把我带上去烧香了。
小庙盖在一个小土丘上,本来冷清得很。这下子山墙上挂满了黄红布制成的匾,中间写着“诚则灵”一类的话,下款是善男信女的名字。我们好容易才从人缝里挤到佛案前,毕恭毕敬地往大香炉里插一炷香。叩完头才取得进殿拜见那位乞丐的资格。那家伙懒洋洋地斜躺在一个土炕上,估计他从来也没洗过澡,身上的肤色同土炕分不清了。
堂兄捅我一下,要我同他一道跪下来,把带来的饽饽匣子供到炕沿上。那乞丐真沉得住气!他连眼皮也不抬,只用他泥污的手掰了一块他吃剩下的苹果,赏给堂兄,堂兄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慌忙接了过来。然后他请乞丐向菩萨祈求,叫他早日找到一个职业。乞丐阴阳怪气地哼了一下,我们才站起来。回到家里,幸好他没让我分享那块沾着乞丐唾液的苹果。他没舍得。
在我同佛教打的交道中,比较有趣的是替堂兄上妙峰山还愿那趟。那是我第一次徒步长途旅行,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当时我大概还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端午节前后的一个大早,我就跟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上了路。他也去那里还愿,堂兄把我托付给他。我们从北新桥一直走到西直门,在门脸搭上一辆敞篷骡车。他把我抱上了车,自己跨在车沿上。车里早已坐了一些乘客。那时西直门外的马路两边是用大块青石铺成的,一路上骡车颠来颠去,不但屁股一个劲儿地在车板上磕碰,有时候似乎心脏都差点儿像枣核那样从嗓子眼儿里颠了出来。
在青龙桥下了车后,就朝西北走。老人指指远山告诉我,妙峰山就在那后边。一路都是土道,还穿过不少坟地。老人累了就咕咚一声,朝坟头上一倒。他掏出烟荷包抽上一袋的当儿,我就可以观赏四周的景物了。经过黑龙潭、温泉,擦黑才到山跟前的北安河。我们在一家店里打了尖,然后也像旁人那样买了一柄火把点着。抬头望去,沿山道弯弯曲曲是由火把连起来的一条长龙。山半腰有一道险路:窄窄的山道,下边黑洞洞的就是万仞悬崖。我说了声:“我怕!”旁边一个朝香人立刻申斥我说:“这孩子可别瞎说,只要虔诚,就不怕了。”
天快亮时,我们来到一个小山谷。进香人爬了一宿山,照例要在这里歇歇脚,把精神养过来,天明好去庙里进香。几家客栈伙计在蒙蒙亮中招徕着客人:“热炕大被窝,没虱子没臭虫。”——其实,两样都有,外加跳蚤。
老人把我带进一家客栈,炕角上已经躺了两个客人。我顺着炕沿爬上去,倚着一只腥臭腥臭的大枕头就睡着了。
妙峰山是由几座庙宇组成的,主庙并不大,但是烟火旺盛得老远就是白茫茫一片。每座庙似乎都代表一个行业。喜神庙挂了许多名伶送的匾。
回想那次朝香,我仿佛看到了宗教同艺术的联系。后来读到希腊史中有关奥林匹克那一段时,我马上联想到那次妙峰山之行。那可以说是华北民间艺术大会演。跑旱船的,踩高跷的。各剧种都有人挑着蒙了黄布的行套担子,代表黄河以北的各行各业去进香,沿途还举行着表演。那正是割完麦子的季节。农民把新的麦秸染成五颜六色,用来巧妙地编成草帽、灯笼和各种有趣的玩具。朝香人买来戴在头上,挂在身上,叫作“带福还家”。有些行业还许愿在山坳里搭粥棚,朝香人可以坐在板凳上歇歇脚,热腾腾喝碗施舍的小米粥。我的鞋磨了个洞,还有个许愿的鞋匠免费替我补好。
可是那次朝香我也看到宗教残酷的一面。来自远至山东、河南的善男信女,有的是替自己求福,有的则是替生重病的家人许愿而来。为了取悦神祇,表达虔诚,他们想尽办法来折磨自己。我看到有隔两三步就跪下磕个响头的——从老远老远就这么磕!还有孝子竟把自己打扮成一只乌龟,在炎日下一路爬行。膝盖磨破了,血肉模糊,似乎连骨头都露出来了。最可怕莫过于跳山涧的。那也是许的心愿:从庙后一个悬崖硬往下面乱石上纵身而跳。前几年美国一个教派几百人在南美集体自杀的惨举就使我忆起妙峰山朝香人跳山涧。信徒的“虔诚”就是正常人眼里的宗教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