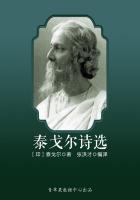教育理念
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诫大家:“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二〇〇八年岁末,“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北京大学因培养了三十五名亿万富豪问鼎榜首,浙江大学以二十三名位居第二,清华大学以二十二名排列第三。于是有人说:这是大学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如今的名牌大学,都成了“亿万富豪的摇篮”!
英国有谚云:“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同样的道理,如果出现“北京大学造了富,全国跟着跑”的局面,那么争当富豪就会成为年轻学子的理想,制造富豪也会成为大学的目标。这种情况,与“文革”期间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形成鲜明对照。
我以为,无论是培养工农兵还是制造富豪,都是对教育功能的严重扭曲!这一判断,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一九一七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学生因为受科举的影响,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获得当官的资格。于是他们往往对来自官场的兼职教员刻意讨好,对专职教员轻薄怠慢;与此同时,对应用专业很感兴趣,对基础专业十分冷淡。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诫大家:“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解释。
一九一八年四月,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把文、理两科称之为“学”,把法、商、医、工等科称之为“术”。因为前者以“研究真理”为天职,后者以“直接应用”为目的,所以他认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章还说,基于这一原因,他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大学令》中明确规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遗憾的是,由于“国人重术而轻学”,再加上“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所以即便是文理两科的学生,也会舍本逐末。
同年十一月,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之所以把研究学术视为大学的天职,并不断提醒大家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显然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
第一,学术是民族精神的寄托、社会进步的希望。
一九一九年,蔡元培的助手和继任者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中说:中国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就好比一群羊——“羊肥了,牧民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政治,即民权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平才有保障。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就是因为他们在明治维新中把牧民政治改成了平民政治。这说明社会进步除了物质改善外,更需要精神改良。因此蒋梦麟强调:“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大学不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把培养富豪作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
第二,学术是个人自立和国家富强的根本。
一九二九年,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参加了当年的毕业典礼。他对同学们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研究学问,就难成大器。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始终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首先要每一个人自立。个人要自立,自古以来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研究学问!他的这种观点坚持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他还在许多场合对青少年讲过类似的话。
第三,研究学术是追求真理、辨别是非的必由之路。
与上述三位相比,竺可桢也持有同样理念。一九三六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那年五月,他在就职典礼上批评了只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格培养的倾向之后,又明确指出:“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他还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如今的大学生被讥为有知识没文化、有教育没教养,究其原因,与他们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关。
近年来排行榜已经泛滥成灾。“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问世后,还有许多大学排行榜纷纷出笼。这就提醒我们,大学究竟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还是把造富与排行作为目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如此下去,所谓建立和谐社会就会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