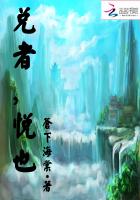被外面一阵接一阵的歇斯底里的哭叫惊醒之后,锡尔瓦揉揉肿了的眼睛坐了起来,看见莎弗朗尼亚睁着眼睛躺在那儿,就随口问道:“你也醒了?”
“他妈这个哭法谁睡得着?”
“那咱们起来吧?”
“可我又想,我现在阔了,我才不想像过去一样起那么早呢!”
锡尔瓦苦笑了一下,说:“外面到底出什么事了,要不要去看看?”
“不去。旁边人家打老婆呢,没什么好看的。”
“打老婆?”
“哦,你们家里大概是不打吧。”
“为什么要打?还打这么厉害?!”
“这事儿谁知道啊?!为什么不行呀?拌嘴了,喝多了,活干坏了,偷汉子了,弄丢钱了,或者就是闲着没事打着高兴……”
“快别说了!”锡尔瓦听到偷汉子那句就听不下去了。她检查了一下两腿的皮肤,重新躺下,躺了没多久又坐起来对莎弗朗尼亚说:“哭得这么厉害,不会出什么事吧,要不要去看看?万一……”
“万一了也是她的命!你都要跟我走一条路了,还想着去救人吗?”莎弗朗尼亚不耐烦地说。本来就毛躁的头发被她翻来覆去弄得更蓬乱了,她拿枕头捂住耳朵,说:“千万别去管别人家务事!没人领情。唉,打老婆的这短命的干嘛起这么早啊!”
锡尔瓦怔怔地坐在原地,听着外面的哭喊一阵阵低下去又高上来。
外面的哭声终于渐渐停了,又到了商旅收拾东西纷纷上路的时间,这阵噪音也停了之后,本想着能睡一觉,后背又有一处痒起来,躺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锡尔瓦坐起来伸手抓挠。听着自己指甲刮擦皮肤的声音,她觉得现在也终于明白什么叫斯文扫地。在外面奔波了三天,还没地方洗澡,不堪入目的茅厕她已经忍了,洗澡越想越觉得是个大难题。莎弗朗尼亚在旁边说:“挠得这么过瘾?听得我都觉得身上痒了!”
锡尔瓦赶紧抽出手,红着脸说:“别说了,我已经觉得够丢人的了!”
莎弗朗尼亚支起身子,说:“丢人?不是吧?!你们有钱小姐都不抓痒的吗?!你们是有什么秘方从来不痒?”
锡尔瓦没好气地回答:“当然痒得少!”
“那痒起来呢?”
“在自己家里没人的时候当然也抓。”
“有人的时候呢?比如在饭桌上?”
“当然得忍着啊!”
莎弗朗尼亚倒在枕头上吃吃笑起来,说:“还得忍着,我要是发了财,还真受不得这份辛苦啊!”说着伸手去搔头,说:“趁着我还没发财,赶紧挠几把,成了有钱人就不让挠痒了,哈哈哈哈哈。哎,昨天去了个好地方,今天去哪儿?”
“你有哪里要去吗?”
“我听你的啊!”
“我想哪里也别去,我腿上还没好。”
“细皮嫩肉的,活该!等把皮都磨糙了就好了,没别的办法。”
“今天先让我歇一天吧!”
“懒蛋!不准歇着,我还在躲人呢,得继续赶路!”莎弗朗尼亚爬起来凑到锡尔瓦耳边低声说:“你说咱们这些东西能卖多少钱啊?”
“当金子卖虽然也不少,但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古董。遇上识货的人,一个小东西值的钱绝对比打它用的金子值钱。”
“那还是先操心那张兔子皮吧!”莎弗朗尼亚突然恢复了正常的声音,把锡尔瓦吓了一跳。莎弗朗尼亚又躺回自己的位置,锡尔瓦笑着说:“还说我懒,你不也是赖着不想起来吗?”刚说完就隔着被子被蹬了一脚。
两人又迷糊了一阵醒来之后,莎弗朗尼亚把那堆金银器都轻轻排在地上,仔细地对着灯光看,把完好些的放在一边,把烟熏得厉害的、镶嵌的宝石脱落了的放在另一边,锡尔瓦明白她的用意,点了点头。然后两人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包裹里,离开了旅店。
骑上马走到路上,莎弗朗尼亚突然小声说:“你在前面走,让你往哪儿你往哪儿,啥也别问!”说完就勒住了马。锡尔瓦回头困惑地看了她一眼,还是按她说的拍了拍马屁股,赶在了前面。在小镇狭窄的小路上左拐右拐一阵之后,锡尔瓦忍不住回头问:“我们不是在原地兜圈子吗?”“闭嘴,只管走!”莎弗朗尼亚呲牙咧嘴地向她低声命令道。她只好回过头去,驱赶着马继续往前。
“停下,就是这儿了。”听了莎弗朗尼亚的命令,锡尔瓦望着狭窄凋敝的胡同,疑惑不解地从马上下来,跟着莎弗朗尼亚的指挥把马牵进旁边的一扇虚掩着的柴门,里面倒是一个挺空旷的院子。莎弗朗尼亚把马拴好,对着锡尔瓦做了一个别出声的动作,自己回身向院门轻手轻脚地走去。她在破木板拼成的篱笆边屏息凝神地猫了一会,突然一脚把门踹开。外面立即传出一声惨叫,莎弗朗尼亚举起马鞭就朝那里抽去。
“好家伙,跟得够紧的啊!”听见莎弗朗尼亚骂起来,锡尔瓦大吃一惊,赶紧跑到门边,看见莎弗朗尼亚对着蜷缩在地上的一个人连着狠狠抽了好几鞭,还踢了一脚。地上的那个人只躲闪,不说话。莎弗朗尼亚朝旁边吐了一口唾沫,又对着他狠狠踢了一脚,说:“还不快滚?!”那个人忙不迭地爬起来,还没站稳,莎弗朗尼亚劈头又是一鞭。
等那个连滚带爬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锡尔瓦终于松了口气,问:“是在客店偷听我们房间说话了吗?可是他也没做什么,你何必……”
“那你还想等他做什么?在这儿把咱俩杀了?跟着咱们到下一个住处,半夜来房间里偷?记住咱们在哪儿,回去带着同伙一起来抢?”莎弗朗尼亚冷笑道,“这还是看了你的面子,要不是你在这儿我有顾忌,我直接一刀砍了他。要是连这点儿都看不得的话,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做大小姐吧。”
“那你又何必有顾忌呢?想砍就砍呗。”
“我怎么就相信你不会在这里跟我嚷嚷起来,过后再偷摸去告官啊。走吧,甩掉了尾巴就方便去该去的地方了。”莎弗朗尼亚走上前牵起马缰绳,回头用马鞭指着锡尔瓦说:“说实话,你刚才要是敢跟我说一句‘你怎么这么狠心?!你怎么能这么做?!’的话,我连你一块揍一顿!”
锡尔瓦跟在莎弗朗尼亚身后走出逼仄的小巷,不时提心吊胆地看看身后。她的确觉得莎弗朗尼亚刚才过于粗鲁和狠毒,但是加斯帕堡仆人偷东西的那一晚,自己明明想都没想,也是这么做的。第二天讲的那些理由几乎全是过后才想到的,事发当时,她只对那两个人充满恨意。
走到大路上,就可以快马加鞭跑起来了,莎弗朗尼亚说要找地方卖金银器,得到大些的市镇去。锡尔瓦早晨打包时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这些器皿上都没有自己家族的标记,应该可以卖。
太阳下山,莎弗朗尼亚又带她在第三家乱糟糟的小旅馆住下。她如释重负地躺在破铺板上,皮肤擦伤的疼痛丝毫没有减轻,可能必须要忍过这一个阶段吧。
半夜里,她刚睡着没一会,突然听见外面阵阵犬吠。凝神一听,那中气十足的低沉吠声像是狮头,她一骨碌坐起来抓起衣服开始套。被她吵醒的莎弗朗尼亚翻过身来烦躁地问:“狗叫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家的狗训过,没有大事不会乱叫。”她胡乱蹬上靴子跌跌撞撞奔下楼去,看见一个人想去解拴狮头的绳子,狮头正乱跳乱叫不让他近前。
“你干什么动我的狗?”那人吓了一跳,猛然回过头来。看着她呆站了片刻,突然对她一笑。锡尔瓦被这笑容弄慌了神,紧张地盯着她,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原来是这位姑娘的狗,我就是想看看。好了,我不动它了。”那人走到灯影里,看起来还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他若无其事地把两手插在衣兜里,晃晃悠悠向旅馆那边走去,贴着她身边走过去还笑了一声。锡尔瓦突然觉得全身一阵冰冷。
过了好一会,狮头平静下来了她才敢回头看,发现披头散发、衣冠不整的莎弗朗尼亚手握钢刀站在她身后。原来是因为这个,那个人才乖乖走了。她叹了口气,说:“谢谢你。”
“****祖宗,这一天事真多!”莎弗朗尼亚从后背上甩下一个大包丢在地上,说:“上去换你拿着!”
“这是!你怎么把行李带下来了?!”
“万一是调虎离山呢?重要东西当然不能离身!”
让狮头卧在房间门口地上,锡尔瓦放下大包,一下子瘫倒在床上。“怎么会有人偷狗呢?”
“你这条狗是纯种,偷去卖给你这样的有钱人家能卖不少呢。你刚才没看地上,他本来丢了做过手脚的东西给它吃。幸亏你这狗训得好,不乱吃东西,他才冒险硬上去解绳子的。你也真是,空着手就跑下去了,万一下面不是一个人是三个呢?”莎弗朗尼亚踢掉鞋子就钻进了被窝。
锡尔瓦把捂在脸上的手拿下来,说:“真的,莎弗朗尼亚,请你教我在外面生活需要的一切吧!”
“经过这么一天你还没改变主意?唉,你是从没出过门,遇见事情还不知道害怕啊!先睡吧,夜里警醒点。镇子大了,各色人都多。”莎弗朗尼亚吹熄了灯。
殴打妻子的丈夫、跟踪者、奸商、盗贼……还有什么?她觉得自己的心像是一颗刚剥出来的熟鸡蛋滚到了坑坑洼洼的沙地里。也许要习惯这种生活,心也要像皮肤一样被渐渐打磨粗糙吧。她又想起了弟弟,即使走的都是大路,还有官吏接应,但是一路上也会有不少危险吧。自己出了城堡几乎就没离开过家里的马车,怎么有资格去责怪他懦弱。她拉上来被子盖着头,又赶紧拉下去,放弃了再哭一场的想法。但是家人一旦出现在她脑海里,一时半会走不掉。如果弟弟还在,他也会渐渐变成一个像父亲一样威武的堡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