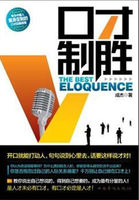已过了晌午,鹅毛大雪飘飘洒洒,自乌压压的半空中飘落下来,似天地间垂下的一道雪帘,挡了视线,瞧不清楚十步之外的景物,今日着实不是个赏梅的好日子。
“今日的雪下得好大,哈哈。”那紫衫公子搓着手,生硬地岔开话题,干笑两声,便再没了下文。
阮思虞也觉着有些不对之处,悄悄掀开银狐披风一角,歪着脑袋偷瞄一眼,才见外面站着那人果真不是陈锦瑄,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便将还套在脖子上未解下的丝帕扯上去蒙住半张脸,大大方方地从夏世子披风下钻出来,在一旁肯定道:“你真的是认错人了……”
说完,见夏世子仍然还抱着几分疑虑态度,便将徐妈妈也给拉了过来:“不信你问徐妈妈,真的是你认错人了!”
“哦,这样啊,今日风雪果然有些大。”夏世子黑曜石般的瞳仁转了两转,背转身子,望向墙角那一株老梅树。
陈锦年赶紧冲那本打算过来打招呼的紫衫公子使个眼色,抬臂做了个‘请’的手势。
那人急忙冲他拱手施了一礼致谢,一撩袍子,急匆匆的走了。
阮思虞咬着唇,定睛望向一旁佯作赏梅的夏世子脸上那双漂亮的眼,轻声问:“世子,你的眼,不碍事吧?”
一转背就能认错了人,这得是七老八十的人才有的症状……
今日风雪虽说确实大了些,但方才那公子可是走到了夏世子面前的,只差面贴面了,夏世子却还能将他错认成了陈锦瑄,此等眼力,着实让人无语。
夏世子正等着有人能问他这句话,当下以袖掩面咳了一声,脸不红心不跳地解释道:“是这样的,前几年我随父出征,去西南打蛮夷,双眼不慎受了刀伤,落下了点小毛病。”
夏世子这双眼确实受过伤,但只是被割伤了眼皮而已,他那一双眼也确实有点小毛病,准确的来说,是脑子里有点小毛病,能轻易背下来几万字的兵书,却记不住人的长相……
从前随父出征时,身边的几个副将经常被他认错,闹出不少乌龙来,后来,乐安王悄悄想了个办法,命令几位副将每人系一条不同颜色的领巾在脖子上,方便夏世子能准确认出他们来。
是以,在人际交往方面,夏世子从不主动与人打招呼,京中子弟时常在背后议论,道他高冷,迎面相逢也做视而不见,态度极其高傲,其实不然,夏世子只是怕认错了人闹笑话而已。
陈锦年听了他的解释,敬佩感油然而生,对这位一面之缘的‘大哥’瞬间好感倍增,当即抱拳,道:“世子赤胆忠心,为保一方太平殚精力竭,请受锦年一拜。”
看惯了太多京中一无是处的纨绔,乍一见到这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英雄,陈锦年心里感概万千,一席话说完,便郑重地向夏世子鞠了一躬。
“身为男儿,本就该保家卫国,二公子这大礼却未免也太重了些。”夏世子淡笑道,单手扶起陈锦年。
“锦年平生最敬佩的便是从军之人,抛头颅,洒热血,再隆重的礼仪世子也受得起。世子,将来若西南战火重燃,请收下锦年到你军中做个亲兵……”
两人愈说愈投机,阮思虞在一旁插不上话,只好当个认真的听众。
从二人的谈话中不难听出,当年‘松林三结义’后,夏世子的父亲乐安候便被天子派去西南平乱,为表决心,乐安候将家眷全部带到西南,抱着不评乱不回京的决心,历时十余年,西南一带才逐渐太平下来,天子龙颜大悦,封夏世子的父亲乐安候为乐安王,并将西南一带赐给乐安王做封地,世袭罔替。
乐安王与天子乃同母所出,扶兄上位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如今边关太平,天子想念胞弟,便在京城重新建了一座王府,每年年关,乐安王父子便会来京小住,过完年后才回封地去。
适才,阮思虞还想着说这结拜大哥怎么结拜就不见了人,莫非是年少无知,当做玩过家家的?却原来,是结拜完便随着父亲上战场去了……辗转十年,白驹过隙,她和陈锦年早已经忘记了当年的事,唯独这位‘大哥’却还记得。
阮思虞却有个疑问,抬眸望向正和陈锦年交谈的夏世子那双长睫上沾了几朵小雪花的眼,心说他有眼疾,辨不清人的样貌,适才却又是如何认出自己和陈锦年,记起当年结义的事呢?
陈锦年也正好心存疑惑,替阮思虞问了出来:“世子,十载已过,我有些好奇,方才你是如何一眼就认出她是当年苦竹寺后山女娃呢?”
夏世子唇角上扬,噙着抹意味不明的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垂眸往陈锦年与阮思虞二人的腰间各自扫了一眼。
阮思虞低头往自己腰带上看了一眼,瞬间明白过来:玉佩!
当年的她刻意想在宴会上表现一番,大冬天里穿着薄纱大跳西域的胡姬舞,即便夏世子曾来赴会,没有玉佩,夏世子也认不出她,也自然的想不起幼时的事情来。而今日她一袭素衣出席,自然不好佩那些花里胡哨的首饰,便从妆台匣子里翻出了一块质地通透的羊脂白玉来,随手系在了腰带上,而陈锦年的腰带上也正好戴着相同的另一枚玉佩。
二人对视一眼,恍然大悟,心说夏世子记不住人脸,记物件的记性却还不错。
隆冬的天昼短夜长,雪越下越大,不过才申时末,天色却已逐渐暗淡下来,前来赴会的宾客们正陆陆续续离开,徐妈妈望了望暗沉的天,上前催促阮思虞去同刘氏母女会合,若是去得晚了,刘氏少不得要教训人。
阮思虞点点头,与两人道别,准备去同刘氏母女会合。
陈锦年担心她认不得路,便自告奋勇道:“世子,我去送送她。”
“正好,我也该回去了,你顺便也送送我吧。”夏世子在一旁笑道:“我这人吧,其实最厌烦这种场合,今日本不愿来的,若不是我老爹将我打出门来赴会的话,也不会与你二人重逢,总算是不虚此行,回去该得给老头子敬杯酒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