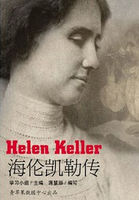我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云庄的各个角落,庄里的人一脸疑惑地望着我,不知道我究竟要干什么。
云庄只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我在这里跟着爹娘住了二十多年,却始终不知道这里住了多少人。在一个红霞满天的黄昏,当祖父咳嗽着拄着拐杖从那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走出来问我现在庄里最老的那个人是谁时,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夕阳的最后一抹光线透过窗的缝隙照在祖父那张斑驳的脸上,我仿佛看见父亲操着熟练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刻在光滑的木头上,划出一道道沟壑纵横的痕迹。
我心底疑惑着,祖父这是怎么了。娘一直说祖父早就患了老年痴呆症,叫我少搭理他。只是父亲一直认为祖父脑子比往年更加清醒。祖父不加辩说,沉默不已。
祖父死死地盯着我说,儿,你能告诉我现在云庄最老的人是谁吗?“我是达儿,是你的孙子。”我有点相信母亲的话了。幽暗的屋子里,我看了祖父一眼,然后飞快地跑出屋去。转身,祖父苍茫的眼神落进我眼底。接下来的日子,祖父一碰见我就问我这个问题。祖父始终没有去问爹和娘,他是把我当成他的儿了。
在一个落雨的深夜,当我梦见祖父掐着我的脖子大喊着那个一直困惑他的问题时,我最终决定帮祖父解决这个问题。
次日顶着烈日,我匆匆往几十里之外的乡政府跑去,一路的风尘扬起来模糊了我的脸,而我的心却愈加澄澈起来。我想我一回来,就能给祖父一个满意的答案。
几个小时后,当我满脸兴奋地告诉祖父现在云庄最老的那个人是村尾的老王时,祖父却一脸凄然地望着我说,老王去年就死了。去年就死了?我一低头,忽然想起去年自己爬火车跨越云庄而后漂向城市的事。当我带着满身的汗水再次跑进乡政府的大门,适才接待我的那个女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你到底烦不烦,这些资料都是五年前的,早过时了。
我茫然地望了望天,而后一脸沮丧地往回走,天上的太阳照在我身上,不时变幻着我的影子,时长时短。
祖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我一脸颓丧的模样,张了张嘴,便踩着高低不平地脚步进屋了。
次日我便马不停蹄地穿梭在云庄的大街小巷,谎称自己是乡里新派来普查人口的。村头的老张一听,疑惑地打量了我一眼,然后从落满灰尘的柜子底层翻出半新半旧的户口本递给我。接过小本本,我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蹩脚的字。望着这些陌生的名字,一张张熟悉的脸开始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拿着抄着名字的本本走在云庄满是灰尘的黄泥路上,无聊时我就跟那些名字玩。我粗糙的小指头一指在一个陌生的名字上,眼前便出现一张活灵活现的脸,时而朝我微笑时而朝我哭泣。说到底,巴掌大的云庄,那些人那些事,我大都见过并经历过。只是有些脸逐渐模糊。
我想为了这次能给祖父一个圆满的答案,得确保出现在小本本上的人都是活着的。当我走进小红家时竟发现自己双腿有点颤抖,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曾经暗恋多年并在一个深夜忍耐不住内心的饥饿非礼过的小红,而今依然满是喜欢。正抱着小孩的小红一脸冷淡地把户口本扔给我。抄写的过程中,小红的家人陆续回来了。一股诱人的菜香窜进我鼻子深处。
望着小红一脸的冷淡,我想我得赶紧走了。“上面的人,都还活着吧?”我支吾着还是问了句。小红随手把一旁的凳子朝我扔了过来,一脸愤怒。你眼瞎了是不是?小红丈夫紧握着拳头,一脸哀伤地望了弄堂上摆着的牌位一眼。我忐忑地跑出来,小红的那句“挨千刀的,你这是往我心上撒盐啊!”还是追上来深深地扎在我心上。
小红的母亲是在前年的那个冬天被抬上山头的,那个我远离云庄闯荡城市年头,没想到成了云庄的本命年。
一个星期后,当我满脸汗水,紧握着厚厚的落满风尘的本子一脸严肃地告诉祖父云庄最老的人是老屠夫李大爷时,祖父终于露出了浅浅的笑容。我始终不知道祖父笑容背后藏着什么深意。
一个星期后,当年余90的老屠夫蹬腿而去的消息传到祖父耳里时,祖父又拄着拐杖一脸急切地跑来问我现在云庄最老的人是谁,祖父急切的眼神指引着我快速地找出了他要的答案。“是凤娇嫂,以前骂我家骂得最厉害的那个。”我解释着说。祖父微微点了点头,便出去了,拐杖落在地上发出沉沉的声音,仿佛一个人的叹息。
晚上,辗转难眠,抱着本子,一遍遍地翻看完,我禁不住颤抖起来。祖父是云庄第三个最老的人。一个星期的奔波,得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想着祖父那张幽深的脸,我忽然若有所悟。
那几张薄薄的纸在深夜月光的映照下,忽然变得沉重无比起来。
年底凤娇嫂逝世时,祖父没有急切地问我。望着祖父,我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祖父依然缓缓地拄着那根拐杖在门探望着。只是,祖父偶尔会和我说说话,聊聊庄里发生的事情。祖父拐杖落地的声音为何变得从容均匀起来,我抓破了脑子,始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祖父拄着拐杖缓缓翻过一个年槛,而这年一个雪花飘飞的夜晚,祖父却悄无声息地走了。
戴孝,下葬。
我跪在祖父的墓地上,擦起一根火柴,把那个小本本点燃成灰。在灰烬里,我始终无法挥去爹和娘以及自己在那个小本本上的位置。
我不知道,那几张我花了一个星期弄出的小本本竟成了整个云庄的生死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