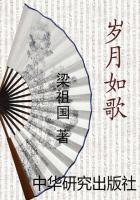近几年想念母亲的情绪与日俱增。积攒多了,夜里就老做噩梦。梦见那些最怕发生,醒后并未发生,又担心万一发生而不敢说出的不吉利事,引得心里直发毛。
母亲生于中国改朝换代的年代。时代给了她太多的苦难、灾荒和坎坷。生下我以后,父亲和她共同背着我和苦难生活的重负在整个民族生与死、血与火较量的夹缝中跌跌撞撞地谋求生存,建立家业。新中国成立之后,炮火刚刚隐去,硝烟尚未散尽,又含辛茹苦地呵护着我和弟弟在弹痕累累、疮痍重重的大地上寻求新的人生之路。为此几乎筋疲力尽的双亲不敢喘息,继续榨尽血汗供我们上中学、上大学……父亲过早去世,更加重了母亲的负担,但心力交瘁的她没有向命运屈服,更挺直了腰板朝前走……
母亲给我的是海洋,我回报给她的只是杯水。
时间一晃,我也提前退休了。送别座谈会上众人用近乎“盖棺论定”的溢美之词概括我的一生,使我感到好像是为我开追悼会。幸亏大家都要表达一下“健康长寿”、“保持晚节”之类的祝愿,这才使我又从“棺材”里“还阳”,意识到我不是死去,而是老了。
这种以前感到颇为遥远,眼下似乎突如其来的“老”,很现实地撞击到母亲的“更老”,使我好像隐约听到母亲桑榆晚景的尾声,回家看望她老人家的念头更超常地膨胀起来。
扑进家门,我宛如归巢的乳燕,亲切温馨之感直透骨髓。看到母亲老而无恙,悬着的心有如伞兵突然着陆了。晚上,睡在母亲身旁,突然感到自己小了几十岁。母亲轻轻抚摸我头上“马鬃(小辫)”的亲昵,责备我“蔫捣”行为的嗔怒,油灯下为我缝补旧衣的专注,依依送我远行的深情……都争先恐后地从岁月底层泛起挤到眼前,来印证我往日的身份。
母亲照例又念叨了:“你身体常出毛病,前几年才动过手术,最近又住了一次医院,再不能大意了,要自己照护自己。孩子们都大了,不要为他们操心劳神了,现在是他们服侍你的时候了……”
夜很静,月很明。母亲的话如深山淙淙清泉,澄澈而响亮,字字句句含着她异常执著又不张扬的母爱。
我怕她说多了劳累,就再不应声,诱她入睡。她果然中了我的计,一会儿就自言自语地说:“岁数不饶人,路上累了,睡着了……”很快,那平静匀称的呼吸声又向我报告了她睡熟的消息。我猜得出她脸上定然挂满微笑,那是她看到为之担心的儿子“完璧归赵”后放心的笑。
然而我却久久不能入睡。
临走那天,天刚麻麻亮,母亲就轻手轻脚摸索着起了床,没开灯就去生火。我被惊醒后问:“妈,这么早生火干啥?”
“你不是一早要坐车走吗?我给你做点饭……”
我的心一颤,忙起来劝阻:“妈,你歇着,我早不该你‘服侍’了,再说,两个多小时的路,早饭前就到了,用不着吃什么……”
母亲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十分固执,十分专心地用她那双饱经风霜的手颤抖着给我煮了荷包蛋,盛在碗里……这双手忙家务、干农活、扼住命运的咽喉,编织全家人的理想,曾经那样灵活有力。由它操作的纺车和机杼声经常柔柔地悠扬在我童年的梦中,伴我进入青年;现在,这双绣过花、织过布、扭转过家庭厄境的手,已经皱纹纵横、青筋隆结、寿斑重重、抖抖索索,却执拗地为她鬓发斑白的儿子做饭,并且不放心地叮咛:“人是铁,饭是钢,上了年纪更要在吃喝上调理……慢点喝,保护好肠胃,你小时候吃饭狼吞虎咽,不管冷热直往肚子里倒。如今到出毛病的岁数了,要自己照护自己……”
临走时,母亲站在门口,用我几十年最熟悉的目光送我,任微风轻抚她稀疏的银发。她显然苍老多了,再也没有力气一程一程地送我出村了,只是不停地叮嘱:“上了车别靠窗户,当心受风,靠前点坐,后边颠……”
每次回家看望母亲,得到的都是厚重的母爱,惹得我鼻酸喉哽,压得我难于喘气。
我恩重如山的母亲啊!
原载《山西老年》2000年2期34页
获2004年山西省企业界书画写作大赛优秀奖
收入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出版的《永恒的母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