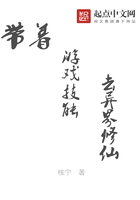仪华殿中,鸦雀无声。
太监宫女们早已被屏退,他们巴不得闭上耳朵,免得又从零碎不成句的密言暗语中听出惊天的阴谋,莫名其妙掉了脑袋。
储向歌趴在案上,抽噎难已,泪水晕化红妆,宛若日斜时分游离九天的霞光。
“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向歌嗔怒:“表姐心忒坏了,都这个时候了,还要引经据典地讽刺我被皇上抛弃!”
魏鹤的面孔上永远蒙覆着一层无缘无由的不屑。“娘娘现在悔不当初了?”
“表姐,你是我们家族之人,怎能胳膊肘向外拐?我确实后悔,后悔没有早些动手!原本胜券在握,谁料顷刻间局势反转。”向歌支起身子,凌空指着异苑方位,“那个沈司言,耍起手段来真够狠的。”
魏鹤徐徐摇起头,说道:“狠?谬也,她只不过是被逼急了。我与沈司言攀谈过两句,隐约觉得她是个进退有度之人。”
“表姐又为她说话!”向歌恼火,拾起一只茶盅就要掷地。
魏鹤也不拦,眉目间飘忽着蔑视之情。“娘娘如此方寸大乱,可见是怕她了。”
储嫔从鼻孔里出气,高声说道:“本宫怕她?魏司记,你察言观色的能力也不过如此嘛,以后还想在宫中生存下去吗?!”
“娘娘息怒,”魏鹤没有半点儿惶惧,“其实,您也该怕她——不对您的敌人怀敬畏心,怎能将她打击地永无翻身之日呢?”
向歌听闻此话,当下转怒为喜。“表姐这么说,是否有意铲除沈司言?”
魏鹤抬眼,平淡言说:“她还没有资格被当作直接目标。依我所见,今儿这趟火是别人撺掇起来的,沈司言只不过受到提点。”
“是谁?”向歌急忙问,又霎那想通,“崔明止!一定是这个老尚宫!我上午在耕熹殿请旨惩罚沈司言,这个老太婆就在一边听着,她还能不为自己徒弟着想吗?崔尚宫,你都七老八十了还要作妖,妄图和本宫斗法,简直自取灭亡!”
魏鹤露出古怪笑容,但她很快举袖遮面,掩盖住了。
“关于对付崔尚宫,表姐有什么好点子吗?”储嫔期冀地看着她。
魏鹤放下袖子,回答道:“法子慢慢想,总会有的,不过,崔明止一旦失势,尚宫局恐会动荡。中宫无主,太后、太皇太后又不稀罕管这些事,娘娘便责无旁贷了,万一有刺头儿添乱,您管理尚宫局有疏忽,岂不罔送英名?”
“这没什么好担忧的,”储向歌抱起魏鹤一条胳膊,笑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届时我向皇上推举你为尚宫,有表姐帮衬我,定当诸事协调。”
魏鹤轻咳两声,眼角上扬。“娘娘现下不要再为沈司言一事忧心忡忡了,她红口白牙咬定您杀了那条犬,但细细想来,漏洞太多,只要皇上肯查,输得还是她。您之所以困陷在这个局面里,不是因为占不着理,而是错了态度,故您只消做一件事——认错以博情。”
储向歌默不出声,她半信半疑地琢磨起来,加之魏鹤耐心分析,思忖良久,一计又生。
再说沈司言,从异苑被皇帝带走的消息狂风骤雨般传遍宫廷,引出各方论调,主打此女子手段高明。
耕熹殿,墨香四溢,纸间摩挲。
“小骗子,起来吧。”皇上专心批着奏章,偶然瞟了一眼从床上摇摇欲坠着起身的女子。
沈尽情发懵,她一身新衣,襟带齐整。
“朕的床很好睡吗?你都歇了一个时辰了。”
沈尽情猛拍一记额头,心中叫苦不迭。
“不准乱想,朕可没碰你,”郭珩轻抚梅花眼,“是宫女给你换的衣裳。朕的床上绝不允许有洒狗血之事。”
“狗血之事……”沈尽情漠然重复一遍,“烈烈被储嫔杀害,皇上预备怎么秉公处理?”
郭珩滑稽地笑了,叹气道:“储嫔聪明的时候你笨,你聪明的时候储嫔笨。朕难道看不出你的伎俩吗?”
沈尽情心跳地快要穿膛而出了。
“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是崔尚宫教你的吧?”郭珩侧过脸,不甚客气地戳破谎言,“沈司言,你手里握刀,满浸鲜血,然后指责储嫔杀犬,不觉得好笑?”
“那皇上为何不当下拆穿我,判个欺君罔上之罪,砍头枭首,多痛快。”沈尽情倔强地说,她当时没有宽裕的时间,否则定能将这个骗局罗织地更细致一些。
郭珩蓦地起身,往她的所在踱步而来。“因为你哭得很惨。”
他接着说:“向歌第一天侍寝,哭得比你还惨,朕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
沈尽情胸闷恶心,暗骂一声“轻佻”。
“朕宠向歌太盛,这个小家伙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来治一治她的娇蛮,也好,免得步长公主后尘。”
“那么皇上要赏我吗?”沈尽情没有好脸色。
郭珩蹲在床前,双臂搁在床沿,撑着脖子看她,道:“不行,朕还没判你殴打天子之罪呢。”
沈尽情像看疯子一样地看着他。
“朕去问了母后你的事,”郭珩的眼眸亮比灿星,“好像沈司言小时候照着宁王鼻子上揍过一拳。”
“宁王大人不计小人过,应当释怀才对。”沈尽情佯装淡定。
“宁王是不会释怀的,但朕释怀了。”郭珩站起身,重回案台边,“功过相抵,你滚吧,别再招惹向歌了。”
沈尽情气笑了:这个天子是靠着胡言乱语坐上龙椅的吗?
她铆足了劲,好歹能使力将身子完全撑起来。
“等一下,有人来了,慢点再滚。”
最是不得体的话,无奈亦为圣旨,沈尽情憋着一肚子火等候。
前来奏启者有五:太傅闾丘陟、工部尚书赵稻、礼部尚书庞德、大理寺卿夏侯咫、礼部侍郎孟芙斋。礼部这两人占据的是太师孙继儒与太保汝定业之席,后二者老死家中,致使三公之盟不复存在,这于闾丘陟而言,更失天子面前话语权。
“五位爱卿所来何事?”
“回禀陛下,”夏侯咫面色阴沉,“督建天协馆的将作大匠姬世炓被人发现命丧野径,其护卫剑客甘蘖亦死在二里地外。”
郭珩皱眉,问道:“可查明是谁人所为?为何害命?”
夏侯咫胆战心惊地回答:“姬大人只喉部一处致命伤,而其护卫甘蘖却重伤多处,大人所带的财物也完好无损,故有司初步判断,此为行刺暗杀。如果真是刺客,那么京中有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刺客组织,嫌疑最大。”
“一个江湖野帮,行刺朝廷要员?听起来站不住脚。”郭珩严峻地说。
“微臣会督促下属继续追查,势必要找出姬大人遇害的真相。”夏侯咫埋头。
庞德犹豫,半晌插话道:“依臣之见,大理寺卿可以着重调查那些反对建造天协馆之人。”
太傅怒目,当下驳斥:“礼部尚书的意思,难道怀疑老臣买通刺客谋害姬大人?”
“这可不好说。”孟芙斋撇了撇嘴,小声嘀咕。
“吾皇万岁!”闾丘陟恼火,“耕熹殿虽非朝堂更胜朝堂,这种不学无术的骗子怎能许他进来商讨要事?老臣奏请陛下驱逐孟芙斋!”
庞德制止:“太傅用不着气急败坏,孟侍郎只不过表一表态度。”
“你!”太傅气短,捂着胸口说不出话。
工部尚书赵稻不耐烦,直言不讳:“诸位大人争论方向有误。现在最重要的是,建造天协馆是否要延期,不延期的话又该由谁负责?”
“姬大人死得不明不白,微臣建议先彻查此事。”夏侯咫禀告。
“有什么想不通的?不就是有人强烈反对这个项目,杀一刀下马威矬矬支持者的锐气嘛。”孟芙斋似笑非笑。
闾丘陟指着他鼻子骂道:“村野匹夫,你再出言不逊,休怪我不客气!”
“当着吾皇的面,太傅说话该过过脑子吧!”庞德不悦,深觉太傅在指桑骂槐。
“天协馆若延期,那些等着朝拜的各邦人士恐会失望。”赵稻耿直,只管说自己的事。
郭珩安静地听他们唾沫横飞,末了,清清嗓子,道——
“五位爱卿休息一下吧,听朕说就行了。大理寺卿,你即刻去调查姬世炓一案,但凡有线索端倪,只管紧追不舍,涉及高官重臣时不必忌讳;赵爱卿,大匠虽死,还有少匠,你与他沟通一下,即刻上任去吧,不过这回必得保障其人身安全,否则便算你疏忽渎职;庞爱卿与孟爱卿,你二人督管撰文写稿,广告万邦,天协馆从破土这一日起就已向他们敞开大门!至于太傅……”
闾丘陟铁青着脸。
“朕的生辰就快到了,那天别忘了和允轲、长公主一同来宫中赴宴。”郭珩漫不经心地说。
孟芙斋挑了挑眉毛:这个小皇帝,还挺懂得伤元老之臣的心。
诸人告退,耕熹殿里重又复了静谧。
沈尽情在偏殿里听得真切,自有思量——比照陇西王对沙菲克斯的态度,那位姬大人极有可能是他派人刺杀的,说不定还是出自小姝之手。
“沈司言鬼头鬼脑想什么呢?”皇帝的声音响起,“现在可以好好地滚了。”
沈尽情懒得和他较劲,下床后疾步出殿,敷衍一个“奴婢告退”,摔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