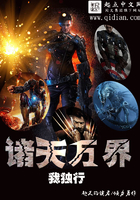“叔叔,你这样是几个意思啊?”柳宫姝手忙脚乱,拽着中年人的胳膊使劲把他拉了起来。
“小姝,我对不起你啊……”
柳宫姝有些愕然,自以为与这人素昧平生。“叔叔为何要向我道歉?我们是头一回见面,没有隔夜仇吧。”
“孩子,你仔细看看我这张脸,就没有想起点什么?”男人迫切地指着自己,眼眶湿润。
柳宫姝依他要求,只得仔细审视一番。良久,脑中浑沌忽如油里浇火,热浪滚起将诸多疑惑烧得噼里啪啦。
“铁梳子苏苏、啊不,铁苏子叔叔?!”
“是我!是我!”
小毛孩儿时的奶声奶气至今还逡巡脑际,然春秋十载一晃即逝,现正当花开时节动京城。
“小姝,你终于念顺了嘴。”铁苏子欢欣地笑道,但又不知怎的,心中萌生出许多失落。
柳宫姝兴奋难耐,恨不能在大街上载歌载舞,毕竟她的“亲人”零落天地、所剩无几。“我看见铁叔叔,高兴地可以三天不吃饭!”
“这不行,饭得好好吃,不然饿垮了身子就不漂亮了。”是否人上了年纪,对插科打诨的悟性就会日渐式微?
小姝终于能把铁苏子搀扶站稳,激动之余也是好奇,遂问道:“刚才,铁叔叔惨兮兮地向我下跪,真把我唬了一大跳,不晓得是什么说法。”
铁苏子拭去重逢的眼泪,暗骂自己行事鲁莽,向姑娘说:“咱们去铁匠铺叙旧——街上人来人往,被坏眼睛坏耳朵们打探到就不好了。”
话毕,柳宫姝由铁苏子指引,故地重回,一如当年从慈幼堂往铁匠铺度假期的情境,照旧吃了糖葫芦和鸡蛋煎饼,只可惜甜食已不如曾经那般诱惑胃口,卖煎饼的老爷爷也辞世多年、由他儿子继承下这副谋生家当。
小姝吃得心满意足,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铁匠铺。锅炉铁器似乎扛住了岁月的蹂躏,只比从前多几分沧桑;墙角的蜘蛛网残破不堪,一只瘪肚的蜘蛛垂死成干尸;隔开前后屋的布帘子满是油污,皱巴巴苦着脸,变成了灰尘土屑的安息地。
铁苏子用袖口抹了条凳和方桌,不好意思地请姑娘坐下。“客人们都不会在我这里逗留太久,我便懒得擦桌抹地了。”
柳宫姝绝无嫌弃之意,她爽快地坐在凳子上,开心地划拉着脚,就差哼一首小曲。“这儿有那么多兵刃武器,我喜欢。”
“这哪像闺阁里姑娘的爱好?你八娘……本立誓要将你养成淑女的……”铁苏子一着急,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冲口而出。
但小姝脸上并没有露出悲伤或感怀的神情,这一点让铁苏子十分诧异,于是斗胆试探:“孩子,你、你晓得八角枫的下场么……我并非故意惹你伤心,只不过……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也长大懂事了,对吗?”
“铁叔叔在说什么?我听着糊里糊涂的。”小姝天真地抡圆了眼眸,等待解答。
铁苏子“咝”了一声,反问道:“八角枫死在皇宫大内,这事你不知道?”未料他转而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子,自言自语地说:“废话!小姝被你害得遭人拐走,哪能晓得后来京城发生了啥。”
柳宫姝见此景,内心免不了纠结,她发现铁苏子得到并深信一个有误的讯息——八角枫十年前闯宫行刺,尔后被羁押天牢、畏罪伏法。但事情的真相应该告诉他吗?柳宫姝拿捏不准。
“现在要回到我同你下跪的事上了。”好在铁苏子也不愿在“八角枫”的问题上缠结,即刻将重心放到了赎罪的情绪中,“我对不起你啊孩子,如果当时没有自以为是地招惹那两个坏人,你就不会被拐跑。小姝在外吃苦受罪多年,大叔的心里则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每天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平安顺遂……我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向你道歉,然而多谢上天赏脸,今日竟能如此机缘巧合、与你重聚,可见我命中注定要赎罪孽。小姝,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让大叔好好补偿你,行不行?”
面对铁苏子近乎哀告的诚心,柳宫姝左右为难,她竟不知自己有一天会遇到如此棘手之事,假使此刻有沈尽情在旁支招那该多好。
“铁叔叔,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你,小情也没有。”
“是呀,还有那个丫头……唉,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铁苏子垂头丧气地说,要不是因为肩负责任,还真想立刻用蜘蛛网吊死自己。
小姝试着思考了片刻,权衡再三,终究不忍心让善良的叔叔被自责吞噬,于是选择性地吐露了真相:“铁叔叔,我得和你讲明一些情况,你听了不要声张,好吗?其实,我和小情过得很好,八娘她……也活得好好的。”
“什么?!”铁苏子不肯相信,好比野猫子落水,内心扑通地厉害。
“是真的,至于其中原委,铁叔叔就不要问我了,我不能回答。”
“给我点时间捋捋顺……”铁苏子连连摆手,目光飘忽。
铁苏子这种游神状态颇令小姝担心,她亦不敢细想自己所为是对是错。
“唉……”从茫然中跳脱而出的铁苏子总算恢复了几分正常脸色,只听他无奈却也不失体谅地说:“我相信小姝所说,八角枫没有死,我也不会为难你,再追问出七七八八的闲事来。总之,你能在大本营吃饱穿暖,大叔也能多饶恕自己一分。对了,八角枫,有没有向你提起亲生父母的事?”铁苏子问完,心中“咯噔”一声,自知这才是一切愧疚的根源。
小姝拨浪鼓似的摇着脑袋,道:“没说。不过我已不是小孩子了,心里明白得很,亲生爹爹娘亲必是被奸人所害,只因八娘不想我被仇恨搅扰,所以当年才编出那种话聊作宽慰。”
铁苏子苦笑着点头,额上慢慢渗出汗来。“倘若有一天,你揪出了那个‘奸人’,会如何报仇雪恨呢?”
“自然是血债血偿。”柳宫姝说这话时,眉头紧蹙、咬牙切齿,恍惚变了个人。
铁苏子干咳数声,耳根子红得不像话。
“对了,铁叔叔知晓慈幼堂现况吗?我惦记小时候的玩伴,想看看他们都长成什么模样了。”小姝捧着脸,一个个数叨,“小木通哥哥必然又高又瘦,华师父生得太好看了,也不知娶上师母了没?还有成日虎着脸的堂主苹婆,会不会满脸都是褶子呢?铁叔叔陪我走一趟慈幼堂吧。”
“不能去!”铁苏子斩钉截铁地说,“今时不同往日,慈幼堂已不复存在。”
“为什么?那么多人呢,总不会凭空消失吧?”小姝追问。
铁苏子闭眼,手不自觉地按在残腿之上。“你离开京城后不久,这里就掀起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杀戮,对象是大大小小的刺客——我若告诉你,你八娘和我都曾是组织中的一员,你应该不会太大惊小怪吧?罢了,这个已不重要,还说杀戮。初时,刺客们只以为是做任务不小心,被人记住了脸孔来寻仇,但随着被暗杀刺客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渐渐意识到,这或许是场预谋。一开始大家没有戒备心,容易着道被害,可做刺客活计的人并非酒囊饭袋、任人宰割不还手,两三天后,只要对面走来同行,彼此都戒备十足,稍有性子急的,不问青红皂白,先杠上再说,这么着,内斗又死了许多人。再者素日有私仇的人,因碍于组织规定不敢动手,眼见天赐良机,便混在骚乱中夺人性命……始作俑者挑起了火花,咱们自己添薪加柴,自困死路之中,如我这等只落下残废、没命丧乱局的,实在算幸运。杀戮持续半个月,诺大京城里的刺客死伤至少六成,这时候有人跳出来游说,便是慈幼堂的苹婆——明面上收容孤儿的正义堂主,原来是组织里的头目,而且杀戮的第一刀正是她下的手,出乎意料吗?她游说我们摆脱大本营的控制,自立阵营、自谋生路,将尖尾雨燕、寒鸦和游隼三门发扬光大。可是得知实情的刺客们早杀红了眼,深感受到一个老女人的捉弄,意气用事之下把慈幼堂里外杀了个精光——据说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后来连屋带宅被官府夷为平地,现在盖成庙宇,供奉某路不知名的神仙——你方才提到的伙伴,大约都遇害了。当然,苹婆也为自己的利益熏心付出代价,她的手下人寡不敌众、明不敌暗,终于轮到被别人偷袭而死,自个儿则朝不保夕,落荒而逃。听说有一回差点被同行追上砍杀,不料半道冲出个高手,即原组织在京城的二级掌事,尹圃,替她打退追兵,顺利逃脱。由此易见,苹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学舌的傀儡,幕后黑手乃是这个尹圃。往后,失掉组织的刺客们日子越发难过,再加上尹圃时时鼓吹自立门派,他们便慢慢回心转意,脱离大本营,投靠进尹圃的新组织中去了。”
柳宫姝大动肝火,握剑的手已掐出血来。
“我不想再参与打打杀杀的事了,尹圃的新组织是什么情况,也不得而知。”铁苏子道,“但有个疑问总想解开——尹圃为什么恨极了大本营,背叛而出呢?”
“居然,居然对无辜的小孩子、老嬷嬷们动手,这群畜生!”柳宫姝红丝布眼,青筋攀附额角。
铁苏子重叹一口气,一来认同她的观点,二来感慨,曾几何时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儿倏忽懂得了愤怒,开始保不住内心单纯的乐土。如果非要体味悲欢离合人间苦楚,才能成长为完整的人,那么他但愿小姝永远是个五岁的傻丫头,尽管这种私心可笑得不值一提。
“铁叔叔,我今日空闲时辰不多,就不在这里久留了。”柳宫姝霍然起身,“铁叔叔知晓尹圃、苹婆的下落吗?”
铁苏子猜到了她的心思,忙不迭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小姝,你不要冲动,什么事还得从长计议。”
“那么,残杀慈幼堂的那拨人,铁叔叔能说得出一二住地吗?”柳宫姝根本听不进他的后半句话。
“这……”铁苏子小声道:“我只知道有个叫马青牛的,这会子或许在元宝丰赌钱……孩子,你听我一句话,此事错综复杂,你纵然杀掉这些喽啰,也不能动摇其后的根基。”
柳宫姝冷笑,不置一言,拔腿出了铁匠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