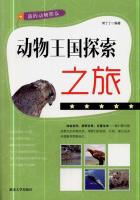冯雪退前脚刚回宫,后脚就被请去耕熹殿。皇帝近侍、年轻的太监总管康豆心惊肉跳地透露说,天子酒醉失风度、闭门不出龙颜怒。虽说心中有些许不痛快,念及妇道、后德,皇后还是巴巴儿地赶去了龙潭虎穴,连正经的朝服都不曾换上,只穿着清淡素衣。
远远就看见内命妇们在耕熹殿外跪成数列,口中娇滴滴柔恰恰求着殿内那君主顾惜身子;再仔细一瞧,连太后老人家都闻风而来,站立在队首,愁眉不展地干着急。
司柟紧紧搀扶着皇后,她知道主子这是遇到了一个难过的关卡,不受点来自各方的委屈是不能交差的。冯雪退还算镇定,她与贴身婢女共患难似的对视了一眼,毅然迎了上去。
“臣妾给母后请安。”
太后正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冷不丁被吓了一跳,张嘴就要斥责:“哀家当是哪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原来是你啊!皇帝把自己关在里头这么些个时辰,宫里大小嫔妃都来苦劝,你作为后宫之主,竟然还要哀家派人三催四请,哼,真会躲清闲呀!”
“母后误会了。臣妾省亲数日方才归来,见康公公在我殿里等候,马不停蹄就赶着来了。”皇后的语气较之从前硬了不少。
太后也察觉到了儿媳妇的细微变化,更加生气:“哟,皇后的意思乃是哀家错怪你咯?听哀家问话,是谁允许你回家省亲的?你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学得什么人这样放肆?若是思家,只管求了谕令将家人接入宫门聚一聚就好,你倒有本事,干脆撂下一应事务,自己跑出去了,要是给平民百姓落下口实,编排些有的没的传闻出来,你可担当得起?天家的颜面就要给你丢尽了!”
“臣妾的作为都是皇上首肯的,若非家父顾念礼法,臣妾还要在家里呆上十天半月呢。太后要责怪,臣妾不敢不服帖,但是皇上也得一并聆听训诫,今后才能杜绝臣妾这种放肆的行为。”皇后答话,一改从前温弱弱的乖巧样。
“你回家究竟是去探亲还是去学诡辩术了,如何变得这样能逞口舌之争?!”太后深感意外,若非被素常嬷嬷护着,都快要被这些话气得翻倒身子了。
向来被赞以“孝顺、有德”的宜妃按捺不住了,她见太后神色难看,急忙起身到近前伺候。“母后不要动气,皇后娘娘是聪明伶俐的人精,绝不会在宫外惹出什么麻烦,即便一时激动话里有失,也定非故意气母后的。”
换做平时,冯雪退十有八九会应承旁人的帮腔,只是不知今天在心中窝了多大的火气,听着宜妃一席话甚是烦躁。“宜妃真会劝人,怎么不见你到耕熹殿里去善解人意呀?”皇后一句,顶得对方哑口无言。
司柟知道主子这番转性缘起于同皇帝的心结疙瘩,尽管事出有因,但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来,更像是皇后骄纵蛮横、欺负弱小;她轻轻掐了主子的胳膊一下,冯雪退霎时清醒过来,待她回想方才所说的话,确实有失度之处。
这样难得一观的吵闹怎么能戛然而止呢?蕙妃笑看皇后与太后、宜妃相争,还不过瘾,自己去加了把火:“哎呀,皇后娘娘有所不知,您不在的这几天,宜妃没少在皇上身边叨扰,好话歹话都说尽了,皇上厌烦地透透的了。说不定,这怒火还是宜妃给点起来的呢。”
“本宫说呢,蕙妃今天怎么如此安静,果不其然,才憋了一会就崩塌了。多说一句话能得块肉似的,嘴不闲。”宜妃把从皇后处受的气转移到了惠妃身上。
只不过斗嘴这茬事在太后是个大忌讳,她忍无可忍、当下发作了:“都给哀家住口!耕熹殿前这般搬弄口舌,还把皇帝放在眼中吗?!你们要是跪累了,就不必在这里装模作样,省得让哀家一把年纪还要看你们甩脸子!儿子是哀家的儿子,你们不在意,哀家可在意!素常,把这些人都轰走!轰走!!”
妄图再作妖、掀风浪的人听了这老母亲的愤言,通通拉平了嘴角,鸦雀无声。
未料耕熹殿的大门却在这时开出了一条缝。
皇帝歪斜的身子倚在门扉之上,醉眼扫视了这群闹喳喳的女人,终是有话要说,指了指冯雪退,道:“只皇后一人进来。”说罢转身而回。
女人们妒恨,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跟皇后吃醋,心中躁狂,暗骂殿前石子路跪得膝盖疼,把无辜的匠人们诅咒了个遍。
冯雪退拍拍司柟拽着不放的手,示意她莫要忧虑,自己独身进殿,将大门闭合在身后。
耕熹殿一人多高的窗户上蒙盖着锦帘,在不点烛火的大白天暗极了。
酒瓶子滚了一地,奏折撒了一地,毛笔砚台摔了一地。
冯雪退蹲下身,安安宁宁地拾掇整理起来。
“你别动,让奴才们来做就好……”皇帝倚在殿中圆柱上,眉眼朦胧,“怎么不在家里多住几天,回来得这么早,莫非是想念朕了?”
“心里不踏实。”
“有什么不踏实的?你是皇后,你父亲是相国,你弟弟是大将军,如果冯氏家族都不踏实了,外头老百姓就更不踏实了。”
“臣妾连同母家的荣耀都是陛下给的,陛下高兴了,臣妾却不敢高兴,陛下生气了,臣妾则惶恐难安,故而日日夜夜没有踏实的时候。”
皇帝努力把眼睛睁开,看着那个纤弱的身影在眼前飘摇。“你冤枉我,我不开心。”
冯雪退一愣,手中的酒瓶子差点砸了。“陛下喝多了,天子不能随庶民称‘我’。”
“天子天子,天底下最大的傻子,我不当、不当……”
“陛下莫要任性,祖宗拼搏基业不易,陛下自当勤勉效力。”
“哼,你又开始说这些官话了……谁不知道,这皇位是传给嫡太子的,我区区一个鲁王,怎么轮得到坐龙椅……”
冯雪退把酒瓶子定立在地,向圆柱走去。“梓容,时局已然如此,你就不要妄自菲薄了。试想,如果你和嫡太子一般昏庸无能,当初怎会有臣子愿意拥护、辅佐你?难道三公、我父亲,甚至林帛夫、敬仚,都看走眼了吗?”
郭梓容“哈哈”大笑,撑着柱子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你说嫡太子昏庸无能?他还写奏折来骂我呢,文笔斐然!喏,就是那个红皮的折子,你看嘛,你看。”
冯雪退顺着丈夫所指,从地上一堆凌乱的文书里翻捡出嫡太子的折子,看了两行,禁不住皱眉。“不过是败寇的牢骚,哪里就值得夫君为之劳神?历朝历代王子之争,但凡落败无一不被上位者诛杀殆尽,夫君能留他在牢狱中苟延残喘,这厮不知感恩惜福,还敢口出狂言污蔑君王,可见终是留不得。”
“你的意思是要杀他?”
“我的意思是,梓容如果心有所累,把包袱除了就好。”
郭梓容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身子重心,默立凝视妻子,半晌,说道:“雪退,我常常在想,这许多年来,把朝廷政事说给你听,是不是错了?诚然,你的聪明才智胜过朝堂上许多人,也在关键时刻帮助、提醒我,但是……但是你不太像妻子,我是说,谁会和谋士同床共枕而心无芥蒂……”
冯雪退细长的睫毛忽闪了一下,有些委屈,可说不出口。“夫君不喜我参政,我从此眼不见耳不闻就是了。”
“我不是在责怪你,毕竟很多事也是我一手造成的……”郭梓容踉跄着向她走去,脚下一乱,跌倒在地,幸好冯雪退灵活,勉强扶住了他。“我想说……对不起……”
“夫妻间不必对不起,我既然嫁给了你,是福是祸,一并承接了就行。”冯雪退低头,看着衣裙上金银花的图案。
郭梓容反身一把搂住妻子,在她耳边呼一口温润的气息。“在政事上让你心烦劳累,是为夫的错,在家庭中让你冷落失意,更是为夫的错。”他环着她的小蛮腰,心跳加速。
“我已说过,你我没有对错可分。”冯雪退挣扎。
这个男子受到酒气的怂恿,把九五至尊的荣光都抛却了,拥着怀里那束诱人的柔花,心存饿狼猛虎,有意采撷。
“梓容,你放开我!”冯雪退小腹内汇集了一团郁结,将脸别转过去。
“你是我妻子,我碰你并不犯法。”他拒绝道,攥住她的手腕,压于身下,如一只心急如焚的松鼠,想尽办法要将触手可及的馥郁橡果填入口中。
冯雪退本就病弱,哪有力气推开他,此时惊惧地落下眼泪。“陛下、陛下,此事不妥!”
郭梓容冷笑:“你想拿平天冠吓唬我吗?好吧,就算如此,朕是皇上,还不是想要哪个女人就要哪个女人!”他扯开皇后领口,一段粉肌白脂现于眼前,精致锁骨由碧玉石色的衣衫衬托,仿佛白鹭展翅连天,美哉。
“我不愿意!不愿意!”皇后哭得噎住声,将指甲也挣断了几根。
“朕就是天,你敢违抗?!”皇帝恼怒,狠狠地吻在她的唇上、眼角、额头。
御花园的荷塘正是缤纷时刻,有几多菡萏还是花苞骨朵,落下一只蜻蜓,毫不腼腆地伫立其上,贪恋自然美色,久久不肯离开。
“你这是要!杀!我!”皇后攒着所有的力道,开天辟地一声尖叫,耕熹殿外的人没有听不到的。
殿内,皇帝像被抽了魂,什么心思都烟消云散了。
皇后哀恸:“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雪退,朕无意伤害你……”皇帝内疚道。
“你这是要杀我、要杀我啊,呜呜呜……”皇后泪难自禁,“难道你忘了十数年前的雷雨夜吗?难道你忘了我腹中为你谋权篡位而牺牲的婴孩了吗?难道你忘了我自那时起就损伤了女子胞,再不是个完整的女人了吗?可你还是要提醒我的痛处……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啊……”
皇帝像个犯错的孩子那样,迟迟不敢抬头看眼前这个崩溃边缘的女人。“雪退,是朕糊涂了,朕喝了酒,神志不清,你原谅朕,原谅朕好不好?”
皇后伏在地上,浑身都疼得很,颈脖子上已经泛出淤青。“别说了,我难受……”
“哪里难受?朕宣太医来!”皇帝紧张地横抱起她,皇后已虚弱如一团棉絮。
“来人!快来人!”皇帝叫喊道,抱着御妻,一脚踹开殿门。
殿外一众人等吓得跟鹌鹑无异,太后瞧着儿子、儿媳这般狼狈模样,惊得连退数步。
“快,康豆,摆架太医院!”皇帝惊慌失措,不等小太监跟上来,自己已跑出十数步,好巧不巧和一位闷头赶路的大臣撞上。
那大臣本也忧心忡忡,见惊扰了圣驾,更是惶恐,抖索着起不来身。
“混帐东西!伤了皇后,看朕不摘你脑袋!”皇帝骂,又要继续赶路。
“微臣罪该万死,只不过得了边疆信函,着急呈给陛下,才这么不长眼睛的。”
皇帝奔跑的脚步停一停,不耐烦道:“什么事值得这样乱心?”
“回禀陛下,边疆将士与敌寇新战大败,死伤无数,冯洗砚将军下落不明!”
冯雪退闻言,在皇帝怀中猛地瞪圆了杏眼,还来不及咽下满腔焦虑,头一歪,彻底失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