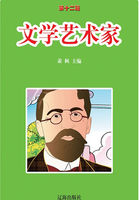都宰昂夜视极佳,平地虽然罩上了鬼魅迷雾,他依然可以看穿遮障,向着远处一块馒头似的天然石墩子走去。只不过看似平淡无奇的“馒头石”其实挺会耍人眼力,真正站临其下就会发现,这墩子巨硕夯实,足有二人之高。
馒头石的平顶上盘腿坐着一个中年人,姜黄发色被银白月光映成粼粼流波,打着大小不一的卷子,服帖地卧在主人脑瓜上。
“我诚意十足,你呢?”中年人平视前方连山叠峦;细究他脸上的皱纹路数,看得出是个热衷劳心者。
都宰昂抬手轻摇,他身后紧跟的七八属下即刻退后丈远。“他们听不懂汉话,就算与您排排坐也不碍事。但若做买卖的双方均心怀顾虑,这交易就很难进行了,是不是?我已照顾了您的情绪,不知道能否换前辈为我着想一次?”
“人都赞你是贝喀第一剑,我瞧着阁下经商也自有门路。你希望我如何替你着想?”
“哎呀,谁都知道沙菲克斯有数不清的‘替身’,前辈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就是本人,那我可不愿意在此多费口舌。”都宰昂斜靠在馒头石上,伸了个懒腰,“方才有个女孩子说,这黑灯瞎火的时辰还在外乱逛的都不是好人,我和她想到一起去了。”
沙菲克斯不加掩饰地嗤之以鼻,道:“你可知‘自证清白’是最无聊的举动?但凡对方抱有偏见成见,纵是将万千事实摆在他眼前,也未必能推翻其人经年累月的妄断和误解。时间珍贵,如果你非要揪住‘我是不是我’继续胡扯,那今晚只能徒劳一场。”
都宰昂砸吧了嘴,说:“前辈真是的,比姑娘家还要傲气娇蛮!我这头货都备好了,您倘若不收,莫非我还要将她退还给汉人?”
“我周旋各国已用尽了嬉皮笑脸、耐心韧劲,轮不到你个后生再来试探。”沙菲克斯今日尤为沉郁,没有说俏皮话的意愿,“安定公主现在何处?”
都宰昂随手折了棵草秆,叼在口中,慢条斯理道:“贝喀生长着一种植物,单是随意触碰就极有可能被毒死,比赤棘那些雕虫小技厉害多了。但贝喀的先祖聪慧且善良,独创古方秘法,能用这些植物制作效用奇绝的香精,专销各国权贵势族。前辈在秾婻享用过吗?”
沙菲克斯漠然答道:“你指的可是‘罢弗’?这玩意效如其名,一经沾染就欲罢不能,十人中九个半都会上瘾。说起来好笑,十五年前我借了点滴成品加入自制的‘灵药’,倒是在京城里折腾起片刻波澜。不过,这和安定公主在哪里有关系吗?”
“前辈也是急性子?话要娓娓道来,才会引起重视嘛。”都宰昂笑了笑,“能将毒物转化为香精的秘诀从古至今都掌握在贝喀王室或亲信大臣族人的手中,譬如我就沾了父亲的光——不握剑的时候专门从事罢弗产销,日积月累囤了不少财物,现下承揽了这附近荒郊,种了三千亩地的罢弗。”
沙菲克斯厌倦了他的述说,打断道:“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标榜自己财大气粗?”
“我想说,”都宰昂吐了草秆,“公主就被安置在罢弗田的地下室中。要想穿越如此广袤的毒物群落并毫发无伤地找到一方斗室的精确所在,没有我的指引,难如登天。”
“所以,你现在有资格和我叫板,是这个意思吗?”沙菲克斯稍稍偏过头,斜眼看他。
都宰昂挠了挠被蚂蚁咬痛的胳膊,道:“加码,想得到公主,前辈得加码。”
“临时改约不是诚信经商的准则吧?”沙菲克斯稍显愠怒,“我已实话实说了自己当时积极撺掇赤棘与贝喀联姻的目的,达到用秘密交换你行动的条件,阁下应当知足了!”
都宰昂不火不躁地说:“前辈指使贝喀第一剑做事时就该心里有数,付出的代价怎可能就那么点。宠姬安雅诓骗了我们国家的土地,这已成为既定事实,前辈有没有其他预见性的秘密能同我分享的?”
“贪心不足,恬不知耻!”沙菲克斯游刃诸国外交有余,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对方国主大臣均秉持君子德行,阴谋诡计出于自己;然而都宰昂并非正经人,他不拘什么手段,都想尝试。
“前辈玩弄天下的本事高超,就不能带带后生吗?”都宰昂仰颈望他,的确怀揣着旺盛的求知欲,“您提示一下,我自己琢磨就行。”
沙菲克斯被夜风吹得头疼,借着火气决绝地斥责:“你这种做买卖的方式,或许得意一时,却必有跌跟头的那刻!滚吧,我不想看到你!”
“前辈稍安勿躁,”都宰昂掉头就走,“货最多积压在仓库里三天,届时前辈还不肯加码,我就只能退回去了,汉人充其量耽搁了脚程,终究会顺利抵达贝喀王宫。”
沙菲克斯气得发抖,指着都宰昂渐远的背影骂道:“天下江湖人都一样狡诈,该死的小滑头!”
头顶扑棱棱掠过怪鸟,兀地咋呼鸣叫,声波荡漾在萧索的空气中,传出去很远。
鸟语飘渺进冯洗砚等人的耳朵,他们个个愁眉苦脸。
“你把公主失踪的情形再描述一遍,不要错漏半分细节!”冯洗砚偏不信邪。
月娉哭哑了嗓子,眼肿如桃。“我已把所见所闻都吐露干净了,再难忆出疏忽掉哪些微小线索……将军,可能我们真的见鬼了……不然,为什么只丢了公主,那些金银财宝分文不缺呢?我听说鬼娶亲……”
“住口!”冯洗砚大喝一声,“少在那里胡言乱语混淆视听!你作为公主近侍,在她失踪一案上脱不了罪责干系!”
“都怪奴婢的话,这趟远行要将军何用?”月娉不甘担负全责,“现在离最近的陇西也相距十天十夜的路程,将军要论法追责,也该在汉地国土上对我动刑!想让奴婢客死异邦,绝不答应!”
冯洗砚真不愿和泼妇斗嘴,他想起莽直的唐贸,居然有些怀念。“别啰嗦了,找不回公主,本将军也得搭进性命。此刻,绑匪团伙或许仍旧环伺在旁,所有人都仔细提防着,一旦有发现,速来向我汇报。”
月娉突然想起什么,分拨开胆小如鼠的宫女们,一眼盯上柳宫姝。“你方才去打水,可曾遇到什么形迹可疑的人?”
小姝认为公主被掳多是自己失职所致,愧疚之情充盈,垂头丧气地答道:“有吧,我还和他说了一会儿话。”
“什么话?”冯洗砚紧张地问。
“奇奇怪怪的话……”小姝兜不住场面,想着缴械投降算了,“其实我不是宫女……”
冯洗砚拔出腰间佩剑,直抵姑娘喉咙。“你最好赶紧解释清楚自己的身份。”
小姝叹气,用手指撇开剑尖,坦言:“我听从陇西王吩咐,假作宫女暗中保护公主殿下,就是为了抵挡意外事故。先时被这个姐姐骂了几句,我忘了护卫要责、负气出走,方才令坏人们有机可乘。”
“哈,这下弄明白了,原是你的过失!”月娉扬眉吐气,得理不饶人地谴责道,“不是宫女所以要和我犟嘴?但你再娇气也仅是个替主子办事的下人,擅离职守该当何罪?!”
冯洗砚紧锁眉目,制止称:“与其说她罪不可恕,不如说是你颐指气使在前,免不了让人怀疑‘调虎离山计’得你暗里协作。”
“冤枉啊!”月娉大惊失色地为个人辩护,“奴婢伺候公主那么多年,耿耿忠心一尘不变!在列的奴才里,敢说只有我对公主至为敬爱,甚至连她的音容笑貌都熟悉得可以模仿!假使你们非得血口喷人罗织奴婢罪状,那我索性以死明志!”
月娉说到激动处,蓦地向锋刃冲过来;小姝疾抽车底宝剑,赶在奴婢寻死前挑落将军手中武器。
“好功夫!”冯洗砚大赞,尽管自己没招架住她的进攻,多少有点丢脸。
“姐姐烈性,”小姝冷眼瞧着目瞪口呆的月娉,“攒着这股子愤慨对付绑匪才不枉你与公主主仆情深。”
月娉缓神,羞愧难当、低头嗫嚅:“我那样凶蛮待你,妹妹还不记私仇阻我自行了断,对不起……”
冯洗砚打圆场:“罢了罢了,都为主人卖力,同道中人就甭讲究这那了。姑娘侠肝义胆、身手了得,不知怎么称呼?”
“只叫小姝就行。”
“哦,那么你缘何会归附于陇西王麾下?我只知他是位不务正业的老宗亲,难道也和江湖中人打交道?”冯洗砚狐疑。
小姝烧脑,撒了个蹩脚的谎:“我、我、我并不专门受命于他,对陇西王也没甚了解……大概他关心疼爱公主,所以才找我来秘密护卫。”
“这样啊。”冯将军并未深究,转而萌生另一念头,“如此一来,陇西王真算得上料事如神,他是否一早便知晓会有人对公主不利呢?不对呀,他有担忧怎么不事先与皇上交流呢?这局势叫我捉摸不透。”
小姝闭紧嘴巴,生怕再说出不得了的话来。
“我得飞鸽传书回京,”冯洗砚打定主意,“兹事体大,必须由圣上定夺。”
将军话才出口,不及众人有所反应,从天而降一柄长矛,径直扎进车轱辘。
“注意警戒!”冯洗砚扬臂高呼。
小姝迅速判断了飞矛来向,留话:“我去查探。”遂持剑而往。
明处众人只有着急瞪眼的份,根本不知暗处贼眼打的什么鬼主意——
“看看看,小美女来了。”
“昂少爷不在乎与那位大人谈判失败,反而更关心女色吗?”
“要容许前辈有时间深思熟虑嘛,这期间反正空闲,我自己再不找点乐子,多无趣。”
“昂少爷收敛些吧,别忘了族中巫师预言。”
都宰昂拉下脸,甚为不悦地瞥了随从一眼。
“我,毁在女人手里?”他掰了掰手骨,咔啦作响,“你好好数一数,迄今为止有多少女人已被我毁了。你先撤吧,将汉人公主看牢是最重要的。”
下属唯命是从,自然不敢坏主人好事,说走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