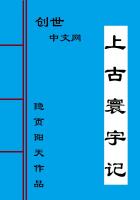国丧毕,五月的余音只剩最后几个节拍。
人燥起来,衣裳可删减,烦扰却层层累加——皇帝的脑海里搁浅三艘巨船,死活拖曳不动:其一,与沙菲克斯会面即在今日,文武百官皆掌握了雄赳气昂的辩术,朝堂的地板又能被唾沫星子刮擦一遍了;其二,大理寺与廷尉府协作调查江野小帮派的端倪,进展不甚明显,有待继续发掘;其三,赤棘人又起狼子野心,竟然漂洋过海去挑弄岬彭民众,中央实不能坐视不理,军队纠集、整装待发。
在前庭诸位国之栋梁争吵地动口又动手时,后宫格外祥和热闹——魏鹤加官尚宫局一把手的典礼,正在储嫔向歌的笑靥中进行,而现下唯一的长辈王氏太后则未置心思于三宫六院的杂务上,她的饭碗汤匙、床榻浴盆中无不满载对皇帝江山社稷的忧虑。
“表姐身着尚宫制服,气势非凡哪。”储嫔遥望相赞,六分真情四分假意。
魏鹤的下巴高挺,眼里根本看不到那些济济身畔、道喜祝贺的宫人。她听到主子称誉,稍欠了腰,恭慎地回应:“我今日显赫,全靠娘娘成全,愿为您倾尽牛犬庸才,鞍前马后绝不疏忽半厘。”
储嫔打一把圆扇,遮去小半张精致妆面,眼眸左右瞭着,突然定在了边角里那个女子身上。
“沈司言,你垂头丧气,大概心里不好受吧?”储向歌缓步下高台,奴婢们战战兢兢地给她让道。
沈尽情深吸一口气,作揖施礼。
魏鹤紧随储嫔而移,此刻正居高审视属下无可指摘的规矩行为。
“一个多月前还是平级的同僚,一觉醒来对方就成了上司主管,这滋味是酸是苦?”储嫔用扇子撩起沈尽情的面孔。
“不酸不苦,只是辣。”
魏鹤轻蔑地笑了笑,道:“沈司言喜欢在文字上翻新出陈,骗得了别人,却骗不过本尚宫。”
“一想到在这个位置上呆了几十年的崔明止朝夕更替间就没了,”沈尽情自顾往下说,“我更庆幸自己只是个传话达旨的小司言,碍不着谁的事。”
“你咒我!”魏鹤扬声,少顷又镇静下来,“燕雀与鸿鹄本性相异,九天之高,前者看了只会头晕目眩,后者却为能伸展开羽翼欣喜。”
沈尽情点头,那表情似乎很是叹服魏鹤言论。“魏尚宫妙语莲花,在娘娘身边伺候,恰如其分。”
魏鹤咬牙:沈司言一边讽刺她“油嘴滑舌”,一边又给储向歌埋下雷火,骂其呆笨,看不出魏鹤甜言蜜语都是有所求的诓骗。
储嫔在闺中读书不少,听得出这一团和气后面有别扭;她默然瞥了魏鹤一眼,摇着扇子,若有所思地走开了。
沈尽情脱身诘难,不甚在意旁人打量、揣度她的各色眼光。
再拖拖拉拉调整了个别女官的品级后,场院里人皆四散;储嫔和魏鹤对沈尽情看轻看扁,也不认为和她较劲能得着多大乐趣,事后懒得搭理,任她在太阳下神神叨叨地冥思苦想。
这会儿,团萃一溜烟从游廊外奔来,向主人汇报:“前朝散了,闾丘大人、孟大人、吴王殿下都有意与您谈话,先见哪一个呢?”
沈尽情不假思索地回答:“你领着孟侍郎往……文慎皇后的寝殿去,那儿比冷宫更萧索,我就在彼处等先生。”
团萃认真地记下嘱咐,小跑着去接引孟芙斋。
文慎皇后生前住地与泰兰殿相比,宽敞、空洞倍余,不知从何年月起传出闹鬼迷宗,据说在特定角度的太阳光线下能看见病死鬼冯雪退把守宫门前、痴离地与人对视。蠢钝的宫女太监没有闲工夫辟谣,平日经过此处绝不抬头就对了。
“娘娘打小怜惜我,”沈尽情在树影葱茏的宫殿前站稳,低声道,“今日借宝殿一用,望您成全。”
也不知出于什么缘故,阳光普照下,她分明看到殿门向里开出一道宽边。
说沈尽情波澜不惊是假的,但她没有恐惧的理由,四下里瞧了无人尾随,于是快步闪身入内。
“嘿嘿,我走了捷径,比姑娘先到。”孟芙斋的脸赫然摆在跟前。
沈尽情诧异半晌,随后莞尔。“还以为是冯皇后英灵替我开门,原是先生啊。怎样,今日朝堂上可有新鲜火热之事?”
孟芙斋将门关得密实,紧贴着糊纸又向外头瞄了许久,方才回答道:“沙菲克斯真不是个东西。”
“啊?”
“不对不对,这么说就显得我落在下风了。”孟芙斋转过头,挠着鼻子说,“他脑子还挺好使,一听说皇帝意欲改址岬彭,也不再急赤白赖地坚持秾婻,转而荐举贝喀。”
“贝喀自建国以来始终受我朝庇护,难道暗中和秾婻勾结了?另外,岬彭是相对而言筑造天协馆最理想的地方,皇帝不会听他胡说八道的,对吧?”
孟芙斋双手握拳,徒增气愤。“哼,所以说沙菲克斯狡猾,他肯定与赤棘进行了不可告人的交易,撺掇他们侵扰岬彭,弄得岛民惴惴不安、耽误生产,根本没有闲情逸致开工动土造楼宇!”
“真的吗?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早就知晓此次朝见会遇到先生设置的阻碍,所以早早备下别的方案?”沈尽情百思不得其解。
孟芙斋拨浪鼓似地摇头:“哪有这么神乎其神,我有这种感觉,他一定是在国丧期观察到了某种变化,由此推测原计划不保。不过老头子想不通,他凭什么能够说服赤棘人呢?”
“比起先生的疑惑,我更想知道他会什么会把贝喀推出来。”沈尽情雾水淋漓。
“姑娘这疑问比我那个刁钻几十倍。据我所知,贝喀就像一个服帖且嘴甜的孩子,也不说它拍咱们的马屁,反正很得宗主国疼爱,历代皇帝对贝喀十分慷慨,即便那时祖先们志不在天下万邦,唯独把贝喀牢牢握在手掌心,按常理,它诸事顺遂,不该找不自在啊。”
沈尽情头一回见着孟芙斋抓耳挠腮,也替他心急如焚。“可惜我消息不灵通,无法为先生解忧。”
“非也非也,老头子屁颠颠来找姑娘,为的不是把问题推给你。”孟芙斋眼中闪烁,“请问姑娘,愿不愿意向你身后的人就此事打听虚实?”
沈尽情霎时语塞,她不知不觉把自己放进了孟芙斋的阵营,几乎要忘掉受本源控制的可怕事实。“当然愿意,就怕我问了他们不说。先生有所不知,这当口儿太傅也在找我。”
“妙极妙极,麻烦姑娘装点二三演技,代老头子探探他的口风吧。”孟芙斋兴奋。
事不宜迟,沈尽情辞了礼部侍郎,主动找寻起太傅。
在御花园拐角一处凉亭外,尖眼的小木通喊了声“沈司言”。
“你去哪儿了?我到处都找不见。”闾丘陟对她连指甲盖大小的好感都没有。
沈尽情气喘吁吁地信口胡诌:“魏鹤新晋尚宫,我想着要巴结她,所以到花房挑选上等木兰去了,可是没有好品种。”
闾丘陟严厉地说:“你既自己提了这事,我就没理由不训斥你。魏鹤借着崔明止一事登上高位,你的出头日在什么时候?成为和皇帝亲密的女人——这任务虽没直白地透露给你,但你就不会自行领悟吗?”
“可你们要我除去太皇太后时,就不怕我败露后直接被砍头吗?”沈尽情心里的疙瘩未除尽,论及此事仍不畅快。
“你不可能死。”闾丘陟一挥衣袖。
“所以,崔明止也是你们的人咯?”沈尽情冷嘲,“好一出苦肉计!骗了我四个多月,也亏得你们有耐心!”
“国丧都过去了,你还要张口闭口杀害太皇太后吗?”闾丘陟怒目圆睁,“崔明止自有志向,你别一口一个‘你们’地想显出自己是多么‘被逼无奈’!要想活得长久,听话最有用!”
沈尽情攥紧了纤纤十指。
“我没时间浪费在一个冥顽不灵的人身上,你注意下态度。”闾丘陟数落完毕,开始说正事,“当前要你做的,是说服安定公主,自请嫁到贝喀。”
“为什么?”沈尽情狐疑,“没有前因后果的话,这也太突兀了。”
“本源安插在贝喀的密探来报,其国要乱。”
“咦,贝喀一直很听话,况且我朝待他们优渥,怎么乱得起来?”沈尽情站在孟芙斋的角度问道。
“这么说吧,贝喀的老国王年近九十,鳏寡四十载,在沙菲克斯的牵线搭桥下娶了赤棘年方十七的公主为妃,万千恩宠集其一身;公主手段高明,居然怀上王嗣,喜得老丈夫送她母国半壁江山为贺礼,赤棘已笑纳了。这还不够麻烦,最头疼的是沙菲克斯居然提出来在贝喀建天协馆!别人不知,我却清楚,他选中的那块地,已归属赤棘辖内!那群野蛮鸟人懂什么文化建设,为答谢他帮忙圈来这么多土地,这天协馆必是由秾婻代理了!我本就反对造这破楼,现在好了,劳民伤财不说,居然还是为他人做嫁衣!”
沈尽情听他说完,终于解开了先时自己那个疑惑。“沙菲克斯这路绕得真远啊,他的计划都不是一日而就,可见在过去的每时每刻,这厮算计完这国又忙着诓骗那国……不过,让安定公主嫁过去,能有什么大作用?”
“贝喀对我朝依恋根深蒂固,公主下嫁实属无上荣耀,必得立为王后方显尊重,而况这是自愿行为,只怕贝喀的王跪着迎娶也表不尽感激之情。在这种形势下下,赤棘鸟妃再得宠也得还政于王,加之咱们的公主坐镇贝喀,谁还敢继续和赤棘勾结、助长贝喀得意忘形之势?!”
“然而让悕公主嫁与行将入木之人,太残忍了……”沈尽情长叹一口气,这任务又令她左右为难。
“要怪就怪沙菲克斯和赤棘人同流合污,到处惹事。”
沈尽情忆起孟芙斋的困顿,忙问:“这个秾婻使臣也够八面玲珑,不知凭什么能说服赤棘与他合作。”
“归根结底还是土地问题。”太傅想了想,将丹帕之事说出,“本源在国丧期抓来沙菲克斯身旁的赤棘护卫拷问,得知这两个国家居然自不量力地觊觎起我们的土地来了。外邦诸国,任是再俯首称臣,也没有赤胆忠心的好狗,故而本源和我始终反对皇帝交好异族的政令——要开疆扩土的话,打过去、攻占下来就是了,何必弄出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
然而沈尽情的关注只在前半句话。“那个护卫后来如何了?”
“杀死了,不然还留着过端午节吗?”太傅笑她愚笨。
“会不会是这个护卫的死亡引起了沙菲克斯的警觉,致使他在应激之下换用贝喀那套备案?”沈尽情想,像大使这种心思极其细密的人,近侍莫名失踪之事必会启发他着手第二种甚至第三、第四种计划。
闾丘陟不以为意地撇嘴:“随他折腾,无论如何也敌不过本源,不是吗?”
沈尽情敷衍地称是,她已等不及要把答案告诉孟芙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