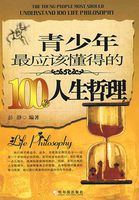朱雄一脚踢上去,阿福疼得大叫一声跪倒在人民面前战战兢兢垂下头,朱雄白了他一眼,对着汹涌的人人群高声说道:“我奉太子爷之命,管教管教这个刁奴。四十六年一月,这贼奴替福王千岁到山东丈田,田边之田,业外之业,恣行包占;二月,替福王往汝州丈地征租,每钱加收五分,逼得百姓卖子揭瓦,易子而食;三月,勒索佃户,打死周化、鲁国臣,草菅人命;其他剽掠为资,欺男霸女,欺行霸市,无年不有,无月不有,像这等恶人,上负天地君亲,下负福王千岁,若不严惩,何以对得起郎朗乾坤。”说完,两个侍卫按倒在地,噼噼啪啪一阵板子,揍得这家伙皮开肉绽,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这情形,众百姓哪里见过,直呼过瘾、解恨,尤其是绣场被打得几个后生,更是起劲地鼓噪,说是最好打死。
看看打得差不多了,朱雄对围观百姓一拱手说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最终如何处置还得娘娘和福王千岁决断,今儿个就把他解到京里。”说完,绑了个粽子扔到车上。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更有一等迂腐之人眼泪涟涟,喃喃自语,青天来了,青天来了。
朱雄等人正激动着,忽然一个清清朗朗的声音说道:“你们也只敢拿这等小奴才撒气,换个大点的你们敢吗?”谁呀,这么烦人,扫大伙的兴!把眼看时,一个瘦瘦高高的秀才走到近前,那人睨着宋乔说:“看得出你是他们的主谋,我叫牛金星,刚才我说的想必你听得清清楚楚。”如此无礼,如此唐突,朱雄立时就要发作。宋乔使眼色拦住,牛金星这个人他太了解了,性喜读书,通晓天官、凤角及孙、吴兵法,精于计谋,是个人才,但热衷名利,心胸狭窄,李自成的事业一大半原因就毁在他手里。所以,听到是牛金星,宋乔吃惊之余,对他有种本能的排斥,不过要做大事业还是要团结多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嘛!
因此宋乔微笑道:“宋某本是平凡庸人,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很开心了,只不知公子说的大的奴才是什么人,所指又是何事?”牛金星冷哼一声,说道:“内官孙堂在西河镇指地为矿,害的多少人家破人亡,如今又说一破庙有矿苗,非逼着周围人家包赔,要不然毁屋填井。这事情你管得了吗?”矿监税使乃万历朝一大祸患,朝野共愤,但万历皇上拼命坚持,谁敢硬来就拿谁问罪,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正直的地方官因此获罪丢职。
所以,这事情不能硬出头,自己被拿问事小,牵连到太子麻烦可大了。毕竟,阿福只是福王的奴才,踩踩他有惊无险,孙堂不同,他是皇上的人,踩他就是跟皇上过不去,而且似乎是太子跟皇上过不去,这可犯了皇家大忌,父子亲情也扛不住。
看到宋乔等人沉默不语,牛金星心里十分得意,哼!让你们得瑟,本来在西河镇我是人人尊敬的先生、智多星,可你们把阿福这一搅和显得我渺小可笑,也让你们难堪难堪,出出丑。宋乔早看出了他的用意,略一思忖,笑道:“矿监是皇上派出的,天下人争了几十年也没有结果,宋乔又何德何能有这个本事。阿福那奴才做尽坏事人人得而诛之,何况是当今太子爷呢,可孙堂是奉万岁旨意开矿交银,太子为万岁爱子,只可在内谏劝,哪能在外阻止,否则岂不陷太子于不孝?”这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在情在理,朱雄等不禁暗暗喝彩,贞儿只是笑,笑得骄傲、幸福。
牛金星脸色微变,心中不悦,咄咄逼人:“你是说这事你没本事管了,是吗?”宋乔摆摆手道:“见到了自当要管,请问孙太监要包赔多少银子?”牛金星笑了,伸出五个手指说道:“五千两!”五千两?这么多,贾母的荣国府那么富贵一年收入不过也才五六千,若是让一个普通人家过生活一百年也用不完。
倒吸一口凉气,百姓们议论开来,太恨了,这些死太监!陈贞慧、朱雄等人也面面相觑,宋乔偏身对贞儿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把所有银票给我。”贞儿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拿出四张银票来,娇嗔道:“这下要睡大街了,别说喝茶了喝水都没有。”宋乔笑笑,接在手中,看着牛金星道:“我这儿正好有五千银子,你拿去包赔。”此言一出,一阵潮水般的惊呼声,连陈贞慧他们也目瞪口呆,想不到这宋乔这么慷慨多金,牛金星更是瞠目结舌,长这么大他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牛金星毕竟是牛金星,迅速镇定下来,拿过银票说道:“好魄力,牛金星佩服,宋公子放心,这银子不会?白花,稍等片刻。”说完也不打招呼,从一名侍卫?手中牵过马骑上得得得走了。什么情况,莫名其妙?宋乔猜想这个牛金星一定会耍花样给自己找个台阶,这个台阶一定?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