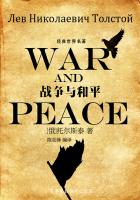幸福的家庭也并非千篇一律的,透过表面的和睦相处,令人烦恼的琐碎小事有可能一步步在恶化,最终发展成致命的冲突。
家庭夫妻年龄逐渐增大,夫妇之间的小烦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升级。夫妻二人刚刚开始新生活时,他们沉浸在幻想之中,希望创造安全的二人世界。正是这个阶段,原来似乎魅力四射的特点也变成了主要的烦恼,而可爱的伴侣也变成了悍妇,变成了粗俗平庸的男人,这也是走向离婚渐变的开始。正如渐变的鸡蛋,从光滑的表面怎么看都是好蛋,打开才知道已经浑浊,产生了变化。
伴侣之间掩盖小烦恼是非常危险的,而同样危险的是任凭这些小小的烦恼加剧恶化,以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幸福的生活本来是甜蜜的。长时间的甜蜜生活最容易让人产生平淡乏味的感觉。自从毕丰收一头扎到钱垛子上以后,香玲也就品尝到这种乏味的感觉。
清明节前后,杏花、桃花盛开。家燕从南方而来,在水湾旁边呢喃,在屋檐下衔泥垒窝。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三月的春风,很快吹绿了麦苗,吹开了村民多年闭塞的心。“五统一,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县普遍推行。农民挣脱了束缚他们手脚的绳索,从大集体中解放出来,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自由就是幸福,有什么幸福能比自由更值得珍贵。香玲的户口在老家东北,在毕丰收分口粮地的时候还没有迁过来,分田到户的时候没有她的口粮地,当然也不用耕种责任田。本来村里就人多地少,实行的又是“一田制”,二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家家过上舒坦的日子。吃的有了,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花的还不充足,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节约点花,减少开销。正如《小河水涨大河宽》所说的:
大河没水小河干,小河水涨大河宽;
国家好比大河水,农家好比小河湾,
家家户户讲勤俭,国富民强大家欢。
毕丰收的家里也就是他一个人的二亩一分地。刚开春的时候,大队推广地膜覆盖新技术,每亩地补贴一定的资金,鼓励农民推广使用这种先进的农业技术。补贴的资金大体够了买地膜和除草剂的钱。毕丰收的家里用村里补贴的钱,买来地膜,开春时用地膜覆盖上花生,除了抠出蒙在地膜里的花生苗,拔拔花生地里钻出地膜的杂草,就等着撑着口袋收获花生了。就是偶尔有点活,毕丰收也舍不得劳夫人的大驾。一天到晚相安无事,香玲也逐渐觉得有点腻歪,进而有几分急躁,仅有吃的就满足,后面花什么?“小农经济”的思想挡住了他向远处发展的眼光。
毕丰收是农民。“小农经济”过早地就在他心中烙上深深的烙印,也可以说已经在心田中生根发芽。
毕丰收出生在毕家洼,毕家洼以前曾经是一个盐碱滩、蛤蟆窝。春种三耧苗不成,种一葫芦打两瓢。正如一首歌谣中所唱到的:毕家洼,毕家洼,下来麦子喝顿汤,吃顿饼就得不留种。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毕丰收的童年饱含着心酸和泪水,是伴着纺车在地窨中度过的。正如歌谣《穷人》中唱道:“穷人身上不值钱,拿着黑夜当白天;刮风也得干,下雨也得干;累得弯了腰,总是缺吃穿;吃的糠和菜,穿的破衣衫;死了用破箔卷。”
蒙受大自然给他们的补偿,穷人家的孩子格外多。毕丰收的祖父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木匠,养育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祖母早年去世,不久,祖父也抑郁而去。他父亲排行老二,伯伯早年参加了“无极道”,在反贪官的斗争中不幸身亡,因为无儿无女,只好让毕丰收的大哥去“顶枝”。家里耕种的三十多亩地(老亩,一亩相当于现在的二亩),生活的重担过早地落在他父亲一个人的肩上。在村里,因为辈分特别大,全村人大多数人叫他“老爷爷”。
由于家里人口多,上有寡居的嫂子,下有未成年的小姑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毕丰收母亲肩上的胆子特别地沉重,压得脸一天到晚紧绷着,很少能看到一丝笑意。那年月,穿衣全靠自己织布。他母亲一天到黑纺线、织布,纺线特别快,只见纺车摇动,棉花菊苣在她手中跳跃,棉线穗子就不断加粗,一天能纺出好多穗子。她纺出的棉线特别细,疙瘩少。他母亲从怀上他以后,到坐完月子,自己纺花,织出一匹布。
由于家里穷,毕丰收大姐没上一天学,斗大字不识一口袋。过早的辛劳,影响了身体的正常发育,长成一个小胖墩,身体的直径跟高差不多,干起活来却雷厉风行。生活的历练使她过早地成为能吃苦耐劳的善良农村妇女。
毕丰收刚刚呱呱坠地就饱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滋味,没吃几天奶,他妈妈的奶水就给饿回去了。当时,山里能吃的野菜、树叶都被饥饿难忍又对生存怀有一线希望的人吃光了,草根树皮都没能幸免。这样,还饿死不少的人。村前死人,村后死人,村里死人,村外死人,一家一户都死光了也不稀罕。由于上面已经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结果饿死两个。母亲生下毕丰收几天就断了奶水,他只好经受断奶的磨难。后来,母亲生活稍微好一点了,慢慢又来了奶水。毕丰收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一样,竟然不喜吃那断断续续的奶水了,一生断断续续吃的奶加起来也只有三个月的时。
毕丰收模糊的记忆开始于64年打飞机。半夜里,刚刚七八岁的他被大人嘈嘈醒,天空一片明亮,跟白天没有什么差别。他不知道出了为什么变了天,就连他的父母也不知道。在父母的惊慌中,他和哥姐们睡眼朦胧的都被父母叫醒,穿好衣服在家等着,父亲先出去打听个水落石出。后来才知道,原来昨天(11日)晚上,台湾国民党一架p2v---7型高空侦察机,窜入大陆上空进行侦察活动,被青岛海军防空部队击落于离他家两三公里的驮山南塂,为了防止特务逃跑,8万民兵包围搜索坠机附近的山林现场。
毕丰收十几岁的时候,堆放着农具的南屋里还完整地存放着一架织布机,一盘磨。他还清楚地记得小驴扣上捂眼推磨,自己跟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走以及自己和小朋友爬上自家南阁子玩捉迷藏的情景;清楚地记得给自留地里的棉花打杈的辛苦和摘棉花时怕棉花粘上杂物时的小心谨慎;清楚地记得母亲纺线、刷机、织布的情景;清楚地记得母亲把铮锔埋在粮食里,以防其生锈的情景。
十年动乱时期,也就是毕丰收上中学的时候,学校请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奶奶忆苦思甜,那老奶奶讲着讲着,把不住调,结果走了调,诉起三年自然灾害的苦。解放前,我给地主扛活时,东家地主糊饼子蒸着鱼给长工吃,自己吃糠咽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就是六零年前后饿死的人老鼻子啦,引得全场师生哄堂大笑。老奶奶说实话,用老奶奶的实话来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生活比解放以前还要苦,毕丰收也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成长起来的穷孩子。
因为家里人口多,家里穷得叮当响,大哥到了结婚的年龄却娶不上媳妇,一个人离乡背井闯关东去了。毕丰收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到了必须娶媳妇的岁数,闯关东的大哥回来了,带回来家里唯一的一本课外书——小说《闪闪的红星》。家里终于有一本课外书了,毕丰收出于好奇,把书带到学校,在同伴中炫耀。林老师看到以后,被主人公的潘冬子的美好形象深深打动,选了几个精彩的段落在班级朗读。不久,毕丰收所在的班级里,小学生单调的学习生活中好像推开一扇天窗,吹进新鲜的空气,很快就掀起一股看小说的热潮。电影《闪闪的红星》演出以后,潘冬子的形象在他们心中丰满完整起来,“红星闪闪,放光彩”的歌曲伴着他们成长起来。
毕丰收的童年是伴着拾草和拔猪菜长大的。童年的伙伴们经常做的游戏是在新耕的土地上赛跑,在青草地上翻跟头,在平坦的场地上摔跤,在池塘边扔石片打水漂,看谁打的大水漂多。经过粗暴的较量,谁的蛮劲最大,也就意味着谁的本事最大。就洋洋得意几番,如同在体育比赛中获得大奖。
大哥回来以后,一家人在离散多年以后终于得到团圆,毕丰收那个高兴啊,无法用语言表达。毕丰收清楚地记得一个远房亲戚给他大哥介绍邻村的一个姑娘做媳妇,也就是现在的大嫂,由于当时家里实在太穷,就差没有把锅吊起来当钟敲。没有现成的新衣服穿着去看人(相亲),旧得衣服刚洗过又不干,只好把刚洗过的衣服放到锅台旁边烤。为了能让儿子穿上一条新裤子,他母亲连夜赶做,一夜没有合眼,到天亮以后才将裤脚缝好。相亲时穿的皮鞋也是借的,嫂子过门以后,好久没有看到皮鞋,一打听才知道皮鞋是借的,娶来媳妇以后又还给人家了。当时流传的俗语: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穿破布头。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排行第五的毕丰收,连破布头也穿不上。地瓜干是主粮,鸡腚眼里开银行。为了给大哥操持个媳妇,抻断腰筋才盖起来四间新房子,房子还没收拾好就拉下一屁股饥荒。
因为弟兄多,为了都能吃上饭,给孩子一条活路,家里差一点将二哥送人。要孩子的人家看上他大哥,已经成了强壮劳动力,能够帮助家人干重活了。毕丰收的父亲却想把老二送给人家。先后有两家人家想要,一家是闯关东的,在煤矿上班,因为能安排儿子下煤窑,就回来领前窝的儿子,前窝的老婆不给,毕丰收他爹“老爷爷”听说以后,想叫他把自己的二儿子领到煤矿去上班,家里将来出个挣钱的。那老客在毕丰收家里酒醉饭饱以后,下了保证,打过保票,将事定下了。可是,等老客回东北以后,就像泥牛入海没了消息。不是那老客吹牛,就是被老婆的枕边风给吹黄了。第二家要孩子的人家离他家四公里路,住在相邻不远的村子,家里没有儿子,想过继个儿子延续香火。毕丰收的二哥好说歹说就是不愿意去。剜却的心头肉,来补身上疮。他母亲只好反复做儿子的思想工作:孩子啊,大敌当前活命要紧啊!他们家没有孩子,吃的住的比咱们家好,至少你过去以后可以有口饭吃。好话说了几箩筐,舌头磨去大半截,才勉强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等到那家人家跑到他村来领孩子时,毕丰收的父亲见那个男人牛皮烘烘的,说自己家养的鸡有鹅大,老母鸡下的鸡蛋比鸭蛋还要大,跟鹅蛋差不多。他爹“老爷爷”一听就知道是个有骆驼不出牛的人。这样的人不踏实,靠不住,将来还不知变出什么花样来。父母之间递了个眼色,自己先变桄子了,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就是说得龙“吱吱”叫也白搭,说什么我们就是不给了。现在看来,要不是阴阳差错,毕丰收一家人可能还会落下七零八落的悲摧。
唯一能让毕丰收一家人自豪一段时间的是家里早早买上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购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煤油要油票,叫洋油;买布要布票,叫洋布。买食品也要粮票,差一点叫“洋票”。当时他们家所在村是先进典型,而所在的第一生产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生产队,粮食亩产过“长江”,用凭票供应的方式,全村配给到一辆自行车。村里就把那辆自行车票分给了他家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因为当时村里总共没有几辆自行车,需要的人太多,于是就采取抓阄的方法分配这辆自行车。这叫用简单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队长按照户数分了三十几个阄,在其中的一个阄上写上“自行车”三个字。一个雨星下到羊眼里,这辆唯一的自行车票让毕丰收的大哥抓到手,很快凭票把一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赶进家。全家人那个高兴劲不亚于生了个四世单传的儿子,你看看,他瞧瞧,比家里谁中了举人不逊半点色。毕丰收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后座上绑一根竹杆子,到场院去学,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一次,家里来了许多客人,趁大人忙,他又把自行车赶到外面学起来,回到家里,客人已经吃过饭,他端起半碗面条大口小口吞起来,看到在场的人都吃吃笑他,笑得他不好意思地扔下饭碗,撒腿跑了出去。事后才知道,他抢的那半碗面条是一个客人吃剩的。还有一次,因家里有点什么特殊事,眼看上学要迟到了,他骑着自行车去上学,被班主任老师误认为是“臭摆”,连讽带刺捎带过,就差点名,言外之意别人知道你家里有辆“大金鹿”。 自行车也曾经丢失过一次,但是好像有神助似的,竟然会被关心自行车的大哥,在公社供销社门前自行车堆里认出,顾不上抓小偷,扛起自行车就走,两公里路没敢停下,一气到家。自行车在失去几个月以后,奇迹般地找回来,又让一家人又高兴一段时间。这辆自行车后来成了他一家人生活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一直用了好多年。
不仅毕丰收家里困难,和毕丰收年龄相仿的三四十个孩子大多都是这样,只有两三件衣服,冬天没有换洗的,一旦洗了,就出不去门了,只好整天呆在家里。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夫妻插穿一条裤子,姊妹插穿一件夹袄,弟兄插穿一双鞋是家常便饭。衣服出汗以后没有替换的衣裳,不能及时换洗,就招了虱子,虱子又下虮子,虮子再生虱子,捉都捉不净。于是就有了这个通俗形象的比喻:捉不净的虱子,拿不净的贼。
毕丰收的小伙伴甜甜跟他同岁,本来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长得虎背熊腰,牛犊一般强壮。割草就割草,抬筐就抬筐,推车就推车。他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跟毕丰收比赛干活,从来没有落在后边的遭数。长身体的年龄,三天两头填不饱肚子,闹得肚子整天喊下课、喊罢工。丢人的事不能干,偷抢万万要不得,实在饿得没有办法了还得自己想法。那个年代没有动物保护法,饥不择食,鸟虫鱼虾只要能够搞到手的,就用来填饱肚皮。于是,春天的青蛙、夏天的知了,秋天的田鼠、冬天的河鱼都成了他猎获的对象。春天,“关老爷磨刀”(农历五月十三)以后,伴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青蛙到浅水里繁殖后代,晚上用马灯一照,连动不动,俯首可拾。白天,青蛙跑进棉条丛中捉虫吃,两个人对着头捉,甚至用棉槐条子抽,一次都能猎获不少。烧着吃,烤着吃,蒸着吃,不论怎么个吃法都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夏天知了的叫声勾引着他嘴里的馋虫,都快钻出来了。跟知了一类的还有好多种,一种叫“吱吱”,一种叫“哇呕”,一种叫“富得喽”。一到夏天,它们先后出洞,蜕变到树枝上,放开歌喉,鼓噪不停,偶尔合成轰轰烈烈的大合唱。他找来长长的竿子,用布条缠到一起,再到母亲封得结实的面缸偷抓一把白面,和成面筋。然后用菜叶或者树叶一裹,放到腋下夹热,然后缠到竿子顶端。在树丛中反复寻觅,一旦看到猎物,就凝住呼吸,双手握杆,往知了屁股上一触,知了就扑扑啦啦成了他掌上的食物。然后用柳条穿到一起,一晌午过后长长的一串知了就被带回家。回家以后,炒熟了,变成香脆的美味佳肴。比知了好吃的是幼蝉——知了猴。夏天的傍晚或者雷雨过后,知了猴从土里钻出来,爬到高处去蜕皮,是捕捉的最佳时机,“大喷”的日子能够捉到近百只。秋天,勤劳的田鼠成宿偷粮食,花生地、豆子地旁边的鼠洞是他的首选。他选择洞口泥多的硕鼠洞盗,铁锨下去很快就会掏出结实的花生和豆子。有时没有倒出硕鼠的果实,实在饿急了,肥大的硕鼠也不放过,点把火烧熟吃。那时候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冷,西北风刮着,烟面雪下着,他们忘记了身上穿的是那样的单薄,挽起袖子下河捞鱼虾,好像病重的母亲在家等着这点鱼虾下锅。忽然,有一天,甜甜再也不爱吃饭了,肚子鼓的老高,像打足气的皮球,不几天就瘦削不堪,等到去找做军医的哥哥看病,已经病入膏肓——肝炎晚期了,回家多给他买点好吃的。只一两个月就离开他生前的好伙伴,离开了他只生活了十几个春秋的村庄,悲惨地死去。
毕丰收的后屋的小伙伴叫喜顺,老家是高密的,因为家里穷,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出来讨饭,走散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被后爹“三崴”收养了。“三崴”走起路来一瘸一崴的,外号叫“三崴”。 “三崴”一脸络腮胡子,脸面胡子吹喇叭——一漫漫的,是个火上房子不知道焦急的家伙,因为年岁大了没有子女就收养了喜顺。“三崴”心眼不坏,就是家里穷,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不知道焦急。用他的话来说,只要生产队的仓库有粮,就饿不死人。于是年年吃救济粮,年年得救济款,一年穷十二个月。冬天来临,喜顺穿不上棉裤,整个冬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岁数大了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于是,他凭着模糊的记忆,偷偷给老家写封信,不长时间就失踪了。据说是跑回老家了。至于喜顺是饿跑了,还是冻跑了,没有谁找到喜顺问问,但是有一点敢肯定,他是被贫穷“穷”跑了。喜顺是捡来的,大家心知肚明,时间一长也就没有说长道短的了。毕丰收本来不是要的,一天到晚穿着露着棉花的破棉袄,倒成了大家戏谑的对象。爱耍嘴的照芝,不仅说毕丰收是要的,而且还能够有鼻子有眼地说出要家,煞有介事,那个说相声的侯宝林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尽管毕丰收巧舌如簧,满身是嘴也推不掉邻居照芝套在他头顶上的破帽子——要来的孩子,吃的穿的都不如别人家成了天经地义的。
喜顺穷急了往外跑,穷怕了又跑回老家。毕丰收再穷没有地方跑,他也曾经抗争过。一次,因为和父母闹了点小矛盾,也有点穷急眼的味道,也可以说狗急跳墙。毕丰收骑上家里那辆大金鹿离家出走了。走的时候接近傍晚,走出十公里路,天就黑下来。远远看见远处有灯光,他就摸着黑闯过去。原来是个看水库的小屋,看水库的大爷是个心软的人,见他是个孩子,可怜他,收留了他。夜里,老大爷问他是哪里人,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一个人匆匆赶夜路。他不好意思将事实的真相和盘端出,编了几句谎话,搪塞过去。晚上,他躺在人家的火炕上,实在是睡不着觉,辗转反侧,还没有熬到天明,就对自己的莽撞感到后悔。天刚蒙蒙亮,就跟老人匆匆告别,又羞答答地回了家。一家人找他折腾到半宿,也没有找到,只好等天明再想办法找。正在一家人犯难的时候,他回去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又惊又喜。当问起他一夜的经历,他告诉家人,自己是钻进苞米秸垛搂着自行车睡了一宿。
周围的村子,由于位置不敞亮,村里有些年轻人一点没出息,不是歪脖子,就是瞎眼,或者瘸腿、罗锅,难得见几个出挑的年轻人。毕丰收所在的毕家洼村三面靠河,风水极好,姑娘个个都细皮白嫩,美如天仙。小伙子个个虎背腰宽,像初生的牛犊。毕丰收就是其中的一个,美中不足的是后头上还长着一块十分难看的赖疮疤。小时候,曾经跑到姑姑家,摸着疮疤问姑姑,看我头上这大疤,将来还能说上个媳妇吗?我妈说我到老也挣不上个笼头,什么是笼头?媳妇是不是笼头?“头发长了就遮死了,保准你将来能娶个好媳妇。”小姑姑的一番知心话,叫毕丰收疑惑的心里充满了憧憬。他吃下一颗定心丸后,顿时心里暖和了许多。
他肩上背的包袱说放就放下了,他父母肩上的担子却从来没有放下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儿子打光棍。
于是,一年四季善待亲朋好友,施舍陌生人,好让别人帮助下茬都说上家口。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一点,好穿的自己舍不得穿一点,收鸡蛋的、卖小鸡的、锯锅锯盆的,但凡沾点脸熟的,经常到他家里去石灰抹嘴——白吃。一年下来,他家不知要管多少瞎饭。临村一个买小鹅的老太婆能说会道,父母还让毕丰收认她干娘,走动好多年,直到老太婆去世。
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愚昧落后啊,最好的表现就是对待化肥。化肥刚刚在这一带露面,公社干部来村推广应用 “料子”(化肥通俗叫法),不用花钱便能领回家。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农民,就是不信邪,说什么“门外没有三大堆,长好粮食全是吹,施这东西能打粮食来,亘古以来没听说”。公社干部的唾沫都磨干了,苦口婆心地找人谈话,走东家串西家,好处说了几箩筐,也没有说通几家。甚至有人碍于干部的面子,白天将化肥领回家,晚上再送到村西头,倒进大湾里喂葛根。第二年看到葛根生长旺盛,知道白花花的料子管用,料子一天一个价,长得比什么都快,花大钱买进口的想买都买不到。
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叫毕丰收过早地经受困苦的磨难。八口之家,一年分四五百斤麦子、十几斤花生油,还要把白面留给客人,把好菜等着来客才吃。一年到头“地瓜饼子、瓜齑茎子、不吃省着”。粮食产量低,公粮任务重,还要把好吃的换点零花钱。每年春天,家家都要给生产队掰花生种,花生种都留饱满的,捌也捌不开,不长时间就会把手指头磨秃露皮,实在没有办法时,用棉槐条子在火里一烤,趁热做成夹板,用夹板夹,甚至用牙咬,咬得满嘴灰尘,吐一吐再咬。心里眼馋花生也不舍得吃,他妈吓唬他说:“如果交不够队里的花生种,会叫队长抓到仓库里,不让回家。”他肚子里饿,嘴就馋,因为害怕被抓到仓库里,忍着馋虫不舍得吃。
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拔麦子。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黄的日子,天长夜短酷暑,紧张劳动一天后,还没歇歇过来,天就亮了。在虎口夺粮的日子里,用镰刀割麦子,白天在麦茬地里一蹲就是一天,日晒地烤不说,晚上还要到大场院去打麦子。麦场上,脱谷机隆隆地响着,人群在汽灯光的映照下穿梭似的忙碌着。刚开始的时候,脱谷机大口大口地吞进麦穗头,从屁股后头一口一口地吐出柔软的麦秧。脱谷机吐出的麦秧堆成了垛,垛麦秧的人站在垛顶上,好像飞到了月宫。用不上多长时间就开始磨蹭起来,没有麦穗子可吞,脱谷机只好空转,熬到半宿也打不出多少麦子。第二天照常下地割麦子,顶着似火的骄阳,踏着晒得滚烫的麦茬地,那滋味好像掉进蒸笼里,实在是不好受。几天下来,人就手无缚鸡之力,实在是割不下麦子,好像是科技队的植物医生在给麦子诊脉,难免会遭到生产队长这样的呵斥:“不愿干,回家养孩子去,别在这里给我磨蹭。”
天天大呼隆干活,把人都快折磨死了,麦收过后,村里人还是没有麦子吃。
气候变暖是近几年的事,毕丰收的少年时代,好像是另一个老天爷主管。天比现在冷;雪,比现在厚。雪下得比这几年频,每年都会有几场二三尺深大雪。每到深秋初冬,生产队就组织收割完农作物的老人们打地窨子,扎进地窨子里编席。毕丰收跑前跑后,在人群中赶着热闹。村民们在离村不远的空旷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大坑,有十七八米长,两米多宽,一米七八的深浅。然后在上面横断上盖房子用的木料,铺上高粱秸、苞米秸,覆盖上厚厚的泥土。北面稍微高出地面,南面高出地面五六十公分,留出几个简易的小窗,做一个简易的门,在出口的地方放一个打场用的碌碡,上下进出方便。刮出来眉秧子堆在地窨顶上砂土上面,雪白的眉秧子抱成团覆盖在地窨子上,背阳的眉秧子上落满积雪,经冬不化,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
地窨子是父辈们用来编席的场所,毕丰收从小就在这里面跟着大人学编席,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在地窨里编席的席眉上撒满心酸,在席子缝隙里布满劳苦。地窨子也是毕丰收少年温馨的港湾,里面温暖如春,不仅能从讲故事高手那里听到迷人的故事,还能从说书人那里听到迷人的戏曲。物以稀为贵,初次听戏曲就叫他陶醉其中,难以割舍,以后每每回忆起来,始终觉得津津有味。
编席是相当辛苦的,秋天收获高粱,刨下高粱秸后,经过剁跟,剥皮,破出眉子再晒干,冬天要砸开湾里的冰窟窿沤席眉子,从冰冷的水里捞出来沤好的席眉子,到蹲在地窨子编出一领炕席需要许多道工序。其中刮眉子编席等工序又累又冻,编席的人常常熬得咳嗽不断,讲故事是他们派遣疲劳的一种方式。在繁重的编席劳作过程中,寻找一点乐子。经常是年幼的问,年长的讲,茶馆式的,七嘴八舌。什么关公战秦琼,什么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大唱空城计,毕丰收少年时听到的故事,多半是从这里猎获的。邻村有个光棍叫王凤考,会唱几段戏曲,夏天给村头纳凉的人唱,冬天到地窨子里吊吊嗓子,唱《王汉喜借年》、《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内容无非是“东西房子南北梁,两个人睡觉鞋两双,驴尾巴长在驴屁股上”之类的大实话。但在那个缺少影视的年代,也成了人们难得的精神佳肴。他是个光棍,不愿意捋起衣袖做饭,也没有好吃的可做。喜欢戏曲的人为了笼络他多去唱几回,有人捎包子给他吃,有人带面条给他吃。那个叫照芝的老汉,用自己夹来的山鸡(一种较大的鸟),做成面条浇汤后带给他。毕丰收只能望“雀”兴叹,自愧不会唱几曲。王凤考也很会吊大家的胃口,每到精彩之处他就会“唱到这里算一段,明天晚上接着唱”。 戛然而止的戏曲让毕丰收大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
经常有人甜生生地喊着王凤考的小名:“蔻,我说你再唱一段。”也有人直接喊“来一段儿”。这时,王凤考就清一清嗓子,用尖溜溜的假嗓唱起来。
踏着咯吱咯吱的积雪,顶着刺骨的寒风回家,为自己的无能多少有点遗憾,偶尔,也吼上几句。毕丰收从小在这里跟着大人学着编席,先编边,后边中间,从简单到复杂,很快就自己能编起一领完整的席。编席要蹲在地上,跟湿漉漉的席眉子打交道,手冻得通红,头低得老大老沉,割破手也是难免的,好在席眉子割手不会化脓。于是,冬天的地窨子成了他的劳动教养所,也成了他接受艺术熏陶的温馨港湾。
地窨子的春天是孩子们的。忙了一冬的父辈们,在家家过年炕上都铺上了新席子以后,就不再光顾撒满辛酸的地窨子。这时,没有了大人,地窨子才真正还给孩子。毕丰收和伙伴们在地窨子里搬家家,捉迷藏,地窨子便成了他们的乐园。眼睁睁看着地窨子被大人们扒掉,毕丰收和他的小朋友们禁不住流出眼泪,比扒他家的房子还难受。好在地窨子年年有,开春扒掉秋冬造,一年更比一年好。